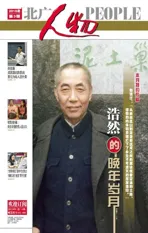浩然的晚年岁月
2018-01-20李培禹
□本刊特约作者 李培禹
『「写农民,为农民写」,我要把这担子挑到走不动、爬不动,再也拿不起笔的时候为止。忘了农民,就意味着忘了本,就表示伤了根,就会导致艺术生命的衰亡。我不该这样做,不敢这样做,不能这样做……』

今年2月20日,是著名作家浩然去世10周年的忌日。今年的3月25日,是他诞辰86周年的纪念日。我常想,如果浩然老师还在,也不过86岁;而他如果还能写作,哪怕仅写一些独有的回忆文字,也一定会很精彩。如果天假以年,他的创作很有可能弥补上以往作品的缺憾。每每想至此,我便黯然神伤。
时光回到10年前,即2008年的2月20日。早晨,我刚走进办公室,就收到这样一条短信:“我父亲于今晨两点去世,特告。梁红野。”红野的父亲就是著名作家浩然。我知道,春节前医院就报了病危。几天前红野在电话里还曾安慰我说:“我们把父亲的衣服都准备好了,他也没什么知觉和痛苦了。”想起最后一次去看望他,是在北京一家医院的病房里。那次,我大声呼喊着:“浩然老师,我来看你了!”却怎么也唤不醒当年那个一把握住我的手,说“你来得正好”的他了……
最后的时光
从1990年我调到《北京日报》文艺部后,因为工作关系,记不清去过多少次位于河北三河浩然居住的“泥土巢”了。每次见到他,他都会热情地握住我的手,说:“培禹同志,你来得正好。”后来我越来越理解他这句话的含义了——他把我们去采访、看望他,看作是报社对他工作的支持;另一层意思是能给他帮点忙。当时他扎根三河农村,一边创作一边实施他的“文艺绿化工程”,即培养扶植农村文学新人,他哪有时间进城啊。我去一次,就会带回一堆任务,比如他为农民作者写的序文、评论,要我带回编辑部;经他修改后的业余作者的稿子,要我带回分别转交给《京郊日报》或《北京晚报》的同志,他匆忙给这些编辑朋友写着短信……这景象仍历历在目。一次,他的邀请函寄到了,打开一看,是他亲笔书写的:“届时请一定前来,我当净阶迎候!”原来,三河县文联成立了,他的心情是多么高兴啊。就这样,浩然在三河的十几年里,自己的创作断断续续,他却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培养出众多的农村作者,付出了满腔的心血。
红野说,父亲走时是安详的,他意识清楚时,儿女、孙辈们都围在他身旁。我说,是啊,他一生写农民,为农民写,那么留恋农村、热爱农民,你看他给儿子起名叫红野、蓝天、秋川,给女儿起名叫春水,孙子、孙女则叫东山、绿谷,你们都在他身边,他会欣慰、安息的。况且,他的骨灰将安葬在他那么挚爱着的三河大地,他将在父老乡亲们的念想里永生!
北京日报社要为浩然同志的逝世敬献花圈。撰写挽联时,我想起浩然老师曾为我书写的一幅墨宝,全部用的是他著作的书名:喜鹊登枝杏花雨,金光大道艳阳天。我准备以此为上联也用他的书名写个下联,便打电话给浩然的好友、《北京晚报》原副总编辑李凤祥和著名书法家李燕刚,我们共同完成了这样一个下联:乐土活泉终圆梦,浩然正气为苍生!——浩然同志千古!
2009年4月12日清晨,一场春雨悄然飘落京东大地。纪念著名作家浩然逝世一周年暨浩然夫妇骨灰安葬仪式,在河北省三河市灵泉灵塔公墓举行。他的儿女红野、蓝天、秋川、春水率孙辈东山、绿谷等早早来到墓园。女儿春水含泪细心擦拭着父母的塑像,轻声说着:“爸、妈,你们看有多少领导、朋友、乡亲们都来送你们了,你们放心地安息吧。”浩然因病医治无效于2008年2月20日凌晨2时32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

浩然1988年落户三河,在这里他“甘于寂寞,埋头苦写”,完成了继《艳阳天》、《金光大道》后新时期最重要的一部长篇小说《苍生》,并把它搬上荧屏,深受农民群众喜爱。浩然魂归“泥土巢”,不仅三河市委、市政府、市文联当作一件大事来办,也牵动着祖国各地他的生前好友、众多得益于他的几代文学作者的心。
浩然是哪里人?
浩然是哪里人?顺义县的乡亲们说,顺义人呗,金鸡河、箭杆河多次出现在他的笔下;长篇小说《艳阳天》就是写焦庄户的,“萧长春”还在嘛!通县的干部说,浩然是通县人,他是在那里成长起来的,他的许多作品都完稿于通州镇,而且他现在还是玉甫上营村的名誉村长。蓟县的同志则理直气壮地说,怎么?浩然明明是我们蓟县人嘛!他们翻出浩然在一篇后记中的话:“从巍巍盘山到滔滔蓟运河之间的那块喷香冒油的土地,给我的肉体和灵魂打下了永生不可泯灭的深深烙印。”(蓟运河古称鲍丘水,元、明两朝称潮河,清代始称蓟运河。现属国家一级河道。元朝定都北京,粮运任务很大,把往通州粮仓运粮的通惠河和连通的潮河,统称为大都运粮河,北京当时是元大都,蓟州防兵军粮,主要来自南方到直沽寨(天津)的转运仓储,先是出海复折蓟运河,后是通过新开河转运蓟运河,直达蓟州。——编者注)
1988年,一本600多页厚的长篇小说《苍生》,悄悄摆上了新华书店的书架,随后,广播电台连续广播,12集电视连续剧投入紧张的拍摄。当一幅展现80年代农村改革的巨幅画卷,渐渐地展开在人们面前时,敏感的海外报刊最先做出反应,香港一家报纸的醒目标题是:《艳阳天》作者沉寂10年又一次崛起。中国文坛不能不为之震动,首都庆祝建国40周年文学作品征文头奖的殊荣,授予了《苍生》。来自农村的同志亲切地呼唤着那个熟悉的名字:哦,浩然!
其实,浩然的档案这样记载着:浩然,本名梁金广。原籍河北省宝坻县单家庄(现属天津市),1932年3月25日出生在开滦赵各庄煤矿矿区。10岁丧父,随寡母迁居蓟县王吉素村舅父家,在那里长大……

他把『心』带到了三河
早在浩然带着女儿住在通县埋头写作《苍生》时,我就萌发了采访他的念头。我向报社一位家也在通县的同事打听浩然家怎么走,这位同事说:“你到了县城街口,找岗楼里的警察一问,谁都能领你到他家,业余作者找他的,多啦!”
1990年4月下旬的一天,我到三河,印证了那位同事的话。“噢,找浩然啊,往前到路口拐弯,再往西就是。”三河人热情地把我引到了浩然的“泥土巢”。“姑父,来客人啦!”朝屋里喊话的是浩然妻子的一个娘家侄女,她住在这儿帮着照顾久病卧床的姑姑,腾出手来也帮浩然取报纸、拿信件。正在和几位乡村干部交谈的浩然迎了出来。他,中等身材,岁月的痕迹清晰地刻在了他那仍留着寸头的国字脸上,鬓角两边已分明出现了缕缕银丝,只是那双深邃而有神的眼睛,是一位充满旺盛创作力的作家所特有的。
显然,那几位村干部的话还没说完,一位岁数稍大点的,把浩然拉到一边“咬起耳朵”来,浩然认真地听着。那情景,我下乡采访时常见到。不用说,浩然这个“镇长”,已经进入角色了。正好,我可以好好打量打量这“泥土巢”。这几间平房,是他担任了县政协名誉主席以后县政府专门为他盖的。东边一间是卧室,和浩然相濡以沫40多年的妻子患病躺在床上已一年多了;中间比较宽敞的,是浩然的会客室,乡村干部谈工作,业余作者谈稿子,都在这儿;靠西头的一间是专供浩然写作用的,写字台上四面八方的来信分拣成几摞,堆得满满的,铺开的稿纸上,是作家那熟悉的字迹。看来,由于不断有人来打扰,他的写作只能这样断断续续。
浩然服侍老伴吃下药后,给我倒了杯茶。“我这人天生窝囊,最怕说话,但动了感情,往格子纸上一写,还行。”他说的是真的,谈起他如何把家落户在三河县,如何写出《苍生》等等,他讲得平淡无奇,但翻看一下他做的有关日记、笔记,或“写在格子纸上”的文章,却处处是真情实感的流露,篇篇不乏精彩之笔。最能说明这点的例子是,他和农民萧永顺(长篇小说《艳阳天》中萧长春的原型)是风风雨雨几十年的挚友,他多次提到过,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后来,他写了《我和萧永顺》,在《光明日报》发表,人们才真正被那真挚的深情厚谊所打动。这篇纪实散文,毫无争议地被评为《光明日报》庆祝建国40周年散文征文一等奖。
书,是作家辛勤耕耘的最终产品;书,是作家漫长创作生涯的浓缩。我的目光不由地停留在占满一面墙的四个大书柜上。浩然拉开布帷,打开书柜,拣出几本给我看,有的是世界名著,有的是已绝版的旧书,经他重新修整并包上了新皮儿,扉页上大都有浩然的签名和购书日期。还有一部分是我国和世界上的一些著名作家、专家学者送给浩然的赠书,相当珍贵。作为一个也写过点东西的业余作者,我最理解,一个作家珍存的,当然首先是他自己写的书。“泥土巢”的书柜里,竟摆着浩然1958年出版的第一本小说集《喜鹊登枝》,摆着他60年代的成名作《艳阳天》,摆着70年代的《金光大道》和80年代的代表作《苍生》,以及日本、法国、美国、朝鲜等翻译出版的他的著作译本。我看到,包括一度给他带来灾难的上下两册《西沙儿女》在内的共50多本书——浩然的50多个“孩子”,他都随身带来了。浩然把自己的“心”带到了三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