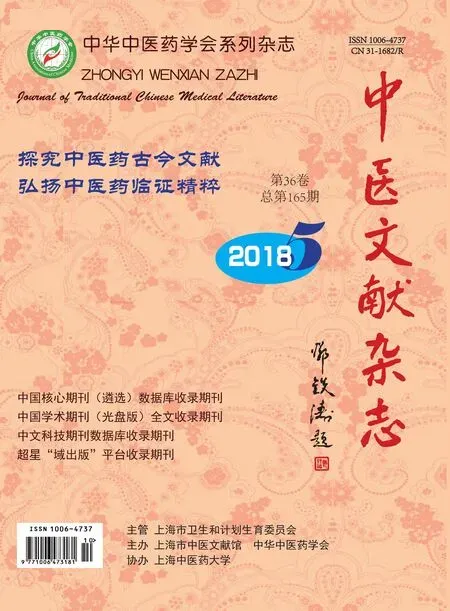中医思维的话语呈现方式*
2018-01-19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210023
南京中医药大学(南京,210023)
周延松
现代语言学认为,语言不仅是人类的交际工具,还是重要的思维工具。从最单纯的方式理解,怀特海认为语言表现为思维在习惯上的结果和显现。[1]中医和汉语都诞生于中华文化的土壤,同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如汉语显示出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中医话语则是中医思维的结果和显现。语言是一种具有层级性的系统,从不同的层面进行考察,无论汉字、语词、语句,还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语段、语篇,中医话语在表现出汉语根本特点的同时,还是中国传统思维及中医思维方式的外在呈现。以下以思维为视角,从上述不同层面,探讨中医话语和中医思维相互建构的特征及其表现,并就规范化、标准化趋势下的中医话语转型,提出相关建议。
涉医汉字中蕴藏着中医思维的轨迹
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指出,作为原始科学通史的一个方面,对“会意”的科学词汇的起源进行考察,具有重要的意义。[2]拼音文字中没有字和词的区分,古代汉语以单音节词汇为主,在一般情况下,字和词是同一的,因而更准确地说,这里的“科学词汇”应该理解为“科学字汇”。他正是从汉字的“会意”性质,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而要追溯“科学词汇”的起源,还原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原初关系,我们的文化视野和心态就要返回造字时代,我们的逻辑思维也需向原始的神话思维靠近。[3]恩斯特·卡西尔也从发生学的观点,把想象和直觉看作是人类言语的一个初始和基本的特点。[4]考察“医”之“源”,“医者意也”,中医思维同样具有这种直觉的性质,因而缺乏严密的逻辑性,这在涉医汉字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如“医”字,繁体作“醫”或“毉”,是“医”、“殳”和“酉”或“巫”的组合;如“药”字,繁体作“藥”,为“艹”和“樂”的组合。既是“会意”,或许缺乏精准的所指,具有一定的模糊性,即如“酉”和“樂”的具体意涵尚存争议,然而它们的语义,无不出于“意”。同时,因为是一种直觉,不少涉医汉字的所指依凭的基础是人类经验,而非如西方医学中解剖学般具有实证性,这也是“意”之一义。如“气”、“神”,如“经”、“络”,皆是如此。
汉字是一种表意文字。狭义的“会意”为“六书”之一,是汉语造字的一种方法,这里所说的“会意”则是广义的。其他的造字方法,如象形、指事、形声,乃至更偏向“用字”方法的转注、假借,或于其音读中显现附加的文化义,但因形见义,我们大都可从“意”找寻到其构形和使用的理据。在这个意义上,“会意”也可说是众多涉医汉字基本的造字与用字原则。如“藏”,本有“隐藏”、“贮藏”之义;“脏”为人体内脏,多特指心、肝、脾、肺、肾五脏。因五脏位于体内,由外部不可见,且具有“藏精气”的共同功能,故而“藏象”又经常写作“脏象”。除了音读相近,“意”才是“藏”、“脏”两字通用的基础。
中医术语的取象比类属性及人本价值取向
术语是某一特定科技领域所使用的专业性词汇。对一种语言来说,不同科技领域术语和全民常用词汇的结构方式应该是一致的,否则会造成交际的障碍,其差异主要体现于词汇的语义构成。一般而言,科技术语的所指是明确的,语义是单一的,且具有很强的客观性。但在中医,却非全然如此。一个显著的特点是,不少中医术语的形成经历了取象比类的过程,使之具有了丰富的语义层次与内涵,同时体现出鲜明的人本主义倾向。而取象比类和人本主义,正是中医思维和中国传统思维的重要特色。
如作为中医理论基础的“五行”,由《尚书·洪范》最早提出:“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这里的“水”、“火”、“木”、“金”、“土”,已不是五种物质材料,而是五种功能、五种属性的象征性符号,这些功能和属性的获得,需经由“比类”的思维。从客观上讲,作为具体物质材料的“水”、“火”、“木”、“金”、“土”与“润下”、“炎上”等抽象的功能属性在认知上具有极强的共性,这是“取象”的前提。
“象”是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医话语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藏象”典型地体现了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它把人体内在的以五脏为中心的生理、病理系统及其表现于外的生理、病理征象与外在自然环境中的事物与现象进行类比,赋予心、肝、脾、肺、肾这些原本仅属于人体器官的概念更多系统性的功能,从而获得一种极具共性的丰富内涵,“藏”的基本语义得到了极大的延伸和扩展。
从人体或日常生活中习见的事物与现象,依基本语义,通过比喻或引申,赋予其专业性内涵,这是很多中医术语的基本形成手段,体现出鲜明的人本主义意蕴,同时形成中医话语的形象性或者说生动性。如“命门”,“命”是生命,“门”是出入的通道与门户,以之命名“先天之本”的肾脏,正取之于“命”与“门”的物质意义,且形象地表明了肾脏与其他脏腑器官之间的功能联系,即便用作特定穴位的名称,其物质意义与生理功能也密切相关。又如“关节”,以物质性的“关节”喻指人体部位的“关节”,两者在功能、属性上的共性至为明显;“气海”为气的海洋,无论视之为脐下的丹田部位,还是作为穴位的名称,气血充盈的显著特征清晰可知。
词汇的语法作用、弹性机制隐含着功能联系、中和思维
法国社会人类学家葛兰言认为,中国人思维的主要特性是把各种事物看成关联性的存在。[5]陈来进而提出,整体主义和关联思维集中体现于中医。[6]中医思维强调功能联系。在人体内部,无论脏腑之间,还是脏腑与形体、官窍,乃至精神、情志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人体各部位的生理现象与病理变化会在其他部位表现出来,因此有“头痛医脚”的治疗理论与方法。而在外部,人体与所在的自然、社会环境之间,同样具有紧密的关联。在疾病的诊治过程中,往往不拘泥于某一具体部位或症状,而要进行总体审察,所谓四诊合参、标本兼治等,也都源于以关联思维为基础的整体主义。所谓“天人合一”,不仅是一种认识论,也是中医思维的方法论,其结果,则是“致中和”,一种服务于整体、以和谐为终极理念的中和思维。
在中医话语的词汇层面,功能联系与中和思维的突出表现之一,是词义与词类的归属。如马建忠所说,“字无定义,故无定类”,只有知道了上下文的意思,才能明确它所属的“类”。[7]“无定义”已如上文所述,“无定类”则典型地体现于词类的活用,两者都显示出中医话语的相对性特征。如“心为君主之官”、“心主血”,“主”一为名词,一为动词;“血瘀”和“瘀血”,“脉浮”和“浮脉”,前为主谓结构,后为定中结构。只有在具体语境中,才能把握某一词汇的语义及语法功能,也只有在特定的上下文中,它才具有确定的词性,其中显现的,是这一词汇与句中其他词汇在功能上的相互联系与协调。
郭绍虞指出,汉语词汇既有单音也有复音,很多处于演化的过程中,而没有固定下来,除了须与其他词汇保持功能上的联系,有时还根据韵律和修辞的需要进行灵活的调整,或化单为复,或化复为单,这使汉语词汇具有了一种弹性的机制。[8]千百年来,中医凭借着有效的诊疗实践和浩瀚的经典医籍得以流传,即便在以现代汉语为主要语言载体的当下,中医话语中依然保留着较多古代汉语的遗存,以双音节词汇为主体的中医现代话语中,并存着丰富的单音节词汇,使之呈现出一种极具古典韵味的话语特色。如对血和气的关系的描述,“血属阴而主静,气属阳而主动”,若以双音节词汇加以表达,必然失去其原有的韵味。再如关于外感六淫的性质,“风性浮越”、“寒性凝滞”、“暑性升散”、“湿性重浊”、“燥性干涩”、“热性炎热”,单双音节交替,韵律感极强。
其实,不论词汇的语法功能还是音节弹性,都服从于更高一级语法单位,即句子乃至语段、语篇的整体表达需要。因为我们对话语的理解,并非根据单个词语的意义,而是通过总体的印象去把握的。[9]
意合成句体现出整体观念
陈来认为,中国哲学注重的是关系,而不是实体。[6]体现在语言范畴和思维范畴的关系上,西方思维和语法更为直接,中国思维则和语义更为密切。[3]在句法层面,因缺乏严格意义上的性、数、格、时、体、态等形态变化,汉语多有“意合”句,而印欧语系诸语言则不同,多为“形合”句。于话语方式所显现的中医思维,同样是基于功能联系的整体主义,其典型为经络观念,一种至少在目前看来被认为“实体”缺失,却“关系”确凿的存在。
甘阳提出,中国传统文化在遭遇西方文化以前,是一种没有逻辑和语法的文化。[10]大体说来,“意合”句在古代典籍中的运用较为普遍,现代中医话语因延续和保存了较多古代汉语的表达方式,也时有所见,或引用,或沿用,或化用。如《黄帝内经》中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是一个假设关系的复句,两个分句之间没有关联词语,只有通过语义而非语法,才能确定其关系。“学医不知经络,开口动手便错”,“针所不为,灸之所宜”,也是同样的情形。在长期使用的过程中,有些说法更进一步简化,形成一种紧缩复句,如“头痛医脚”,它甚至由医学话语进入了全民常用的惯用表达系统之中。
汉语缺乏屈折形式,有人便因之诟病。威廉·冯·洪堡特却坚持认为,从表面上看,汉语没有任何语法,但正因为此,汉民族才发展起一种敏锐的意识,能够明辨言语形式中的内在联系。[11]这种意识,与中医思维的取象比类、功能联系、中和思维及更为深在的整体观念一脉相承。在语言层面上,从涉医汉字的“会意”特点,专业词汇的语“意”构成,到句法结构的“意合”特征,一以贯之,呈现出“医者意也”的思维底色。也正是这些特点,形成了中医、汉语和中国文化区别于西医、印欧语言和西方文化的独特性,并以其数千年不衰的发展历程,证明了它旺盛的生命活力。
语段结构、语篇模式折射出系统与变易思维
东方文化注重综合,西方文化注重分析。[12]作为东方思维的基础模式,综合思维鲜明地呈现于中医话语之中,而综合不仅可以和整体观念互相阐发,而且与系统和变易思维紧密相关。系统论的基本思维方式,是把宇宙万物视为系统,从系统及其构成要素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出发,分析其结构和功能,系统的动态演化则是变易思维的基础。
“气”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基本概念,被应用于各种学科领域。在哲学层面,气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气的运动推动着万物的发生、发展及变化。于中医学理论,作为一种运行不息的精微物质,气是人类化生的原初物质基础、生命活动的源泉与动力,以及人体与外部联系的中介。显现其中的,是整体观观照下人体的系统性,和生生不息的变易性。而在古典文论中,同样讲求文气的自然流转和前后贯通。中医学的气理论和文气理论的结合,形成中医话语语段及语篇的基本呈现方式,文气的通畅成为其内在的基本要求。张景岳在《类经附翼·医易》中说:“《易》者,易也,具阴阳动静之妙;医者,意也,合阴阳消长之机。虽阴阳已备于《内经》,而变化莫大乎《周易》。故曰天人一理者,一此阴阳也;医易同原者,同此变化也。”从语段的层面加以分析,起承转合,语意流通,虽极少使用关联性词语,却自有一股文气贯穿其中。医易同源,医意同理,系统与变易,整体与综合,从不同角度,共同揭示出中医思维的特性所在。
中医的辨证施治,也明显体现出系统的思想。[13]病案是中医话语语篇的典型形态,病案的书写鲜明地体现出中医思维的系统性特征。从疾病的诊治来说,它把疾病患者作为一个系统,而非仅限于确定的发病部位和当下的具体症状,望闻问切,综合运用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各种感觉方式,通过对现病史和既往病史的全面考察,追溯病因,并针对疾病的施治,作出预后的推断。落实到病案的书写,便包括了疾病的发生、发展、演变、预后等各个阶段和诊治、调理、康复等各个环节。这样,就在历时与共时、静态与动态相结合的基础上,对疾病的整个过程作出系统综合性的描述,其历时与动态的演化,正是变易思维的集中体现。
余 论
法国人类学家克洛德·莱维-斯特劳斯说过,在逻辑关系、对位、相关性等各个方面,语言和文化所得以建立的材料都属于同一种类型。[14]对涉医汉字、专业术语、词法结构、句法特点、语段构成及语篇模式的考察分析,使我们较为清楚地认识到中医话语的特性及其与中医思维的紧密关联,中医话语所具有的模糊性、相对性、生动性和韵律性,无一例外地可从中医思维方式找寻到其内在的理据,而在更广的层面上,它们又从中医这一专门领域印证和呈现出汉语及中国文化的性质与特征。
中医话语及显现于其中的中医思维,是历时地形成的,且具有相当的稳固性与连续性。一个显著的例证是,作为中医学理论体系形成标志的《黄帝内经》,自诞生起直至当今,其基本的概念及理论术语、表述方式等,还依然存活于现代中医话语之中。随着中医现代化与国际化的进程,中医话语的规范化、标准化逐步被提上议事日程。对此,不能把西方科学话语作为唯一的参照系,采取单一化的科学视角,而应结合中医思维及其话语特性,缓步推进。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医话语权的缺失,和中医思维相较科学思维的弱势地位密切相关。在世界范围内,与文化全球化并行的,是一种多元化的潮流和趋势。在西方国家,早就开始反思“科学”的独尊地位,并伴随着对英语霸权的不满和抗争。作为一种本土原创的理论体系,对中医思维与话语方式的深入探究,将是提升中医话语权的必经之途,也是提高中医文化自信的重要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