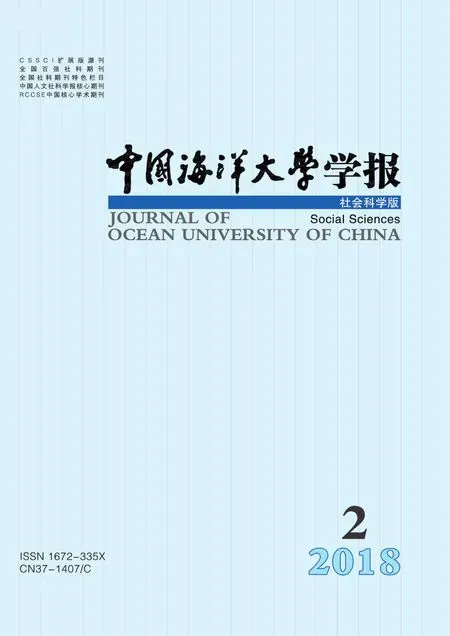我国海洋渔业法律制度的困境与破解*
2018-01-15王小军
卢 锟 王小军
(1.上海海洋大学 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上海 201306;2.上海海洋大学 海洋政策与法律研究所,上海 201306)
近年来,我国近海渔业资源严重衰退,大部分经济鱼类已不能形成渔汛。[1]在严峻的海洋渔业形势面前,我国政府以促进海洋事业的健康发展为核心,探索联合执法机制,组织开展专项行动,实施海洋督查制度,在渔业资源养护方面取得了积极进展。然而,由于传统和体制的原因,我国政府依靠超常的组织和动员能力,试图通过强化管制措施来改变近海“无鱼可捕”的现状。但危机似乎并未真正解除,既有的海洋渔业法律制度遇到了实施困境,近海渔业资源日益减少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如何完善法律制度,规范相关主体的行为,促进渔业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成为摆在立法和执法部门的一道难题。
一、我国海洋渔业法律制度的生成逻辑
从表面上看,海洋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是不可占领的;应向所有国家和所有国家的人民开放,供他们自由使用。[2](P24)然而,人类影响的加剧,威胁到海洋的长期生产力。连坚定的市场信徒都承认渔业是一个非常需要制定政策的领域,若不加管制的话,市场通常是失灵的。[3](P601)伴随着二战后北半球渔业资源使用的惊人膨胀,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以自上而下的命令与控制手段为主要特点的政府管制模式。[4](P88)这种模式主要表现为基于许可证制度的管理,行政部门设定投入和产出控制指标强制渔业生产者遵守,对违反者施以严厉制裁。
在我国,国务院1979年颁布的《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要求建立渔业许可证制度,将自由入渔改为准入控制,并对捕捞的时间、水域、渔具和渔法等提出了要求。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以下简称“《渔业法》”)强化了许可证制度,通过控制渔业人口来限渔。为加强渔船管理、限制捕捞能力,农业部1987年开始对海洋捕捞渔船船数和功率数实行总量控制。为养护渔业资源,农业部1995年颁布《渔业捕捞许可管理规定》正式实施伏季休渔制度。2000年修改的《渔业法》明确了捕捞限额制度,规定对渔获量进行量化限制管理。总的来看,我国的海洋渔业法律法规体系以政府管制模式为主,基于渔业许可证制度、船网工具控制指标制度、伏季休渔制度和捕捞限额制度,由政府自上而下地确定投入和产出控制指标并实施监管。对于违反规定者,施以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没收渔具和渔船、吊销捕捞许可证、罚款等行政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既对受处罚对象形成特定威慑,也对其他监管对象形成普遍威慑,继而保证制度的实施效果。这种模式的逻辑起点是,渔业生产者作为理性经济主体,受经济利益驱动,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当违法成本高于违法利益时就会选择守法,反之则倾向于违法。[5]有两个重要因素影响了守法状况,一是处罚的严厉程度,二是违法行为被发现与实施处罚的几率。因此,监管者往往通过提高处罚力度和执法频率来迫使监管对象者出于对不利后果的恐惧而选择被动守法。这种模式的优势在于容易管理操作、短期效果明显。
在我国近海渔业资源几乎枯竭的背景下,以威慑为基础的管制极有必要。严格落实渔船“双控”制度,深入推进“绝户网”和涉渔“三无”船舶清理整治行动,开展伏季休渔专项执法行动,对于集中解决突出的违法问题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单向度的管制方式具有天然的片面性。一方面为克服“市场失灵”而强化的监管者本身也有可能“失灵”;另一方面由于忽视监管对象的合作者角色,不易达成共识,很难形成常态化管理。这就导致了我国主要的海洋渔业法律制度在实施过程中不同程度地遇到了一些问题。
二、我国海洋渔业法律制度的困境及其原因分析
(一)渔业捕捞许可和船网工具控制制度的困境
渔业捕捞许可和船网工具控制制度是限制捕捞力度的投入控制措施。《渔业法》第二十三条规定,“国家对捕捞业实行捕捞许可证制度。……批准发放海洋作业的捕捞许可证不得超过国家下达的船网工具控制指标。”但投入控制措施往往会刺激渔业生产者创造新的方法、采取新的技术或工具规避监管,最大限度提高捕捞量。
为了在技术层面对渔具渔法加以限制,《渔业法》要求禁止使用或者限制使用的渔具和捕捞方法由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规定。2014年,农业部完善了海洋捕捞网具最小网目尺寸和禁用渔具目录,从多环节对违规渔具进行清理整治。据不完全统计,2015年沿海各省共开展执法行动1万多次,出动执法人员12万人次,清理违规渔具近26万张(顶),使禁用渔具和“绝户网”蔓延态势得到一定程度遏制。[6](P70)然而,渔业生产者逃避监管的行为带来了巨大的执法压力。海洋执法相对陆地困难更多,执法成本更高,茫茫大海违法行为不易被发现、取证难,执法装备不足,人员编制有限等原因导致执法难成为海洋渔业管理的瓶颈。[7]
(二)捕捞限额制度的困境
限额制度是限制捕捞渔获量的产出控制措施。《渔业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家根据捕捞量低于渔业资源增长量的原则,确定渔业资源的总可捕捞量,实行捕捞限额制度。……捕捞限额总量由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确定,报国务院批准后逐级分解下达。”一般来说,通过在特定水域范围设定总可捕捞量,使鱼类种群维持在可繁衍水平,在不损害其繁殖潜力的情况下确定限额,从而支撑持续的产出。当产量低于最低种群规模的阈值时,则重新调整限额。但自上而下的逐级分解下达方式难以克服限额制度的不确定性。
首先,总可捕捞量所依据的种群评估具有不确定性。经验和模拟分析表明,即使有成本高昂的监测设备,评估方法有时也可能产生50%以上的错误概率,研究调查中得到的大量数据是不可用的。[8](P95)其次,对捕捞量的控制具有不确定性。即使具备充分的科学依据,监管的有效性也难以达到预期的控制,因为准确控制实际捕捞量具有相当大的难度。最后,在限额分配和执行上的不确定性。沿海各地方政府出于各自的经济利益考虑往往在捕捞限额的分配上难以达成一致,或者在执行上无法落实到位。这些因素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该制度的实施。
(三)伏季休渔制度的困境
海洋伏季休渔制度自1995年在我国管辖海域全面实施,是养护海洋生物资源的一项重要制度。《渔业法》第三十条规定,“禁止在禁渔区、禁渔期进行捕捞”。国务院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有权力采取禁渔措施。2017年1月农业部发布《关于调整海洋伏季休渔制度的通告》,5月全国海洋伏季休渔专项执法行动启动会在浙江宁波、辽宁大连和海南三亚同步举行。这标志着休渔时间更长、被纳入休渔范围的渔船更多、监管力度更大的海洋伏季休渔新制度首次开始实施。[9]
实施伏季休渔制度的目的是要给每年夏季来到浅海产卵的海洋鱼类一个喘息的机会。但鱼类的产卵时间不尽相同,“一刀切”的做法不见得是最合理的。更糟糕的是,休渔期间积蓄的捕捞力量在休渔期结束后会立刻释放出来,据全国海洋捕捞动态采集网络监测数据结果,2015年休渔期结束后,9月份全国海洋捕捞总产量为近5年同期最高,同比增长15.86%,[6](P52)休渔制度产生的积极效果在休渔期结束后不长的时间内迅速消耗殆尽。
(四)原因分析
1986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六届十四次会议在《<渔业法草案>审议结果报告》中指出,“我国近海渔业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应当合理安排捕捞力量”。三十多年过去了,我国海洋渔业资源持续衰退的局面并未得到有效扭转,甚至出现了水域荒漠化现象。我国海洋渔业法律制度面临严峻的现实困境。究其原因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点。
1、以管制相对人为主,政府行为约束不足。管制方式严重依赖政府,行政机关与监管对象之间是控制与被控制关系。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看,政府集体决策者与单独的个人并无二致,公共决策和执行不无例外地反映出个人的偏好和意愿。行政机关作为决策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其行为同样受到自身利益支配。由于这些利益往往与资源的管理绩效无关,这些监管者并不总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相反却是为其正在试图加以控制的利益服务,转而偏向特定利益集团,即所谓的“管制俘虏”。实践中,一些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在部门利益和地方利益的驱动下,出卖海域、滩涂使用权,围海、占海,侵害渔民利益的案例并不少见。[10](P324-403)地方政府决策和执行过程中有指向性的偏差,直接影响到渔业资源的实际监管效果。
2、单向度的管制,未考虑本地情势。自上而下的决策和实施,缺乏沟通与交流,渔业生产者被动地接受行政机关管制,未能满足其参与决策和实施的意愿,一方面导致相关决策及其执行的合理性不足,另一方面造成守法的内生动力不足,摩擦不断。渔业生产者作为理性的个体自然知道采用“绝户网”捕捞幼鱼不可持续,但仍会尽力捕捞。这是因为,海洋中的鱼对渔民来说是没有价值的,如果他们今天放弃捕捞幼鱼,就不能保证明天这些鱼还是他的。[11]从理论上看,若公共池塘资源是一种生物资源,如渔场或森林,逼近资源单位的极限不仅会产生短期的拥挤效应,而且可能会摧毁资源本身继续生产资源单位的能力。[12](P39)这种“挤出”效应降低了社区建立监督“搭便车”行为和发展社会资本以战胜资源保护困境的能力。[13](P8-9)在缺乏促使渔业生产者以其特定知识、由下而上参与决策程序的激励的情况下,外部监管者无法充分理解他们的具体动机而不能设计出有效的规则。虽然立法机关制定了大量、复杂的法律法规,但却不能不面临难以理解、难以落实的窘境。
3、“运动式”执法优先,自组织管理阙如。采用急风骤雨式的统一执法行动往往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使违法行为有所收敛。然而,海洋渔业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行政机关不仅需要适应变化的环境和发展的技术,而且需要面对大量的中小监管对象、层出不穷的规避行为以及不同的地方实际和问题。由于假定渔业生产者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对资源不负责任的理性经济主体,对海洋渔业社区、合作社等具有内部管理功能的渔业生产者组织重视不足,[14]虽然行政机关造就了日益庞大的管制机器,但“一刀切”的管控方式,无法填补管制漏洞,无助于投机的冒险行为,难以掩盖行政管制的疲态。同时大范围的执法行动也提高了执法成本。因此,不是解决海洋渔业法律制度困境的长效机制。
海洋渔业资源的保护和利用涉及多方主体之间的博弈。如果缺乏有效的制度安排,无论是作为监管者的地方政府,还是作为监管对象的渔业生产者,都不会选择采取合作行动,从而陷入多方面、多维度的“囚徒困境”。其结果就是,我国海洋渔业正经历着历史上最严重的衰退,不少近海渔场已经被彻底破坏,短期内很难恢复。这迫使我们必须考虑新的治理方法或制度安排,以保障各方主体之间相互协作和制约的互动关系为出发点,使海洋渔业资源得到养护和合理利用。
三、迈向合作治理的海洋渔业法律制度:从理论到实践的考察
私益与公共物品之间的矛盾导致市场与政府都面临着“失灵”的风险。20世纪80年代国际社会逐渐兴起的治理模式试图在以国家为基础、自上而下的管制和单纯依赖以市场为基础的规范之间,在集权化命令与控制管制和个人契约自由之间,构设第三条道路。其目标在于超越管制和解除管制、法律指令和自发的市场行为这种概念上的二分法。[15]治理模式的理论前提是,相互依赖的个体同时受到经济和社会动机影响,能够意识到自己所处的资源困境和不确定环境,可以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依靠科学和传统知识建立合作规则,通过群体生活取得持久的共同利益。这也是之所以“无论国家还是市场,在使个人以长期的、建设性的方式使用自然资源系统方面,都未取得成功;而许多社群的人民借助既不同于国家也不同于市场的制度安排,却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对某些资源系统成功地实行了适度治理”[12](P1)的逻辑起点。从这一起点出发,海洋渔业法律制度的治理模式通过形成保障各方主体合作治理的规则,为破解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失灵”提供了方向和路径。
(一)多元的治理主体为制度构建提供了基础
海洋渔业问题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决定了没有一个主体可以单独解决,需要多元主体承担起保护和利用的责任。多元主体之间双层或多层的嵌套结构为治理模式的构建提供了基础。在确定的渔业资源边界内,由行政机关、从事捕捞的个人和社区等不同主体形成互补的双层或多层嵌套结构。各单元都拥有一定的自治权,平行的小单元可以嵌入更大的单元系统,在相互支持、相互监督的过程中取得平衡。行政机关处于嵌套结构的最外层,搭建起由专业人士和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决策平台,提供“交互性守法”的制度环境,承担着协调者、实施者和监督者的职责。在行政机关之外,还有作出和实施决策的正式与非正式主体,以及为实施决策而建立的正式与非正式结构。从事捕捞作业的个人和社区以合作的方式、分担的责任共同达成政策目标,他们既是资源的使用者、也是监督者和责任者。一方面利用嵌入到当地生活的传统知识,确定合理的捕捞时间、空间和方法;另一方面协商制定本地化的规则,排除外来捕鱼者和本地违约者,这是在社区管理的近海渔业中发现的最普遍的机制之一。[16]
在实践中,美国《马格努斯—史蒂文斯渔业保护管理法》(以下简称“《渔业保护管理法》”)经过两次重大修订,确立了一个由多元主体组成的完整的治理架构。其核心是通过建立8个半官方性质的区域渔业管理委员会,将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主体相分离,[17]这使得美国的渔业管理由政府管理为主转向由政府和利益相关者共同协商、共同参与的模式。海洋渔业管理计划的制定权在一定程度上赋予了渔业生产者代表和熟悉当地情况的专家。商务部长负责程序性审查和实施渔业管理计划,国家海洋渔业局和海岸警卫队负责具体的监督管理和执法。公众监督主要体现在参与相关政策制定、听证、对行政部门提起司法审查。法院不仅仅可以对执法行为的程序和实体的合法性进行监督,还可依据法律规定进行司法审查。多元主体之间的相互合作与制约保证了治理架构的稳定。
(二)双向的互动关系为决策制定提供了平台
单向度的政府行为不是治理,治理的核心在于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间的互动。这种互动是持续的、结构性的,某种程度上是制度化的;公私主体之间的区分是模糊的,界限是不固定和相互交叉的;政府行为不是单向度地施加于非政府主体,而是双向度地与之共同实施。[18]决策过程也由自上而下、命令加控制转变为源于并适应于地方情势的反思性路径,演化出适应不同生态条件和成本利润分配习俗的本地化规则。同时,在互动的过程中,经由制度化的协商和差异化的选择也改善了各方的对抗性关系,增强了合规的内生动力。
从决策方式上看,集体参与决策制度是成功的渔业管理制度的先决条件和合理依据。[19]《渔业保护管理法》要求区域渔业管理委员会采用利益相关者和渔业科学家参与的集体决策程序,在充分考虑对渔业社区影响的基础上,为每个渔场制定渔业管理计划,评估和说明渔业的当前和可能的未来状况、最大可持续产量和最适产量,并在计划中确定年度捕捞限量、实施细则或年度规范要求,以严格的问责措施确保渔场内不发生过度捕捞。委员会的每次常规会议都应当在《联邦登记》上提前公告,并向公众开放。委员会还需设立由专家组成的科学与统计委员会和由渔业利益相关者组成的咨询委员会与咨询小组,分别负责提供科学建议和收集各方意见。在渔业管理计划的编制过程中,委员会应在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召开听证会,以便听取所有利益相关者关于计划编制和修订的意见。一旦形成计划的终稿,还应对未采纳的意见作出解释和说明。商务部长在收到计划后应在《联邦登记》上公告,接受公众评论。通过这样的方式,一方面增强了决策的科学基础,另一方面整合了利益相关者的传统知识和诉求,构建起各方主体双向互动的治理模式。
在限制准入特权的分配上,《渔业保护管理法》要求区域渔业管理委员会制定相应程序,确保初始分配的公平和公正,防止特权不公平地集中在一些人手中。限制准入特权方案组合了投入和产出限制,以捕捞配额和可转让配额的方式将渔场的总捕捞量份额分配给社区和满足资格要求的渔业生产者。渔场内每种受管制鱼种的捕捞总量在社区或“部门”间进行分配,每位渔民在该部门的捕捞份额中取得一定比例或个人可转让配额,可以在一个年度内全部或部分使用该配额,也可出售给部门内部和部门之间的其他渔民,这就提高了经营灵活性。[20]通过建立双向的互动关系,越来越多的社区和个人承担起海洋渔业资源保护和利用的责任。
(三)渐进的分级责任为合规监督提供了保证
海洋的广阔性和数量众多的分散渔业生产者,决定了监督渔业法律的遵守是一项艰巨的工作。只有对各种潜在的违法行为都设定了适当的责任,监督机制才可能取得成功。以渔业社区为基础的嵌套结构,可以根据违规的内容和严重程度,确立渐进的分级责任,为制度的实施提供了保证。一方面借助于社区的凝聚力,设定自愿遵守的预期和规则,以内部的自我监督和制裁方式,避免渔业生产者“搭便车”或其他机会主义行为的诱惑;另一方面由行政机关追究社区和渔业生产者的法律责任,以社区为单位改变分散的监管局面,解决行政机关在面对纷繁多样的执法对象和复杂多变的违法手段时出现的执法监督乏力问题。
从合规保障上看,历史上美国国家海洋渔业局主要依靠人工观察员和执法人员,目前更多地依靠技术手段和社区管理。渔船和鱼商强制性报告义务已成为收集执法和管理所需信息的重要途径。渔船定期向国家海洋渔业局提交船舶航行报告或日志,报告捕捞量数据,经销商同样需要提交报告。渔业社区管理者审核和比较自行报告的捕捞量和鱼商数据,通过纳入包括关闭渔场或渔区和减少允许的捕捞总量在内的问责措施使渔业管理计划“有效执行”年度捕捞限量,以防止超过年度捕捞限量并处理年度捕捞限量被超过的情况。对于违反法律者,采取从警告和民事处罚,到吊销许可证和刑事责任等多种处罚措施。一般的民事处罚金额不得超过10万美元,持续的违法行为将施以按日计罚;妨碍执法检查、攻击执法人员、提供虚假信息者,将处以刑事罚款或监禁。通过自行守法和外部强制的结合,美国以有限的执法人员实现了对海洋渔业的“善治”。
综上所述,海洋渔业法律制度的治理模式以参与性和灵活性为主要特征,通过多元主体间各层面的互动,破解管制模式的现实困境。美国与许多其他国家一样,有太多的渔民争相捕捞太少的渔业资源。在过度捕捞严重、渔业资源日益枯竭的背景下,《渔业保护管理法》确立起互动的、多维的治理体系,自2011年以来,近90%的渔场都保持着低于年捕捞限额的产量水平。[21]美国的经验告诉我们,构建海洋渔业法律制度治理模式的关键在于,如何保证各方主体在相关决策、实施和监督过程中的协作和监督,如何保证一个地方和社群中互相依赖的渔业生产者实现真正有效的自我组织和治理。
四、构建我国海洋渔业法律制度的合作治理模式
政府管制模式的失灵直接推动了由开放的公共管理与广泛的公共参与整合而成的治理模式的兴起,这代表了通过分散权力来集中民意的公域之治的发展趋势,其典型特征是开放性和双向度,解构自上而下单向度输送规制指令的封闭管道,建构各类行政法主体通过平等理性商谈获得共识的开放场域。[22]因此,我们应当从多元主体合作治理的视角出发,破解我国海洋渔业法律制度的困境。以此为突破口,《渔业法》的修订应当注重三个方面的制度设计。
(一)明确海洋渔业相关主体的法律地位
要构建海洋渔业法律制度的合作治理模式,必须先明确相关主体在渔业法律关系中的地位。一是以权力下放和地方负责为原则,规定农业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的职能和责任,将提供资源以及决策协调、实施、监督作为其重要的工作职责。二是搭建决策平台,规定由农业部和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渔业行政主管部门设立渔业专家咨询委员会和公众咨询委员会负责提供专门知识和公众意见,明确其人员组成、议事规则和工作职责。三是弥补海洋渔业生产者以个体为主、分散性强、组织性弱的缺陷,承认渔业社区等主体的法律地位,将其界定为在确定的资源边界内主要依赖或大量从事渔业资源的捕捞或加工以满足社会和经济需要的社区,规定社区(或合作社)的治理结构和成员的权利、义务,内化渔业生产者的正、负外部性。
(二)完善海洋渔业相关决策的科学和民主机制
决策是现代行政活动的起点。要提升海洋渔业相关决策的质量,需要完善科学和民主机制,将专门知识与本地经验结合起来。通过多元主体之间的有效互动,共同确定准入制度、捕捞的规则、时机和强度,适应生态条件的改变和社群的需要及时作出改变。对于行政机关,为克服渔业领域可能出现的“政府失灵”,应当将《渔业法》中的“监督管理”改为“包括监督、指导、协调和服务在内的综合管理”,以行政程序和信息公开的设计约束管制权力,政府责任由此转变为以回应公众、满足公众要求为核心。对于咨询委员会,应当广泛纳入专业人士、社区和渔业生产者代表、利益相关者等主体,并授权其实质性参与渔业生产者准入、年度捕捞限额及其分配等决策、实施和评估的过程,以结构化的机制确保利益相关者能够就其关切事项提出意见和建议。对于渔业社区,授权其在特定区域内使用、分配和管理渔业资源,并承担主要的养护责任,同时基于个人捕捞配额和个人可转让配额,形成渔业生产者负责任行为的激励机制。
决策的质量直接决定了政策的实施效果。治理模式的一个创新性制度设计是以多元主体的决策互动机制,调和多方利益。如前所述,行政决策的主体单一、方式僵化,是我国渔业法律制度的薄弱之处。由受影响民众借由适当管道参与决策过程,可以调和利益冲突、促进民主政治的发展、以及改善“政府”的决策品质。[23](P94)在治理模式之下,渔业社区和渔业生产者参与决策的过程是协商的过程,也是学习与分享的过程。他们具有丰富的本地经验,知道在一个捕鱼区可以用60多种捕鱼方法,有40多个有特征的暗礁和400种鱼类以及鱼类迁徙的路线和不同鱼类的产卵行为。[3](P606)他们既是利益主体,也是认识主体,通过倾听与分享彼此的观点以修正自己的认识,在协商中不断的交换、学习、适应和改进,寻求与凝聚共识,使方案最大限度照顾各方利益,藉以提高决策的合法性与执行的有效性。
(三)健全基于自行守法和外部强制的分级监督机制
渔业法律的治理模式并不意味着放弃监督,有效的监督保证了责任的承担。为确保决策的落实和责任的承担,需要综合运用基于自行守法和外部强制的分级监督机制。一是在渔业社区内部制定共同的行为规范。通过完善渔船渔捞日志填报、交易数据报告、采集和检查统计制度,推进自行报告、自愿数据收集并逐步电子化;实施捕捞限额预警制度,由社区采集数据信息、统计分析产量,在接近捕捞限额时发出预警,将责任内化为守法的意识。二是由行政机关对违法社区或个人施加的惩罚和制裁。具体包括:通过关闭渔场或停止捕捞,以及减少允许的捕捞限额等方式,对超过年度捕捞限量的社区实施严格的问责;使用多种方式监控渔船,开展海上和渔港检查,根据违法程度的不同,实施口头或书面警告、行政处罚直至追究刑事责任。
五、结语
责任政府与行政效率之间具有内在的关系。一个有效率的政府才能切实履行政府责任,而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才能有效率。高效的现代行政部门既需要具备完善的行政管制措施,也需要具备充分的协商与合作手段。一方面是渔业生产者的生计,另一方面是渔业资源的耗竭。除了自然所带来的挑战之外,监管方面的挑战来自于社会、经济和体制结构。行政机关肩负着一项艰巨而又重要的任务,即平衡当前和未来渔业生产者的需求,以及公众的长期利益。旨在维持生产的管制活动常常会影响到渔业生产者的生计和沿海社区的稳定,从而产生压力和摩擦。堵而抑之,不如疏而导之。我国近海渔业资源状况的改善亟需建立健全法律的治理模式。治理模式之下,政府不再是“全能型选手”,而是以更加灵活的方式,藉由各方主体的协商与合作,使决策更多地基于共识和地方情势,使守法和执法更主动、更有效,实现单一中心“监管”向多中心“治理”的转型,进而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1] 国务院关于印发全国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的通知[EB/OL].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5-08/20/content_10107.htm, 2015-08-20/2017-08-12.
[2] (荷兰)格劳秀斯著,宇川译.海洋自由论[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
[3] (瑞典)托马斯·思德纳著,张蔚文,黄祖辉译.环境与自然资源管理的政策工具[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4] R.Quentin Grafton, Ray Hilborn, Dale Squires, et al. Handbook of Marine Fisheries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5] Timothy F. Malloy. Regulation,Compliance and the Firm[J]. Temple Law Review,2003,(3):451-531.
[6] 农业部渔业渔政局.中国渔业年鉴[M].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16.
[7] 黄进.广东探索海洋渔业保护联合执法机制[N].南方日报,2016-12-14(A16).
[8]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Improving Fish Stock Assessments[M].Washington,D C:National Academy Press,1998.
[9] 严冰,田佩雯. 中国开启“最严休渔期”[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7-05-05(2).
[10] 孙宪忠.中国渔业权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6.
[11] H. Scott Gordon. The Economic Theory of a Common-Property Resoure:The fishery[J].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ic,1954,(62):124-142.
[12] (美国)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著,余逊达,陈旭东译. 公共治理之道[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13] (美国)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著,郭冠清译.公共资源的未来:超越市场失灵和政府管制[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14] 李延敏,崔红,宋磊. 海洋渔业专业合作社的政府扶持及优化——债务融资能力的视角[J].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5):8-12.
[15] Edward L. Rubin. Law and the Methodology of Law[J]. Wis. Law Review,1997,(1997):521-565.
[16] Michael Cox,Gwen Arnold, Sergio Villamayor Tomás. A review of design principles for community-based natural resource management[J]. Ecology and Society,2010,(4):38.
[17] Scott C. Matulich,Richard H. Seamon,Monica Roth,et al. Policy Formulation versus Policy Implementation under the Magnuson-Stevens Fishery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Act: Crab Rationalization[J]. B. C. Envtl. Aff. L. Rev.,2007,(34):239-272.
[18] Daniel J. Fiorino. Rethinking Environmental Regulation: Perspectives on Law and Governance[J]. Harv. Envtl. Law Review. 1999,(23):441-465.
[19] 张涵,刘曙光. 欧盟参与式渔业管理制度发展概况、类型及特征研究[J].中国渔业经济,2017,(3):34-41.
[20] Andrew M. Scheld, Christopher M. Anderson. Market effects of catch share management: the case of New England multispecies groundfish[J]. ICES Journal of Marine Science,2014,(7):1835-1845.
[21] Magnuson-Stevens Fishery Conservation and Management Act[EB/OL]. http://www.nmfs.noaa.gov/sfa/laws_policies/msa/index.html,2017-10-25.
[22] 罗豪才,宋功德.公域之治的转型——对公共治理与公法互动关系的一种透视[J]. 中国法学,2005,(5):3-23.
[23] 叶俊荣.环境政策与法律[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