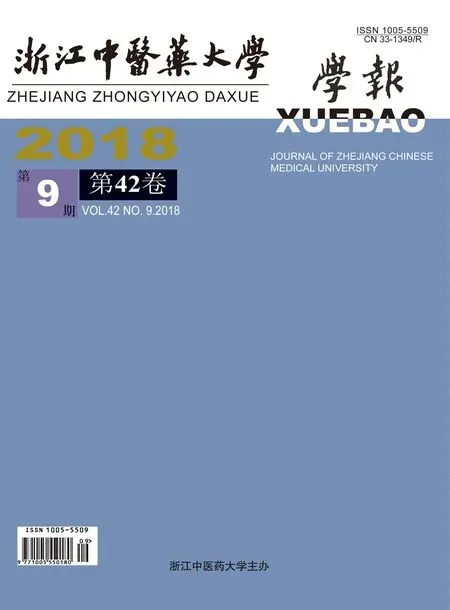“郁乃痤”之浅见
2018-01-14赵杭赵东瑞
赵杭赵东瑞
1.浙江中医药大学滨江学院 杭州 310053 2.温州市中医院
痤疮俗称“青春痘”“暗疮”,中医称“粉刺”“酒刺”,主要好发于青少年,是临床上常见的多发性损容性慢性炎症,以好发于面部的粉刺、丘疹、脓疱、结节等多形性皮损为特点[1]。目前,现代医学多采用抗生素、维A酸、抗雄激素药物、糖皮质激素等手段治疗,联合应用光照治疗,取得了较好疗效,但维A酸、糖皮质激素等药物长期使用会产生不良反应,从而影响患者治疗的依从性。近年来中医药治疗痤疮的研究逐步深入,传统中医药为痤疮治疗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手段。本文拟从“阳郁”的角度分析痤疮病因病机,并依此提出治疗见解。
1 痤疮之文献记载
祖国医学在很早就有关于痤疮的记载。《素问·生气通天论》篇曰:“汗出见湿,乃生痤疿。高梁之变,足生大丁。受如持虚,劳汗当风,寒薄为皶,郁乃痤。”这句话应该是最早对痤疮病因病机及症状的描述。今为其中一字——“郁乃痤”之“郁”浅谈痤疮的因证论治。“郁”通“鬱”,《说文解字》曰,“木丛生者,茂林也”[2],又曰“郁,积也”,表明“郁”为“积聚、凝滞”之意。纵观上下文,《素问·生气通天论》是《内经》中关于病因病机的学说,原文所论为“阳气者,烦劳则张……”,故此一“郁”字,当取“凝滞”之意。
历代医家对“郁乃痤”的解释有很多。王冰[3]在《黄帝内经素问》中注释:“皶刺长于皮中,形如米,或如针,久者上黑,长一分,余色白,英而瘦,于玄府中,俗曰粉刺,解表已,玄府谓汗空也。痤,谓色赤,脂愤内蕴血脓,形小而大,如酸刺枣,或如按豆,此皆阳气内郁所为,待耎而攻之,大甚出之。”马莳[4]在《黄帝内经注证发微》中指出:“凡若此者,皆阳气不固使然也。”王洪图[5]在《王洪图内经讲稿》中也强调:“阳气受伤,或卫气被郁。”张介宾曰:“形劳汗出,坐卧当风,寒气薄之,液凝之皶,即粉刺也,若郁而稍大,乃成小疖,是名曰痤。”[6]
2 痤疮之分型论治
中医外科学教科书中将痤疮分三型论治:肺经风热型,病在上焦,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宜疏风清肺,予枇杷清肺饮加减;肠胃湿热型,病在中焦,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宜清热除湿解毒,予茵陈蒿汤加减;痰湿瘀滞型,病在下焦,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宜除湿化痰、活血散结,予二陈汤合桃红四物汤加减[7]。所用方药多具有清热祛湿之功效,以表证、阳证辨证治疗,清热除湿解毒之剂为多,多为苦寒,久服易伤及脾胃之阳,致寒湿内生,长期不愈者可出现寒、湿、瘀互结之象。
3 阳郁与痤疮病机
综上可知,痤疮发病,历代医家多认为因“阳气被郁”所致,“阳郁”可解释导致痤疮的不同证型,病机大致可解读为以下几个方面:(1)阳气被郁,郁而化热,热性炎上,易犯上焦,风为百病之长,发于上者,易与风邪合而为病,而致肺经风热之证。(2)阳气被郁,不能外达肌肤,卫外之气失充,难以御寒,致寒邪侵袭,寒性凝滞,易致气血凝结,积聚不散,故有痤疮患者出现形寒、肢冷、皮损出现结节难消之症。(3)阳气被郁,脾阳被困,不能化湿,致湿阻中焦,蕴而化热,而出现湿热内蕴之症。如痤疮以口周居多,反复难愈,舌红苔黄腻等。(4)脾为化痰之源,阳气被郁,脾失运化,致痰湿内阻,上泛于面,出现囊肿、结节等症。(5)久病必虚,久病必瘀,阳郁日久,气行不畅则致气滞血瘀,出现色素沉着、瘢痕、舌暗红或绛、苔少、脉沉涩等气滞血瘀之象。综观上述5种证候,与原先阐述的痤疮证型不外乎肺、脾、肾三脏,也不外乎上、中、下三焦,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多数医者治疗痤疮常用清、消等下利之法,短期之内确有功效,但治后痤疮往往容易复发。受《内经》“郁乃痤”之启示,近年来笔者跟随老师在治疗痤疮时,发现部分患者痤疮反复发作,经久不愈,出现瘢痕、结节、色素沉着等继发性皮损。这些患者往往自觉大便粘滞不爽,素食油腻肥甘、辛辣之物,或熬夜通宵达旦,以致形成多痰多湿之体;或久病不愈,素体阳虚,自觉形寒肢冷、观其舌淡苔白、脉沉迟,此类患者均可适当予以温阳散寒、行气解郁之治法,佐以清热解毒、健脾利湿、活血化瘀,往往能取得较好疗效。
4 病案举隅
余某某,女,22岁,2017年11月25日初诊。面部红色丘疹、脓疱反复5年,皮疹此起彼伏,以丘疹、脓疱为主,愈后留色素沉着,胸、背部亦有类似皮疹,伴神疲乏力、形寒肢冷、便溏。追问病史,患者平素喜食冷饮甜食,在外院多处诊治,均予以抗生素、维生素或清热解毒类中药,外用药膏多达十余种,疗效不佳,或偶有改善,稍有饮食、睡眠不节即复发。患者舌淡苔白略腻,边有齿印,脉濡细。中医辨为粉刺,证属寒湿蕴结、卫阳郁滞。故治拟温阳健脾,佐清热化湿。方用:麻黄 6g,附子 3g,细辛 3g,黄芩 10g,炒白术 15g,炒山药 15g,茯苓 15g,生米仁 30g,黄连 3g,木香 10g,蒲公英30g,连翘10g,生甘草3g。服药3d,皮疹反增多,出现细小脓疱,但脓疱周围皮肤为暗红色,而不是鲜红色,嘱稍安勿躁,继续服用。
2017年12月2日复诊。无新发皮疹,所有脓疱均在原有的丘疹、粉刺基础上发生,患者乏力、肢冷均好转,舌淡红苔薄腻,脉趋平稳,原方去附子、细辛,加珍珠母30g、白芷10g。
2017年12月10日三诊。原脓疱结痂脱落,留暗红色素沉着,少有新发皮疹,原方再去麻黄、黄连、木香,加党参15g、丹参15g。再服两周后,各症基本消失,舌脉渐趋正常。
按语:患者素食冷饮、苦寒药物损伤脾阳,致阳气被郁,不能升发,不能化湿,致湿阻中焦,蕴而化热,湿热泛于肌肤而致皮疹,湿性缠绵,致病证反复,故治拟温阳健脾,佐清热化湿。服药3d,皮疹反增多,出现细小脓疱,但脓疱周围皮肤为暗红色,而不是鲜红色,此应为阳气升发、托毒外出之象。温阳之方,当以仲景之方为首,仲景之方,又当以麻黄细辛附子汤为宜。此方主治阳虚感寒之证,有助阳解表之功效。《伤寒论》谓之:“少阴病始得之,反发热,脉沉者,麻黄细辛附子汤主之。”[8]方中以麻黄为君,取麻黄之辛温,发汗解表散寒;臣以制附子,取其大辛大热,温补阳气,助麻黄鼓邪外出。二药相伍,无伤阳之弊,相辅相成。细辛助麻黄解表,协附子温里;山药、白术运脾化湿消积;薏苡仁、茯苓健脾祛湿、引热下行;黄芩、黄连、蒲公英清热燥湿;木香与黄连,助其行气消滞;连翘为“疮家圣药”,均为佐药之用。甘草调和诸药。诸药配伍,共奏解表散寒、化湿祛瘀之妙。二诊时,患者乏力、肢冷均好转,去附子、细辛,加珍珠母、白芷。三诊方再去麻黄、黄连、木香,加党参、丹参以巩固。
5 结语
本文依据《内经》之“郁乃痤”理论,从阳郁的角度阐述了痤疮的发病机理,强调临证时除教材中提出的分型论治以外,需关注患者的阳气。案例诊治对笔者颇有启发。若患者素来贪凉饮冷,过用苦寒之药,均可伤及脾阳,以至阳气郁结,导致病情易反复发作,缠绵不愈,表现为形寒肢冷伴神疲乏力,大便溏泄,舌淡胖边有齿痕,脉细濡、舌淡黯,脉沉细无力。故痤疮之治,并非一味应用寒凉之物,宜灵活辨证,仔细应对,方有满意疗效。与此同时,预防痤疮,平素应注重顾护自身阳气,如夏日高温时不过食寒凉之品,进出室内外温差不宜过大,运动后不应立即冲凉,保持心情舒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