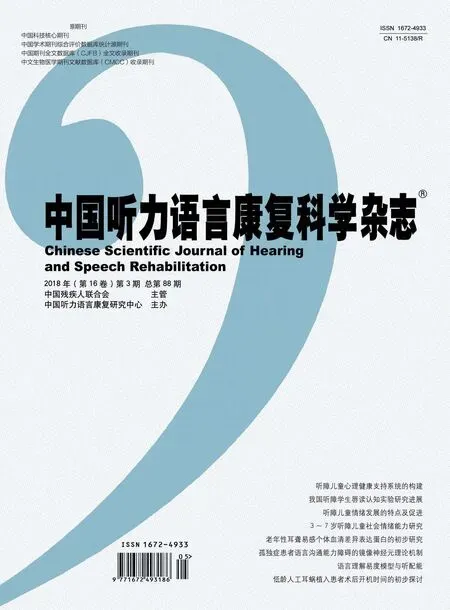听障儿童情绪发展的特点及促进
2018-01-13伍新春赵英
伍新春 赵英
情绪是一种重要的心理现象,对个体的生存发展、人际间的信息传递等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早期未习得语言的婴幼儿,就能够通过观察成人的情绪了解自己所处的环境状态,也可以通过表达自己的情绪使自身的生理或心理需求得以满足。积极良好的情绪可提升个体认知及行为活动的效果,而消极不良的情绪则会产生负面影响。相对于成人而言,儿童的情绪可能更不稳定。听障儿童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由于其听觉刺激的输入及言语信息的输出都存在困难,无法与其他人顺利地进行沟通,更容易封闭自己,产生情绪困扰。因此,了解听障儿童情绪的特点及相关影响因素,采取相应的干预措施,帮助听障儿童培养良好的情绪就显得十分必要。
1 听障儿童情绪发展的特点
部分或完全的听力受损直接影响着听障儿童的日常生活。著名作家、教育家海伦.凯勒曾说过:“盲隔绝了人与物,聋隔绝了人与人。”虽然人工耳蜗及助听器等设备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听障儿童接收与处理听觉信息,但由于生理年龄和医学手段的限制,先天聋的个体必定会经历一段时间的听力损失。同时,由于助听设备对听力言语康复效果差异较大等因素,听障儿童并不能完全像健听儿童一样,充分地与外界交流和互动。由于人际交往、社会互动的匮乏,听力障碍的儿童更容易陷入悲伤、冲动、易怒等负面情绪,遇到不利情境时,则可能会产生较大的情绪波动[1]。相关实证研究从心理健康的角度出发,采用儿童行为量表(child behavior checklist,CBCL)、法兰克福自我概念量表(Frankfurt self-concept scales,FKSI)等工具对听障儿童的情绪问题进行了评估[2,3]。与预期相一致,听障儿童的自尊水平较低,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感到被同伴接纳,但还是会经常体验到孤独感与焦虑感[3,4]。
袁存梅等[5]以61名学前听障幼儿为对象,通过问卷调查法、观察法以及实验法对其情绪和认知表现进行了分析,结果发现,被试的情绪都会影响其认知发展,积极的情绪可以保证认知活动的顺利进行,低落的情绪则会降低认知效果。Rieffe[6]的研究表明,健听儿童缓解消极情绪的能力显著好于听力障碍的儿童,当消极情绪产生时,听障儿童所采取的调节策略并不十分有效。因此,了解听障儿童情绪发展的影响因素,并在此基础上制订相应的干预措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2 听障儿童情绪发展的影响因素
听障儿童的情绪发展除受到自身特征的影响外,也受到外界环境系统的综合影响。本文从语言技能、情绪理解及心理理论三方面的个体特征,家庭、学校以及社会三个环境系统出发,分析听障儿童情绪的影响因素。
2.1 个体特征因素
2.1.1 语言技能 健听儿童可以接触到各种各样的声音刺激,持续的听觉信号输入使其语音加工能力渐渐发展,进而习得语言。而听觉通道受损的听障儿童感受不到声音,长时间听觉经验的缺失或不足直接影响听力障碍人群的语言发展。语言是信息传递的载体。由于语言发展的滞后,一方面,听障儿童无法有效地向他人表达自己的想法,诸多需求难以得到诉说,容易陷入不良情绪之中,且无法通过向他人倾诉予以排解。另一方面,语言的滞后使得听障儿童的思维和认知发展受限,难以对社会刺激做出合适的反应,不能很好地理解社会互动的过程,一旦自身需求没有得到满足,就容易产生情绪问题[7]。
2.1.2 情绪理解 个体能够监控并区分不同的情绪、正确分析情绪的诱发因素,是有效的情绪调节的必要条件[8]。对情绪的本质、诱因及调节过程的认识能力,即情绪理解[9],可以帮助个体更好地把握人际交往过程,从而促进其个性及社会性的发展。一般而言,出生后的第一年,婴儿就开始对面部表情以及声音中蕴含的情绪意义变得敏感,逐渐发展情绪理解能力。然而,听障儿童的情绪识别能力相对滞后,且不能对情绪的诱发因素做出合理地推测。相关研究表明,当要求听力障碍的儿童判断简单故事中主人公的情绪时,虽然不同年龄组间听障儿童的成绩没有显著差异,但任何年龄组听障儿童的正确率都显著低于同龄健听儿童[10]。Rieffe等[11]给听障儿童呈现消极情绪(如悲伤、愤怒)的诱发情境,之后要求儿童回答故事人物的感受,并追问其情绪产生的原因。结果发现,与同龄健听儿童相比,听障儿童更多地注意到这种不利情境造成的后果,而不理解造成这一后果背后的原因。由此可见,听障儿童很难意识到他人情绪的细微变化,情绪理解能力较差。遇到不利情境时,他们可能更多地产生负面情绪,并且由于不能对相应情绪的诱发因素进行适当分析而出现恶性循环。
2.1.3 心理理论 除情绪理解外,心理理论(theory of mind,ToM)也是儿童社会认知的重要方面[12]。心理理论是指个体基于自己或他人的信念、目的、意图等心理状态,进而理解和解释人类行为及社会情境的认知能力[13]。不论是在家庭、学校还是社会环境中,听障儿童和父母、同伴之间缺乏高质量的互动,其获得心理理论的时间晚于健听儿童。在听障儿童心理理论的研究中,儿童对错误信念的认知是研究者常采用的基本范式,即向儿童呈现一个故事情境,观察儿童是否能够推断出主人公的真实信念。Peterson等[14]首次测查了听障儿童对错误信念的理解能力,发现其错误信念的发展滞后于健听儿童。其他研究也发现了相似的结果[15,16]。由于心理理论的滞后,导致听障儿童在理解他人信念、目的等方面存在偏差,他们更多地以自我为中心,认知发展相对不成熟,从而影响其情绪的形成和发展。
2.2 外界环境因素
2.2.1 家庭 个体从一出生就处在家庭系统中,家庭系统在儿童的身心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父-母-子三者之间的关系以及父母的教养质量直接影响孩子的未来发展。Kwon等[17]的研究表明,父母协同教养的质量会通过母亲的指导影响孩子社会情绪能力。因此,父母的态度、情绪、行为等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听障儿童的情绪发展。根据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如果父母在教养过程中,更多地采取支持、鼓励的态度,耐心温柔地和孩子交流,听障儿童也会进行模仿,采取相似的方式与父母、同伴或者他人沟通交往,表现出稳定、积极乐观的情绪。然而,有些听障儿童父母对孩子的生理缺陷感到愧疚,会对孩子过度保护,过分溺爱孩子;有一些父母则相反,对孩子感到不满,对孩子漠不关心,缺乏应有的关爱。这两种态度都容易导致听障儿童不良情绪的形成。
2.2.2 学校 首先,学校的教育理念渗透在学校生活中。而提及听障儿童的学校教育理念,手语、口语之争则是众多教育者和研究者一直以来争论的热点话题。近年来,一些聋校越来越主张口语教学模式。但是,向口语能力较差的听障儿童强推口语教育,不关注儿童内心的真实感受,容易使其产生自卑、无助等消极情绪[18]。其次,在所有影响儿童发展的学校因素中,教师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有研究表明,教师的情绪状态影响学前听障幼儿的情绪。如果教师精神饱满,幼儿就会表现出积极的情绪,反之则会比较低落[5]。最后,随着融合教育的逐渐开展,越来越多的听障儿童进入主流教育系统,但他们却不得不面对如何与健听儿童建立高质量的同伴关系的难题。Schorr[19]的研究表明,虽然年龄较小的(约5~9岁)听障儿童感到自己受到了同伴的接纳,体验到的孤独感与健听儿童并无差异,但年龄较大的(约9~14岁)听障儿童对自身适当行为的感知水平较低,并且有较高的孤独感。由于听力水平的限制不得不在聋校接受教育的听障儿童,则会因为聋校突出的校园欺凌现象,出现抑郁、感到孤独、成绩下降等问题[21]。
2.2.3 社会 相关政策文件的颁布、无障碍设施的提供、社会对听力障碍群体的态度等,都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听障儿童的情绪。虽然目前倡导营造理解、尊重、关心、帮助残疾人的社会氛围,但听障儿童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会受到歧视。由于听力受损,听障儿童可以享受的教育资源远远少于健听儿童,且未来的就业机会也受到限制。这种不平等会使听障儿童各方面的需求得不到满足,感到自己受到社会的冷落、他人的排挤,不为大家所重视,容易导致不满、悲观等负面情绪的产生。
3 听障儿童情绪发展的干预措施
3.1 了解儿童特点,促进有效的语言交流
听障儿童与健听儿童在各方面的差异,其最根本的原因都可以追溯到听觉通道的受损。听力损失直接导致了儿童言语理解及表达能力的滞后,而语言是信息传递的媒介、思维发展的载体,影响儿童的情绪发展。为此,应该充分了解听障儿童的特点,促进其与他人之间有效地语言交流。坚持“早发现、早干预”原则,对于人工耳蜗植入较早或者残余听力较好的听障儿童,应该重视早期的听力言语评估和康复。而对于听力受损严重且没有任何助听设备的儿童,强行要求其学习口语可能会使他们感到受挫、无助,形成不良的情绪。手语的输入对口语并不一定都是阻碍作用,也有可能会缓解早期听力剥夺对其口语发展造成的负面影响[21]。此时,应该鼓励手口并用,保证听障儿童可以与同伴、父母、教师等进行高质量的语言沟通,感受到自己与他人的联结,避免消极情绪的产生。
3.2 训练儿童思维,培养良好的情绪理解
皮亚杰认为,认知发展是比社会性发展更为基础的一个过程,可以从相应的认知发展阶段理解儿童社会性发展的特点。影响听障儿童情绪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思维发展的滞后。思维训练可以借鉴错误信念的研究范式,引导儿童进行假装游戏,并对儿童的反应进行积极反馈。促进儿童心理理论的发展,可以帮助儿童更好地了解他人的动机和意图,维持良性的社会互动,以使其内心情感得以充分交流。同样,儿童情绪理解能力的培养也可以借鉴情绪理解的评估方法,如给儿童呈现面部表情、简短的语句或小故事,之后要求儿童就面部表情或故事主人公的情绪状态、造成这一情绪的原因以及如何调节情绪等做出反应[12]。李娜等[22]曾基于情绪理解的情景故事,自编儿童的情绪理解问卷并设计干预课程,结果证明听障幼儿的内、外部情绪理解水平都有显著提升。家长和教师在日常生活中,可以通过绘本阅读、讲小故事等,引导儿童理解他人的情绪,关注他人的感受有助于儿童对自身情绪的理解和调节。
3.3 调整儿童认知,鼓励合理的情绪表达
帮助听障儿童掌握有效的情绪调节策略有助于儿童积极情绪的形成。Gross在情绪过程模型中提出了认知重评这一情绪调节策略[23],该策略与心理咨询和治疗中的理性情绪疗法理念相似,即通过改变对事情的认知,看到事情不同的一面,从而改变情绪体验。基于这两个理论,当听障儿童遇到不利情境产生消极情绪时,父母和教师可以引导其从其他角度看待问题。此外,表达抑制是Gross提出的另一情绪调节策略,即抑制自己的情绪而非将其表达出来[23],但该策略的有效性以及对听障儿童是否适用值得探讨。可以肯定的是,对于愤怒等极端情绪进行适当的抑制而避免产生不可挽回的后果是必要的。但听障儿童因为沟通交流不便,经常将自己的真实情绪隐藏起来。这时,就应该鼓励他们以合适的方式将情绪表达出来,比如和好朋友交流、写日记、做运动等。
3.4 建立家校合作,发挥各系统积极作用
儿童的情绪不仅受到个体与环境间相互作用的影响,同时也受到各个环境系统间相互作用的影响。听障儿童出生前后的各项听力筛查、康复机构的干预效果等是父母比较熟知的,而他们在校期间的学业情况、人际关系等则是老师比较了解的。因此,建立稳定的家校合作,一方面有助于教师了解听障儿童的生理特征、家庭教养方式等,从而可以有针对性地对儿童的不良情绪进行干预;另一方面,也有助于家长了解儿童的学业压力、人际关系等,在家庭中就相应的问题与儿童进行沟通。听障儿童良好情绪的发展离不开各系统的积极作用,家庭、学校以及社会都有责任参与其中。政策的制定者及社会中的每个个体,都应该努力创造良好的氛围,关心与帮助听障儿童,使他们感到自己被接纳、被尊重,从而拥有更好的身心状态。
[1]纪秀霞.聋生不良情绪的分析[J].吉林教育,2009,(17):116.
[2]Konuk N,Erdogan A,Atik L,et al.Evaluation of behavioral and emotional problems in deaf children by using the child behavior checklis[J].Neurology Psychiatry & Brain Research,2006,13(2):59-64.
[3]Keilmann A,Limberger A,Mann WJ.Psychological and physical well-being in hearing-impaired children[J].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ediatric Otorhinolaryngology,2007,71(11):1747-1752.
[4]Kluwin TN, Stinson MS,Colarossi GM.Social processes and outcomes of in-school contact between deaf and hearing peers[J].Journal of Deaf Studies and Deaf Education,2002,7(3):200-213.
[5]袁存梅,冯蕾.聋幼儿情绪状态对认知发展的影响[J].中国听力语言康复科学杂志,2005,3(5):37-38.
[6]Rieffe C.Awareness and regulation of emotions in deaf children[J].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2012,30(4):477-492.
[7]周姊毓.聋生消极情绪影响因素分析及教育对策[J].南京特教学院学报,2011,(3):19-21.
[8]Rieffe C,Oosterveld P,Miers AC,et al.Emotion awareness and internalizing symptom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The Emotion Awareness Questionnaire revised[J].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2008,45(8):756-761.
[9]Pons F,Harris PL,De Rosnay M.Emotion comprehension between 3 and 11 years:developmental periods and hierarchical organization[J].European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2004,1(2):127-152.
[10]Gray C,Hosie J,Russell P,et al.Attribution of emotions to story characters by severely and profoundly deaf children[J].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and Physical Disabilities,2007,19(2):145-159.
[11]Rieffe C,Terwogt MM,Smit C.Deaf children on the causes of emotions[J].Educational Psychology,2003,23(2):159-168.
[12]Ziv M,Most T,Cohen S.Understanding of emotions and false beliefs among hearing children versus deaf children[J].Journal of Deaf Studies & Deaf Education, 2013,18(2):161-174.
[13]Remmel E,Peters K.Theory of mind and language in children with cochlear implants[J].Journal of Deaf Studies and Deaf Education,2008,14(2):218-236.
[14]Peterson CC,Siegal M.Changing focus on the representational mind:Deaf, autistic and normal children’s concepts of false photos,false drawings and false beliefs[J].British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1998,16(3):301-320.
[15]Schick B,deVilliers P,deVilliers J,et al.Language and theory of mind:A study of deaf children[J].Child Development,2007,78(2):376-396.
[16]Woolfe T, Want SC,Siegal M.Signposts to development:Theory of mind in deaf children[J].Child Development,2002,73(3):768-778.
[17]Kwon KA,Jeon HJ, Elicker J.Links among coparenting quality, parental gentle guidance, and toddlers’social emotional competencies:Testing direct, mediational,and moderational models[J].Journal of Family Studies,2013,19(1):19-34.
[18]黄丽娇.义务教育阶段聋校中的不平等现象研究[D].辽宁师范大学,2014.
[19]Schorr EA.Early cochlear implant experience and emotional functioning during childhood:loneliness in middle and late childhood[J]. Volta Review,2006,106(3):365-379.
[20]王永红.聋生校园欺负行为的特点[J].中国特殊教育,2008,(2):12-17.
[21]Davidson K,Lillo-Martin D,Pichler DC.Spoken English language development among native signing children with cochlear implants[J].Journal of Deaf Studies and Deaf Education,2014,19(2):238-250.
[22]李娜,张福娟,吴季令.听力障碍幼儿情绪理解的干预研究[J].应用心理学,2011,17(2):177-184.
[23]Gross JJ,John OP.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wo emotion regulation processes: implications for affect,relationships,and well-being[J].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2003,85(2):348-3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