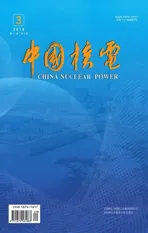核能发展的公众沟通
——专访杜祥琬院士
2018-01-12高树超,王丹
“无核武世界”
《中国核电》:1933年人们用加速器发现了核聚变现象;1938年德国科学家发现了 “铀核裂变”现象,从此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原子核释放的大量能量很快在军事上获得突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 “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号召下,军用与民用同时并举。请您谈谈,核能的发现和利用对世界和我国具有怎样的意义?
杜祥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国家很困难,国际环境很复杂,我们的国力不强,工业、科技都不先进,但是我们必须搞核武器,这是时代背景和国际形势决定的国家战略需求。但是,非常明确,我们研究核的初心是什么?就是要“和平”,为了中国、也是为了世界的和平努力。因此,1964年10月16日,中国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后,提出了中国的基本核战略思想——中国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中国主张全面禁止彻底销毁核武器。这就是“无核武世界”思想最初的提出。虽然2009年4月5日,时任美国总统的奥巴马在演说中表示,美国政府将致力于建立 “无核武世界”。但,建立 “无核武世界”这一思想的 “知识产权”是属于中国的。现在世界许多国家不愿意放弃核武器,因此,中国当下核战略的总体思想是,必须要保持核力量有效性,同时要着力发展核能的和平利用。我国的核战略就是要充分地利用核能,为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发展提供支撑。这一点无论是公众,还是决策者,都应该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在当今世界上,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不能不掌握核科学技术,否则,我们会等同于一个无核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会受到威胁,发展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我国需要核武器来维系和平,但和平利用核能造福人类的主张永远未变,让核能造福中国,造福人类,最终臻于 “无核武世界”。
核起于基础研究,用于军也用于民。所以我国一旦有了机会,就会腾出手来,开始发展自己核事业,把核科学技术用到为人类造福上,这一点自始至终没有变过。核工业产业链很长,从科学技术、工业生产到产业发展,整个产业链的建立是非常必要的,基础研究、技术能力和工业水平都要齐头并进。在中国的电力结构中,核能的占比将逐步扩大,成为绿色、低碳能源的战略选择之一,成为非化石能源的支柱产业,核能、核技术亦必将为我国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核能的和平利用意义非常重大。
“理解”是科普的前提
《中国核电》:核电发展,科普先行。多年来,核行业工作者始终把普及核科技知识,让公众了解核电、走近核电作为重要工作来抓。怎样才能把科普工作做到公众心里去,使其真正发挥作用?请谈谈您的看法。
杜祥琬:要做好核电的公众沟通工作,科普是重要的也是必需的,但光科普是不够的,要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角度想问题。首先,从业者要学会理解公众,了解公众。众所周知,公众对核电安全心存疑问或恐惧。为什么?主要是公众对核电缺乏科学的认识,三次核事故又加重了心理阴影,放大了人们对核电安全的质疑和担心。找到原因,我们就能在公众沟通上对症下药,通过切实有效的科普,让公众对核有科学和理性认识,对于核事故有深入的了解,这样就能减轻甚至消除公众对核电的恐惧。其次,理解是相互的,公众也要理解核行业工作者。任何工程科技领域的创新和发展都不可能一帆风顺,总是伴随着代价和牺牲。比如航空、航天领域,现在发展日新月异,但有不少人为之奋斗终生,甚至有先行者为成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对核能的认识和利用历史并不算久远,经验还不算足够丰富。人类科技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核电的发展和其他领域的科技一样,也有一个产生、发育乃至成熟的过程,要驯服核能,让之为人类造福,失败或痛苦也是难免的,要让公众理解,其实我们做每一件事情都是谨小慎微,自始至终把安全作为核心来抓。因此要学会理解核工作者,把眼光放长远。
在理解的基础上做科普,我有三点想法。一是尽量用科学数据说话,数据不会说谎,能客观科学地说明核电的安全系数很高,但在展示数据的时候,一定要用深入浅出的语言让公众听懂。比如向公众普及核电的安全水平的事故概率为10-7,它表明我国核电安全标准很高,但是这样科普显然是不够的。“不怕一万只怕万一”,10-7在公众看来并不是一个万全的数字,他们会担心“千万分之一”如果发生了呢?所以还要回答他们真正担心的问题。既要说清楚核电安全标准将核事故概率降到了最低;更要说明,即便 “千万分之一”发生,我们也完全有能力做到 “事故后果可控”,不会对公众、环境和社会产生实际影响。
二是让公众明白,像切尔诺贝利和福岛那样的核事故在我国是不可能发生的。为什么呢?因为全世界的核电工作者都在挫折中总结经验和教训,防止出这样的事故,一旦出现事故一定会出台更安全的措施防患于未然。比如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操作错误仅仅是导火线,根本原因在于堆型缺乏最基本的安全防护,安全壳都没有。这种堆型在切尔诺贝利之后已经弃用了,现在的反应堆堆型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现在核电站防止放射性物质外泄的四道屏障能防患于未然。再比如福岛核事故,本质上 “它是一个事故序列”。首先,发生九级地震之后核电站正常停了堆,但地震引发海啸,14米高的海啸冲到岸上破坏了核电站的供电,又冲走了备用发电机,没有电力供水,热量难以排出,这样才导致核泄漏,后期处置又做得很差。在我国这样的海啸会不会发生呢?海洋、地震和核领域的专家通过共同研究已经得出了不会发生的结论。尽管如此,我们沿海地区核电站还是不敢掉以轻心,防波堤都加高了,就是为了防止类似事故。
第三,要让公众认识到我们可以驾驭核能,预防危机,并且核电安全做到切实可控。刚才说了世界上已经发生的核事故在我国不可能发生,那么没有发生过的事故呢?事实上,对于核电站运行过程中可能产生的任何微小隐患,对于能够认识的各种外部的、特殊的原因造成的事故,都做过预设和分析,都设计了安全稳妥的应对方案,努力做到安全,就连大飞机撞击都考虑在内了,那么事故发生的概率已经非常微小了。在国内,无论沿海或内陆,核电安全稳扎稳打,核电站发生事故的概率会进一步降低。同时,采取了各种措施,即使在事故工况下,对事故造成的环境污染和社会影响,都能做到实际可控。
理解的确是公众沟通的关键要素之一,把科普讲到公众心里去了,唯有如此,我们的一番苦心才不会白费。
公众是核电的受益者,不是风险的承担者
《中国核电》:目前,我国核电公众沟通主要是由核电企业主导和承担各种形式的核安全公众宣传。核电厂作为企业,其公众宣传活动被认为是在传播一种企业文化理念。您是如何看待公众沟通工作的?
杜祥琬:要达到有效公众沟通,必须提高认识,这不是简单的科普,还应该做到制度化、法制化和组织化。因为公众不仅是科普对象,还是参与主体,搞核电的最终目的是为公众谋福利,要让公众感觉到发展核电对大家有利,而不是风险的承受者。把工作做到这样的程度,我们的核电事业就会健康发展。所以,我们与公众沟通讨论核电安全,一定要把他们当成主人,让他们参与进来。而参与进来不是开一个报告会,让他们当听众这么简单,必须制度化、法制化、组织化,形成一种机制。
举个例子,大亚湾核电站建设之初,香港曾有人反对,为此组织了安全委员会,企业、公众、政府、专家全方位参与形成了组织制度。有了这样的组织和制度,大家就可以做到深度沟通:担心什么问题?如何规避风险?对大家的好处是什么?不同意见通过沟通得到化解,最后大家就能达成一致,切实感受到其中的 “利”。国外也有很多例子,比如建立 “环境协调委员会”等类似机构,在处理核电、焚烧垃圾厂等与公众利益相关的项目时,环境协调委员会在项目启动之前建立一个政府、公众、企业、专家四方参与的机制,着手进行公众沟通工作。对公众关心的一些实际问题做深入沟通。内容包括项目初衷和目的,项目给公众带来的利益,项目对社会经济发展起到的作用,如果有风险如何解决等,实际沟通效果很好。再比如,法国在公众沟通制度化、法制化、组织化实践上做得很好。这个国家才几千万人口,相当于我们一个省,却有58座核电机组。这么高的核电比例,为什么法国人能够接受?因为他们形成了很好的公众沟通制度。良好的制度使公众对核电有获得感,公众对专家建立了种信任:“有话找得到地方说,有问题找得到地方解决,可以安心、放心。”这就是制度化、法制化、组织化的魅力。
鉴于此,我建议我国也要推进和完善公众沟通制度化、法制化和组织化,形成一套完善的科学、民主、透明的决策程序,而不是只做科普宣传。公众应作为参与主体,一开始就参与立项的酝酿、沟通和论证。要建立政府主导,公众、企业、专家协同参与的机制,做到四方责、权、利清晰,还可发挥地方人大和政协的作用,大家对项目的科学性和可行性、项目风险和利益达到高度共识,只有这样,才能推进核电事业平稳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