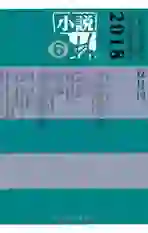连环套
2018-01-08安石榴
1
平原,丘陵,山地,这些词儿他们不会说,说不上来,他们说,嚯,这荒地呀,我的天老爷!这大荒地呀!他们做了一个手势,一只手或者两只手,在脸上划拉一下,他们说,没完没了哇!寻思这辈子也走不完了呐,咬着牙走到头,就进了山了。他们说起这个眼泪汪汪,偏转了头,眯了眼,像是躲避什么。他们躲避什么呢?他们从哪里来呀?他们闭口不谈。他们从春走到夏,又走到秋。起先站在那一眼望过去,近处尽是枯草,远处,那再远了就啥也看不见的地方,倒是一棵枯草也不见了,绿茸茸的一层毡子似的。走着走着绿草就没了膝盖,后来齐了腰,最后他们淹没在荒草中了。一阵风过,草秆儿即刻来了个大弯腰,他们才见了见整个的天空。他们没有留在大荒地上。他们为什么不在大荒地上建一个家呢?谁都不说。他们进山了,从此成了山里人。
2
贤明贤良兄弟俩大晌午头子呼呼大睡,轰隆隆像跑着两列火车似的。塔头墩垒砌的小屋一阵阵起着哆嗦,辣太阳透过破窗户煎烤着两张大脸,工夫不大就汪出一层油了,招得苍蝇轮番扑上来开洋荤,洋荤开过,就两两一边摞在一起,不动了。吊在大梁上的一串灰嘟噜,终于忍熬不住,倏地坠地。屋外一只芦花大母鸡,瞪着两只圆眼,伸长脖子,一边愣呆呆地转动着米粒似的小红耳朵,一边慢而迟疑地向墙根移动。突然,它耷拉下两只翅膀,喔喔叫着跑起来。屋里,鼾声磨牙声同时终止,贤明贤良兄弟俩睁开眼,对望了一下,支起上半身去看屋门。门打开了,一下推到底,门边子咣当一声抵在大墙上,回不来了。屋门大敞,一个人走进来。
我找个人,走到你们这儿了。那人一副少见的高壮骨骼。贤明贤良两人跳下地,才发现这个人块头大得根本无法与他对视。他慢腾腾地坐在炕边儿。贤明给他舀来一碗凉水。来人接过喝了,却并不急切。把碗放在炕沿上,掏出怀中的长杆烟袋。
贤良把烟笸箩推过去,暗中打量着他。这人一脸大胡子,鼻子眼睛不清不楚的,好像他脸上只长了大胡子似的。那胡子也不顺溜,乱扎扎一脸。
贤良问:老哥,哪儿来的呀?
山外。那人回道。
到哪儿去呢?
山里。
咋称呼老哥?
那人莫名其妙地说:有点账算,找個人。
这人说话金贵。兄弟俩又对望了一眼,屋里一时静悄悄的。
那人点上烟,慢慢吸着,吸了一阵子,重新把话头提起——
你们干啥营生啊?
贤良说:采蘑菇,挖药材。
怪不得墙上没挂枪呐。他来了这么一句。
兄弟俩没吱声,不接话。那人于是说:山里有枪的人家,手里都攥着人命,是吧?
说完,只顾大口抽烟,一会工夫,满屋烟雾。直到烟雾散尽,那人说:水也喝了,脚也歇了,我给你们讲个新鲜事儿就走人。
山里人烟稀少,消息闭塞,有时候一年半载遇不到一个外人。所以,偶尔有人来,山里人家都倾尽所有招待这些陌生人。过路人便把一路见闻留在途中,以此答谢允许他们住宿、打尖、歇脚的人家。
他说,昨晚,有个老客,运气好,整了一块大烟土。嘿嘿,他寻思自己挺精——那人指指窗外,稍作停顿,一股微弱持久的轰鸣声远远传来。
听见没?他问贤明贤良兄弟俩,说,和这条河一样,水流急,倒是不深,能趟着走。老客要趟着河水走到山外去。你们猜怎么着?来人并不等兄弟俩回答,只是看了看兄弟俩的脸,说,他背着一块大烟土。又重复道,像是赞同谁的话似的,说:是啊,他这是扛着一座金山呐!这老客寻思他自己想得挺周全,不走山路,走水路。呸,他算计错了,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那人陡然停住了故事,转身盯住兄弟一人,半天,问,昨晚是几儿?
贤良说,十六。
对呀,十六!那人一拍大腿,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这老客寻思十六的月亮只成全他自个儿呢!一片水亮亮,好走呀!劫道的人埋伏在山路上,逮不着他!没想到哇,月亮对谁都一样!来人哈哈大笑两声,两只大手搓了搓乱扎扎的胡子,说,他失算了。还有一步,老客就出山了,这老客可能就要乐颠馅儿啦,可说时迟,那时快着呢,就听啪,啪,啪——
贤明贤良两人一惊,那人哈哈大笑,胡子乱颤起来,小屋又开始哆嗦。他笑啊笑,突然就绷了脸,阴冷冷地说,这三枪从树林里钻出来,那叫一个准,一下子就干碎了老客的脑袋瓜子!
贤良霍地一蹿,要扑上去,贤明一把将他按在炕上,他挡在贤良的前面,对峙立即发生了。贤明算是看清了这个不速之客的模样,他们的眼睛都瞪到了最大,死物一样,连眨都不眨一下。苍蝇嗡嗡地从两个人之间来回飞舞,四只眼睛只想从对方那里强取豪夺些什么。
最终贤明挪开了眼睛,他爬到炕梢去,推开一堆杂物,取出一个四四方方的油布包袱。那人接过,转身就走。
贤明贤良兄弟俩冲上去,重重摔上屋门,门后两支枪倚墙而立,他们一人抓过一支,贤明却伸出手再次拦住贤良,低声说:就一个人,他也不敢。两人右手提枪卧倒,耳朵贴地,踢踢踏踏的马蹄声传来,他们仔细辨识,踢踢踢……踏踏踏……
兄弟俩脑门上全是汗,交换着他们的判断:
四匹马。
四个人。
不知道什么时候,阳光又从破窗户钻出去了,小屋暗淡下来。兄弟俩坐在地上,一只蚰蜒簌簌爬着,贤明盯着它,直到它爬到手边,猛地用拇指按住,一旋,说,杂种操的,这事儿没完。贤良咬着牙齿点了头,说,明摆着,必是王福那个王八羔子干的!
3
他说他叫李福。
哈尔滨这条街上的姑娘们都喜欢他。姑娘们叫他李福儿,就拐了那么个小弯儿,听着甜得都齁得慌了,嗓子痒痒的。她们说:李福儿鬼头鬼脑,挺好玩儿,还敞亮,不抠搜,好掏钱给她们买好吃的。有的姑娘啰嗦,问他,李福儿,你打哪儿来呀?李福说,你别管,我又不差你钱。姑娘一翻白眼,笑了:死样!
李福找姑娘上瘾,他还好下馆子,几个月下来,油光满面的整个人大了一圈,喧乎乎的了。可是,心不静。后面总像有个人跟着,他整天疑神疑鬼、一惊一乍的。本来玩着呢,好好的,突然就奓了毛,从幔帐褶子里生生看见一双贼溜溜大眼睛,招得姑娘们尽逗他,她们捏住他的下巴,不让他的眼珠子四处跑,然后问:你真叫李福儿?你的钱怕不是好道儿来的吧?
李福待不住了,跑到呼兰,还闲逛,不知道干啥。其实李福就是心不静,怀里揣着事儿呢,他没法让自己消停下来。左不是右不是,没着没落的时候,有那么一天,李福在道边上抽烟发呆,一辆单匹马拉的大车嘚嘚踏着小碎步,跑得蛮精神,经过李福身边突然停住不走了。赶车的老板子“嗷嗷”训斥他的马。那是一匹白马,有一个圆滚滚的屁股和修长的身躯。白马一副充耳不闻的样子,呆呆地站着,慢慢将两条棕色睫毛落下来,遮住眼。
咋回事呀?李福伸头问。
不对心思了。车老板子说,这畜生千好百好,就一个毛病。不管你干啥,在啥地方,它不对心思了,呱唧一停,打死也不走了。
嘿——李福发出一个疑问的长音,嘿——他有点兴奋。
车老板子把鞭子摔在身旁,手去腰间取下烟袋锅,他也不知道得靠到啥时候。李福双手撑住车大板,一蹦一扭,坐大车上了。就在他往后蹭着屁股,收起双腿盘起来的当口,马车一动,向前走去。
漫天火烧云,起火了似的,烧得西天下一刻就要塌架了,马车“忽忽”跑起来,火苗子上蹿下跳。
不下去呀?老板子沒回头。
走吧,不下去了。李福望着通红的天际。
必是碰了一棵蒲公英秧子了,车前猛地冒出一团蒲公英的小伞。逆光中,点点黑色乱影四处飘散,一会儿就不知所终了。
李福心想,爱哪儿哪儿吧,越远越好。他没有把这话说出口。
李福并不知道他走了多少日子,又换过了几辆大车。
这一带山不高,山谷开阔敞亮,阳光分外充足,林地间青草又短又齐,一律亮晶晶的。李福心中叫了个好。望见林地间和缓坡上错落着几棵松树和柳树。松树笔直高大,柳树矮,还团溜溜地像个帽头儿。大树是大树,小树是小树,并不混杂在一起,仿佛是按着什么规矩人工造的。李福心说,美观呀,和哈尔滨的公园一个样。这时,一棵山柳旁转出一个大闺女,他一眼就看呆了,大姑娘也和哈尔滨的一个样!目不转睛地再看,李福就跳下车,不再走下去了。
姑娘叫玉兰,十八岁。
第二年秋天,李福带着玉兰两个弟弟挖窑。他打算烧炭。跟他们说——他背地里才敢叫他们小舅子,说:你姐扎个“大撒配”。我走南闯北,也只见哈尔滨的姑娘才兴“大撒配”。两个十四五岁的山里小子问:啥玩意儿,大撒配?他们蹲在方坑边儿上往下看李福。李福扔了铁锹爬上来,给他们一人一脚,踹到坑里,让他们接着挖。李福看着他们的头顶,说,大城市的姑娘也梳一根大辫子,可是人家辫根儿不扎头绳儿,直接梳下来,一根大麻花似的,美观。俩小子仰起头发呆,一脸不解的样子,不知道姑娘家那么个小东西有什么了不得。李福指指坑底,示意他们接着动锹,他则蹲下来,临着坑边,脑子里又浮出玉兰的模样来了。他笑了,说,你姐这么一下子就把我造蒙了。俩小子中有一个后返劲儿,停下手里的铁锹,摸摸屁股,说:告我姐,你踹我们啦!李福呵呵笑了,说,告啥告?我都打算好了,烧几窑看看,赚钱的话,就干这个了,将来姐夫给你们说媳妇儿。小伙子听了就撒起欢来了,一锹锹土飞出坑外。
烧窑,多多少少要拜托老天爷。出窑的木炭是黑、亮、整齐,还是破碎、乌涂,多多少少要拜托老天爷,再怎么行家也要拜托。烧窑的人非常在意出窑的日子。出窑那天,每个窑主都带着酒肉嚼果,木炭一出手,大造一顿。
李福出窑的日子嘎巴嘎巴冷。今年木炭的行市好,巴彦来的大车早早就候在山下了。李福带着俩小舅子忙乎完了,从天窗看着空空的窑,心里满登登的。他顺着天窗下到窑里,四处仔细闻了个遍。空窑里一点儿异味儿也没有,暖烘烘的余热让人高兴。李福仰头叫道:下来吧。俩小子瑟缩着身子,带着酒肉嚼果乐颠颠下来了,不消一会儿工夫,三人都衣襟儿大开。空窑里可真舒坦啊。
李福又叨咕他的“大撒配”姑娘。俩小子噢了一声,说,问我姐了,那天她在河里洗衣服,晾在草地上等晒干。她又去河里洗头,扎辫根儿的毛线绳让水冲跑了,她没招儿哇,扎不了辫根儿,只好扎辫梢了。哈哈哈……俩小子乐得不行,以为挫败了李福一把。李福根本没理睬他们,他想着,哈尔滨姑娘穿蓝色棉袍,露出枣红色毛裤,脚蹬黑色垛跟皮鞋,俩毛球在脚面子上滚来滚去,俏。他想着,他要给她置办齐。最好领着她去哈尔滨,让她随便挑选大围脖——他突然受困于那些大围脖了,配什么颜色的才美观呢?这时候,他听见一个小子说,你可不能打我姐啊。李福一挑嘴角笑了,说,打老婆?那是你们山东棒子才干的事。俩小子垂头了,他们的爹动不动就打他们的娘。李福一想这老山东子就有气,是个爷们儿,厉害使到外面去,打老娘们儿算啥本事。只是这老山东子太鬼,我这媳妇没娶到手呢,钱倒是让他崩去了不少。不过也没啥,钱嘛,有去就有来。不寻思这些了——喝酒吃肉!李福大叫一声,恶声恶气的。
看不见的小蛇一条条从四壁的土墙中钻了出来,在曾经窑内一片红火的过程中,它们深深嵌进泥土中。窑空了,它们慢慢返了回来,有一些从敞开的天窗飘出去,有一些找到了更好的去处,它们钻到三人的脑子里去了。
三个人四仰八叉躺了一地。其中一个迷迷糊糊坐了起来,一歪头吐了几口。他记起了一些事,他听屯中的爷们儿讲过,这是熏着了,闹不好会死人!他拉拉身边的李福,李福一动不动。他又去拉他兄弟,那小子晃晃悠悠坐了起来,也吐了两口。两人一先一后爬上梯子,爬出空窑。然后连滚带爬地跑了。
4
三家子。
刘瘸子和凤翔围坐在火盆旁边,听着秋风从西边那条道上卷来,打着呼哨撞翻在东山上,劈成两股,斜奔向两条向南和东北去的路。两个人不说话,就是听,仿佛风声里有什么故事似的。
风,停歇了,路上遇到什么耽搁,久久不再起。在漫长的回味当中,刘瘸子猛地打了一个激灵,凤翔在暗中看到刘瘸子虚空在火盆上的两只手微微抖了一下。就在这时候,屋门突然打开,一股冷风嗖地窜进来,刘瘸子和凤翔惊愕地扬起脸——
一个又高又壮的黑影立在屋地当中,刘瘸子和凤翔点了穴似的僵住了。
黑影无声移动,坐到火炕上,朝向火盆,身子和脸在一片黑暗中缓缓地现了出来。他一脸乱扎扎的大胡子!
凤翔欠起身,盘着的腿绊了她一下,“咚”地又坐了回去,再起,悄然跪爬过去点了一盏油灯放在小炕桌上。灯芯燃成吃碟大小的光晕,配合着骤起骤歇的风声紧一阵松一阵地颤动。
屋子亮了一些,两个男人背着各自的影子相对而坐,沉默不语。凤翔探出身子把烟笸箩推向来人,灯突兀地哆嗦了几下。大胡子取出烟袋锅子,插到烟笸箩里,手用了劲,烟叶子发出牛反刍的声音。烟袋锅子满了,瓷实实悬在火盆上空。凤翔爬开去拿曲灯儿,刘瘸子出手阻止了她,一抖,那只手直接伸到火盆里,捏起一块红红的炭块,举着,似乎并不急于出手,眼睛却定定地看住大胡子。大胡子稳稳地擎着尺把长的烟袋,头稍稍地倾了一倾,嘴就噙住了烟袋嘴儿。刘瘸子将炭块凑近烟袋锅儿,外面的风又狂躁起来,发出尖利的嚎叫,屋子里却死寂成古墓。大胡子噙着,他不抽吸,烟杆尽头的烟袋锅得不到流动的氧气助燃,碎烟叶只能算是一小撮冰冷的土屑。刘瘸子手中的炭块发出温润的红,手指上慢慢地滚下滴溜圆的珠子,落在火盆中“噗”“噗”“噗”接连升起几缕青烟,一丝焦灼的怪味在三个人的鼻子之间游荡。
我不欠你,你找王福算账去。刘瘸子说。
那人接住,说,你们谁都跑不了。
不就是钱么?都给你拿走!
我只要我的那份儿。
……
这一夜风声不停,松涛阵阵,吼得瘆人。猎户老海和追棒槌的狗剩子在各自小屋中的土炕上沉睡,隐约听到马嘶车鸣,他们一概归置到星夜下的狂风中去了。墨色浓云狂奔不息,直到天光发白,才隐退消散,了无痕迹。太阳淡淡地挂在清晨的天上,不大精神。落叶积在院子里、路上和角角落落。客栈门上顶着一根木棍,表明主人不在。土路上点点血迹,像一种奇怪的小兽足迹,向东北方向逃遁而去。老海和狗剩子循着去又循着回,他们拿开顶门棍,打开门,闻到一股刺鼻腥气。刘瘸子仰在炕上,双腿耷拉在炕沿下。他脚下,躺着一个男人,他的脸血肉模糊,一脸大胡子浓烈异常,向四周扎煞着!他们已经冰凉僵硬。
小炕桌翻在地上,炕席半卷着,露出的炕面子被刨开,土炕上、地上散落着几块陶罐碎片。老海蹲在炕上,向炕洞里看,又伸手摸了摸,什么都没有。
老海看着陶罐碎片,琢磨了一会儿,说,有赫儿(钱财)呀!
狗剩子说,好像不老少。
5
贤良带儿子进深山老林,是十二年前的事情。那时,贤良三十八岁,儿子八岁。他们上路的时候,贤良知道只有这一条路走。当时他已经明白,之前的二十年,他白活了。如今,贤良只能带着儿子去找一个荒无人烟的地方。
儿子并不知道他曾经有个叔叔。
儿子跟在贤良身后,一门心思计数白天和黑夜。这件事他起初干得很来劲儿,后来累垮了,只记住了一些。一段明亮的鹅卵石河滩,他记住了,他不想忘,一辈子都不能忘了。它藏在矮树、大树和蒿草里面,他毫不知情,一步迈上鹅卵石滩,便看见它闪闪发光。从此,他知道了,闪闪发光的,可不只是太阳。鹅卵石滩、急流、白桦林,甚至深浓的绿叶,都会闪闪发光。还有林中穿行时听到的鸟鸣。它们总在远处,他永远都看不到它们。没有一只鸟在他身边的树上鸣唱。它们害怕着什么似的,躲在森林的深处,咕的一聲就闭住了嘴。森林静得不行,他贴着父亲的腿行走,被自己的呼吸声催促着。他只在山谷中看到过飞行的鸟,可是,飞行的鸟不出声,它抿着翅膀,树叶子似的飘落到草窠里,不见了。他们还走过了几个屯子,但他们都没有留下来,继续走。有一天,父子两人走过一处山脚,儿子眼尖,看见一只白骨生生的腿从一个凹陷的坑里伸出来,直愣愣地指向天空。儿子指给贤良看。
贤良问他,怕了?
儿子摇摇头,问,爹,那是谁呀?儿子什么都要问问,他以为凡是大人就什么都知道。贤良也总有答案给他。
贤良说,烧窑的。
儿子问,爹,你认得他?
这回轮到贤良摇头了。
那你咋知道他是个烧窑的?
贤良笑了,说,你没看到坑么?空窑塌了。
儿子又问,为啥他死了?
贤良说,必是有缘故。贤良想了想,给了个温和的答案:烟子熏死了吧,烧窑的一大意就好这样呢。
儿子走出去好远还转过头看。从这之后,再也没有遇到过屯子、人家。路也没有了,树林凉哇哇的,阴暗,树隙落下稍许光条。他们走上一条非常隐蔽的毛毛道,贤良分开蒿草和杂树才找到的一条路。儿子的脸和胳膊被枝叶划出一道道血痕,沁过汗水,火辣辣痛。父子两人的食物全吃光了,好像半步也走不动了。他们遇见了一个小房子。小房子可真小,一个小窗户,一个小门,窗户和门框由带皮柞木小杆做成。小窗子打着井字格,柳条子编的门大敞四开。屋里没人。贤良先看到地上两节光皮树桩,贤良知道那是空树桩做的木桶。他揭开盖子,吁出一口气,一个桶里装着玉米面,一个桶里装着小米。不管主人在还是不在,贤良都可以熬一碗粥和儿子一起喝。然后,他才看到桶盖上一层厚厚的灰尘,以及到处的灰网和尘埃。小屋只有一铺小炕。儿子叫了一声,他发现炕面子上紧挨着烟囱根儿长着一蓬绿莹莹的青草。小房子塔头墩垒砌。塔头墩哪来的呢?很久之后,父子俩上山下套子,走出去挺远,碰到一块沼泽地,苔草和泥炭凝结成一个个塔头墩,像一颗颗黑黢黢厚墩墩的头颅,列队似的布满沼泽,铺展出庞大阴森的阵势。塔头墩缝隙中的水幽暗青紫,只在一侧根部隐现半匝水银亮线。它们一动不动,一声不响,像是早就等待着什么。贤良抬起头,望向天边。夕阳正浓,天边铅色云朵挡在晚霞之前,又被渐渐薄透的亮色间隔分割,紫粉色云片、浅灰色云朵低垂,染上了父子两人的脸。贤良眯了眼,将一只手摁在儿子的肩上,他告诉儿子,小房子的主人不会回来了,小房子是我们的家了。儿子问,那个人是谁?他去哪里了呢?父亲摇摇头,望着青山,没话可说。从此,他们安心睡在主人铺在炕上的狍皮褥子上,使着主人的铁锅,和别的几样家什,遇上爆发火眼,父亲也会摘下天棚上的熊胆用上一用。
十二年之后,熊胆还用着,而且他们又有了一只。有一年,父子二人打到一只黑瞎子,取了胆。这只熊胆他们送给了几个采参人,人家留下一斤食盐,还有一袋子小米。
贤良的思绪戛然而止,他不乐意想起的事情更多些,他躲避它们。他躺在炕上几个月了,昨天傍晚他嘴角突然流出一丝涎水,一直悬垂到衣襟上。儿子以为父亲想荤腥了,对他说,明儿个我打个狍子吧,回来烀上。
清晨,儿子把一碗小米饭、一碗水放在父亲枕头边。他没事儿的时候坐在外面柴火垛上给父亲刀刻了一只红松木夜壶,也放在伸手可及之处。然后他说,妥妥的了。贤良想,儿子还不知道他不会说话了,儿子从未见过垂死的人,他哪里知道一个要死的人是什么样子呢?
儿子向山上走去,很快进入一片针阔混生林。山中六月,树木茂密藤萝繁盛,父子两人在另外三个季节开辟的便道还原成林木,他用猎刀一边清理一边前行。两个时辰后,他终于进入松林。他松了一口气。阳光透射进来,投下或疏或密的亮点和亮块。倒木上有一只花鼠。他在稍远处停下来看,不想打扰它,却觉得有趣。花鼠独处的时候也是一副慌张惊恐的样子。它嘴里含着松子,两腮鼓鼓的。他知道它在晾晒储物,可是,要把一粒松子放到倒木上,它却不能一次做到。它哆哆嗦嗦地跑来跑去,四下张望,总要几次三番才肯放下。小东西发现他了,仓皇逃窜,再也不出来。他走到近前去,倒木上蘑菇、松子摆了一排。多么会过日子的小家伙!他猫着腰又看了一会儿,捡起一颗掉在松针上的干蘑菇,替它放在蘑菇队列里。他没有跨越倒木,绕了过去。
他走出了松林。前面一片草海,紧连着阔叶林带边缘,他在那里会找到狍子。但他并没有马上行动。他坐了下来,双手扳着两腿交叉盘结处,头低在胸前,等了一下,他突然松开四肢,仰身躺下去。蒿草淹没了他,天空瓦蓝瓦蓝,他看着那一方蓝,发了好一阵子呆。他爬起来,拿过枪。山林被亘古积累的庞大寂静裹挟着,一颗子弹的爆裂声似乎被那寂静扼住了,与一根垂挂很久的枯枝突然坠地的声音不相上下。他肩扛着狍子踏上归途。
松林里出了大事。那根倒木被推翻在一边,蘑菇和松子撒了一地,倒木下现出一个被破坏掉的小土洞,留下了入侵者的足迹。他仔细端详着,想,这是个大家伙。他把狍子放在地上,捡起蘑菇和松子揣进怀中,爬上一棵松树,选一根粗枝,把它们摆在树枝上。他想,要是小东西那时候恰巧没在家,要是小东西躲过了黑瞎子的魔爪,它就会找到它们。
剩余的路已经不多,也不难走,他走在自己早上开出的道上。他走出针阔混生林地的时候,对面山上的林木一片黑暗,灰蒙蒙的雾气在山谷间翻滚流荡。小房子没入苍茫之中,就像沉入急流之底。他知道它在那,可是他看不到它。他不敢再往下想。狍子横在肩上,他两只手分别抓着狍子的前腿和后腿,抓得牢牢的。然后,他站在那儿,低声叫着爹呀爹。他呜呜咽咽地哭了。
作者简介:安石榴,本名邵玫英,黑龍江人。已在《北京文学》《北方文学》《小说林》《山东文学》《山西文学》《青春》《黄河文学》《福建文学》《广西文学》《飞天》《四川文学》等发表中短篇小说散文若干。有文章被《小说选刊》《青年文摘》《读者》转载。获黑龙江省文艺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