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鲁敏:让我们拥有写作的取景器
2018-01-08孙永庆鲁敏
孙永庆 鲁敏
鲁敏,女,上世纪70年代生人。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现居南京。1999年开始小说写作,已出版中短篇小说集《九种忧伤》《墙上的父亲》《纸醉》《取景器》《惹尘埃》、长篇小说《六人晚餐》《此情无法投递》《百恼汇》《奔月》、散文随笔集《我以虚妄为业》等。曾获鲁迅文学奖、庄重文文学奖、人民文学奖、中国作家奖、中国小说双年奖等。多部小说入选中国小说学会历年小说排行榜及中国小说年度精选本。有作品被译为德、法、日、俄、英文。下面是教师、作家孙永庆与鲁敏老师的对谈。
孙永庆:您的第一本散文集用《我以虚妄为业》为书名,“虚妄”这个词也在您的作品中经常出现,我们就从“虚妄”说起吧——这个词对您有何特殊意义?
鲁敏:我有几个同行好友,他们对宗教有自己的接触和体验。我是完全不敢碰。我性格里火气很重,既有烟火气,还有愤怒气、不服气、志气等。说来有些惭愧,从生活样貌上讲,我完全不是“空”或“虚妄”的人。比方说,我莫名其妙的,就很喜欢一大早去挤地铁,混在人群里匆匆奔跑。那种使劲儿活着、朝气蓬勃的滋味,总是让我满怀感慨地捕捉,并反复咀嚼。
可我又一直是服从和崇拜“虚妄”的。虚妄,在我这里的理解,不是否定或悲观之词。它是挺实在的一个中性词。它就是我所理解的人生的一个恒常之态。各个阶段、各个方向上,我们都在含糊地占有与失去,追索又重建,虚处生实,实中又生虚。活着即是如此,写作更为典型,妙手空空,空生万物,万物归尘。承认虚妄,不惧虚妄,我才有力气,也感到踏实,甚至时不时还有点儿高兴呢。我只负责把暗疾撕开来,夸张地、变异地呈现给大家看,但不负责“解说”或“解决”。我并没这个企图,也觉得或许没这个必要。
我喜欢“虚妄”这个词,不仅仅因为我是个写作的人。人生是既充实又虚无的存在。那种虚妄性,大家兴高采烈的时候察觉不到或意想不到,但其实它是生活的大背景和基调。小说的虚妄为什么可以抵抗这一切?因为虚构给人生带来了无限的可能性,写作就是一种精神“出奔”。小说里你可以反复逃离、反复出发、反复回到起点,它是丰富人生的综合体,你可以站在人性的深渊边或尖峰上,上上下下,来回奔跑,不知疲倦,没有终点。有了虚构,我的人生不管怎么单调贫乏,怎么短暂,都可以忍受。这是我的职业的最大便利和恩惠。虚构艺术有力量来弥补、包裹我们无力庸常的人生。
孙永庆:读《我以虚妄为业》,知您当年的中考,是江苏省盐城市第三名。工作后您还参加了自学考试,连续考了40多门课程,取得了3个大学文凭,可见您有超强的自学能力啊。和我们分享一下您的学习经验好吗?
鲁敏:无他,花时间而已。还有一个动力是骄傲与虚荣。这两个词,通常来讲都是贬意的,是人性的弱点,但在学习或带有竞争性的事情上,也可以化其为动力。我是很想通过努力远远地跑在前面的那种性格,不甘中庸,不肯落在下游。
孙永庆:“作文本来就不是文学审美”,我也这么认为。作文是考察学生对语言的掌握情况,也就是运用语言的能力。您认为,作文和文学是两个概念吗?
鲁敏:这确实应因人而异。说文学与作文差异很大的人有,说语文训练对写作有益处的人也有。其实我还挺怕应试作文的,因为它违反了写作的本性,而文学写作是需要发乎心声、发乎性灵的。我尝试过用作家的眼光去教女儿写作文,效果并不好。那些我们认为好的写法、创意,似乎并不适合孩子们的考场作文。
孙永庆:您写了《思无邪》《离歌》《风月剪》《逝者的恩泽》《纸醉》《颠倒的时光》等以故乡江苏东台为背景的小说。故乡对于您的写作来说,是一口可以不断深挖的井。我想到美国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威廉·福克纳,他从著名的《喧哗与骚动》到《押沙龙,押沙龙!》中,一直致力于描述他在美国南部乡村的老家。很多同学在写作文时,总是为不知道写什么而苦恼,是不是能够从你们的写作实践中得到这样的启发——写作素材其实随处可见,关键是看怎么挖掘。
鲁敏:兴趣与热爱,决定你对某类题材或领地的叙述愿望。眷念故土,有时会像爱母亲一样,近乎本能。所以我感觉以故乡为“第一口井”,也算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真正的能力,是无中生有,是对不够熟悉的东西也可以通过想象和虚构抵达。学生在作文中,也要有意地建构这个能力——从实用的角度来看,最起码可以用来对付你不熟悉的命题。这个能力从哪里来,窃以为要怀有一种广袤的对生活和大自然的爱,对新鲜事物的好奇,对陌生外界的包容与善意。
孙永庆:您说过,文学魅力的奥秘在于“取景”——写作者都有一个秘密的了不起的“取景器”,这一取景器的层次、远近、构图、核心焦点、曝光参照、光圈系数,正是一个作家的眼光与气象所在。请您和师生们谈谈“取景器”这个话题吧。
鲁敏:写作者在这个问题上是一样的。面对生活与时代,面对同样的复杂世情、同样平淡的市井岁月,一个写作者的高明,肯定不在于裝上最先进的“镜头”,不在于气喘吁吁地去跟现实赛跑,最起码不仅仅是这样。
之所以说文学魅力的奥秘在于“取景”,是因为这个“取景器”是你所独有的,不同于别人的眼睛,也不同于先进的放大器,并且要胜出新闻、社论、电视剧或微博、微信,其核心部分所认领所介入的,正是肉眼所不及的、工具所不及的非物质部分。我相信每一位写作者都持有一个秘密的“取景器”,在对世界进行剥离与萃取。这一“取景器”的层次、远近、构图、核心焦点、曝光参照、光圈系数,正是一个作家的眼光与气象所在,并最终生成和决定了他作品的成色。
孙永庆:您在邮局工作了15年之久。从《致邮差的情书》《在地图上》等作品中,能看出您的这段的影子。“信件是一件多浪漫的事,你会想着每一封信的背后,都有不同的人和不同的故事。”您的这段话引起了我的遐思。现在人们已经很少写信了,尤其是当下的学生。书信最能够表达真情实感,而让学生多写写书信,是否会更引发他们的写作兴趣?
鲁敏:同意。写作就是跟陌生人说话,对陌生人写出心里想说的东西,说是写信也可以。每一部作品都是写給读者的一封信。
孙永庆:我读您的长篇小说《奔月》,觉得这样的文字读起来很舒服。但您说《奔月》的写作并不顺利,从2014年7月到2016年7月,改了六稿。有一次修改特别值得记取:“比如,我一直喜欢在行文中发议论。《六人晚餐》就有这毛病,改过,没改好(是因为我当时的固执,为什么我就不能讲话?)这一次,又发作得很厉害,时不时就大讲画外音。因此有那么一遍修改,针对这些冗赘,我一直像拿着砍刀在砍。这样的‘杀戮,从结果上看是无痕的,但对自我则很有教益。我记得那些残词断句有如落英纷披,它们没有被白白写出,也没有白白死去。”呈现在读者面前的《奔月》,是反复修改出来的,我想这应该会对同学们的写作有些启示。
鲁敏:对,好文不怕千遍改。我们的许多同行都是这样。修改从来不是白费工夫,你会感到一种技术上的进步。就好比练武之人,也会无数次地重复基本动作。对为文者而言,修改就是基本动作。
孙永庆:您曾回忆自己读书,要做大段大段的读书笔记。读《巴黎的秘密》《基督山伯爵》等大部头时,因为里面的人物和事件比较复杂、纠结,就挨个儿地替人物做年表、做故事线、做家族谱系等,把书里所有的伏笔、呼应、关节点什么的全都标出来,做成表或图,错了就修改。这样就把故事情节的来龙去脉、人物命运的跌宕起伏弄得清清楚楚,既训练了遣词造句的能力,也学会了如何谋篇布局。您的这种读书法,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鲁敏:这样的读书方法虽然比较笨,也比较慢,但就跟熊孩子拆开手表看看有什么零件差不多吧。从来没有无缘无故就无师自通的人,做任何事情都需要花些笨功夫、蠢功夫,包括白费的功夫、错误的功夫。
孙永庆:您把阅读称为补充维生素——维持生命的基本元素必须全面,不然身体要出问题。有一个主题的阅读必须强调,那就是“死亡”。您不仅经常读这方面的书,还写过不少这种主题的作品,比如《离歌》《墙上的父亲》《小径分叉的死亡》等。时下经常有报道学生为点小事就轻生的消息,我觉得应该让同学们多阅读这类作品,从而正视死亡,敬畏生命。
鲁敏:生命是最宝贵的恩赐。我们的教育大部分集中在强调如何奋进、拼搏、成功,成为人中龙凤等方面,对另一个向度的强调还是相当欠缺的,比如失败、缓慢、退步、死亡、回归、停止等。书写死亡也是为了不断地去与死亡正面相对,宁静地、审美地、多维度地去正视生命的起伏沉浮。
孙永庆:您曾说:“经典是我榨取幸福的源泉——这样的宣言也许显得肤浅和赤裸,但我不回避这种偏颇。我一向把精神上的丰满、流量充沛视为生活的最高级。”能和师生们聊聊您的经典阅读吗?
鲁敏:我的阅读比较混乱,不成体系。我喜欢粗糙的文风。这个粗糙不是不讲究,而是类似未加工的粗麻、四散的土坷垃与石头块那种质感吧。同样是女作家,我喜欢安妮·普鲁,她的《船讯》多好,多野气,多结实。爱丽斯·门罗我就没那么喜欢,那是女性化、中产化的发达触角……我自己也写不出粗犷强硬的东西,这大概是出于缺啥爱啥的心态。
偶尔喜欢装大尾巴狼,读一些偏理性的东西。我喜欢过福柯。他对疯癫、疾病、神经质有着华丽的见解,引申到社会隔绝、阶层压迫、教育误区、文明进程的戕害、平权与特权的诡变等,很有意思。我还喜欢西蒙娜·薇依。她有不同版本的传记,但都写得影影绰绰。她在世界上最确切的遗产就是她的哲思。《重负与神恩》是床头书,看得特别慢,看了后面忘了前面,却心甘情愿地再次复习,再次遗忘。薇依很奇怪,她有种清泠泠、几乎是拒绝般的态度,像风中传来的交谈。列维-斯特劳斯的《忧郁的热带》,我读起来也是兴致勃勃。我对田野调查、人种起源、部落形态之类的书,总是无条件地着迷。如果不是做作家,我一定争取去追随人类学家,哪怕做他们的打字员。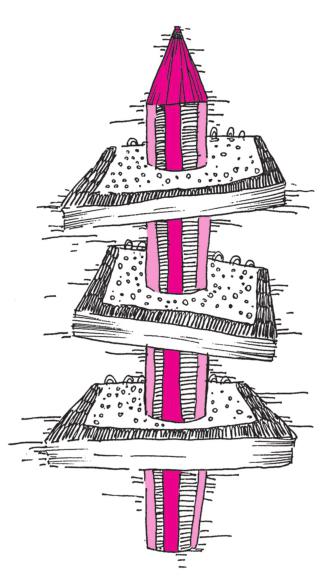
对,还有幽默感,这特别要紧,有时候它是显示作家才华的一个隐形指针。这种幽默需要发乎本真,发乎哀伤乃至愤怒。冯内古特有这股子劲儿,他的《五号屠场》我看了三遍。奈保尔的小说也总是有着绝望的幽默感。或许幽默本来就是绝望者的最后一道护身符。奈保尔在这方面术有专攻。铺陈如泻、狂放无忌的鲁西迪当然也会让人发笑,可是他的幽默里没有哀伤。他是进攻型选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