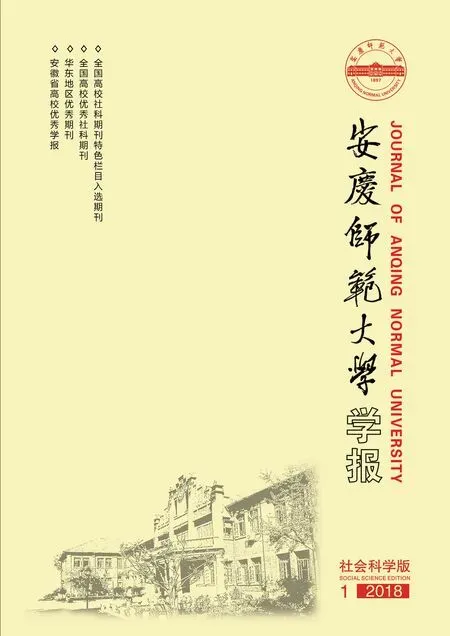李宗侗史学研究综述
2018-01-01李沛
李 沛
(淮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安徽淮北 235000)
李宗侗(1895—1974),字玄伯,河北高阳人。早年留学法国,回国后历任北京大学、中法大学及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讯研究员。李宗侗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一度非常活跃,但自从他1948年赴台后,因两岸学术交流中断,以致在大陆长期声名不显。学界对于李宗侗的研究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39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至1948年赴台前,这一阶段学界重点关注了李宗侗在古史研究领域的成就,蔡元培、顾颉刚、杨堃等学者就其古史研究发表评议。1974年,李宗侗逝世,台湾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纪念文集《李玄伯先生哀思录》,收录许倬云、孙同勋、文长徐、芮逸夫、杜维运等学者的纪念文章。这些纪念文章侧重不同,或评价李宗侗的古史研究,或关注其清史研究,或感佩其人格学养。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大陆学者对李宗侗学术的关注日渐回温,刘家和充分肯定了李宗侗的古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徐韬的硕士论文《李宗侗学术初探》(2010年)揭开了系统研究李宗侗学术的序幕。福建师范大学黄远东的硕士论文《李宗侗古史研究——以〈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为例》(2013年)为系统研究李宗侗学术再添新章,系统梳理李宗侗史学研究的发展脉络,将李宗侗史学成就更全面地展现于学界。
目前学界对李宗侗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学术背景,中国古史研究,清史、史学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和广育后学五个方面。本文就此展开论述,敬请方家批评指教。
一、关于李宗侗学术背景的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徐韬的硕士论文《李宗侗学术初探》与福建师范大学黄远东的硕士论文《李宗侗古史研究——以〈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为例》皆是系统研究研究李宗侗学术的著作。在论述李宗侗的学术背景时,前者以“从世家子弟到新潮学人”“故宫四年”“潜心学术的岁月”三时段为线索,介绍其学术背景;后者从“家学渊源”“留学法国”“时代影响”三方面介绍其学术背景。两篇文章在论述这一主题时存在相同之处,亦各有特色。
首先,两篇文章皆以时间发展的顺序论述之,大底内容分为五个时段:一、学习传统文化阶段;二、留法阶段;三、积极应世阶段;四、转折阶段;五、潜心学术阶段。
其次,两篇文章各有特色。徐韬的文章主要突显李宗侗积极应世的志趣、关怀时政的情怀以及献身学术的精神,而黄远东的文章则突显李宗侗史学方法的形成,于铺陈处埋下伏笔,为后文介绍李宗侗的史学方法及成就作以铺垫。知其人、论其学,徐韬关于李宗侗学术背景的介绍,侧重点在“人”,而黄远东的文章着眼处在于“(李宗侗)学识渊博,古文功底扎实,出身于晚清名臣、帝师宰相李鸿藻之后,对研究清史有很多便利”[1]10,将着眼处放于“学”。综其两者,我们对李宗侗其人其学的背景都有所了解,前者重“人”,后者重“学”,若是将二者的思路糅合为一,着重研究其学术背景与学术思想的关联,或会有新的发现。
二、关于李宗侗的中国古史研究
“古代史是玄伯师早期研究工作的重点”[2]2,1939年,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由上海开明书局出版。该作借鉴法国史家古朗士的史学研究方法,多有创见,可谓当时国内古史研究领域的一朵奇葩,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可。蔡元培为其作序,肯定了李宗侗在研究古史时对于民族学知识的运用,认为“历史的材料,以有文字而后为限断;过此则有资于史前学及考古学。但史前学之所得,又往往零星断烂,不能为独立的说明;乃有资于旁证的民族学。”[3]3除此之外,还点明《新研》的五点精要:“一、中国有图腾制;二、中国祀火的事迹;三、中国曾有母系制;四、昭穆的更迭;五、尧舜的荐贤。”[3]4这五点精要从新颖的角度解释了部分过往学界存疑的古史问题,蔡序则更突显其重要性。
杨堃在40年代末期发表《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一文,肯定了李宗侗的古史研究,认为“若从方法论而言,实堪称为一部划时代的著作”[4]117,但对其社会史学和比较史学的方法提出了不同的意见,指出李宗侗在比较时“一方面应比较其同点,一方面亦应注意其差别”[4]121。这篇书评客观评价《新研》,有扬亦有抑,对我们正确认识此书的史学价值大有裨益。
芮逸夫认为李宗侗的古史研究有三点突出贡献:一是证明春秋末期以小人阶级为主的新的“士”阶级的崛起;二是证明我国古代确有殉葬和人祭的存在;三是证明我国古代姬、姜二姓的频繁联姻,正如辽代萧氏与耶律氏的外婚制[5]。许倬云则认为李玄伯在古代图腾制度的功能、宗教与政治的交互影响、社会变动与阶级升降的因果、古代婚姻与亲属制度的关系等研究方面皆有创见,给后学以启迪[6]。刘家和充分肯定“李玄伯的译著与专著把中国中西古史化比较研究提升到了一个空前的新高度。他所提出的具体问题,一般皆具有继续研究的价值。”[7]但也认识到李宗侗古史研究的局限:“有悟于古希腊罗马与古代中国的时代之同,而侧重究中西古代制度之同,也有忽略了中西之间区域之异的倾向,只作‘中国与希腊罗马古代相同制度表’,便可见此倾向。”[7]此外,黄远东的硕士论文《李宗侗古史研究——以〈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为例》着重论述李宗侗的古史成就。文章围绕“主即火”“图腾即姓”两个论点展开,指出“李玄伯运用了详实的史料考证,从古文字学等角度论证了中国的‘木主’和古希腊罗马的‘祀火’是相同的制度,即‘主即火’”。
三、关于李宗侗的清史、史学史研究
学界在研究李宗侗时,关注点多在其古史研究上,但对其清史、史学史的研究亦不能不提。
许倬云在《李宗侗文史论集》的序言里点明:“玄伯师是名门之后,他的祖父是同光间的名臣李鸿藻,帝师宰相,一时人望。家学渊源,于晚清历史,见闻渊博,是以玄伯师研究清史,常有一般学者未能想到的观点。”[2]2李宗侗出身清代世家大族,论及清史,如数家珍;他家藏资料十分丰富,这些条件都是寻常学者望尘莫及的。
在清史研究方面,因北洋政府官修的《清史稿》多有纰漏,李宗侗在1953-1957年间,指导台大历史系学生校对《清史稿》,主要方法是用《清实录》比勘《清史稿》,此举促进了台湾地区清史学研究的发展,成果斐然[8]。再者,李宗侗于1967年刊于《史语所集刊》37本上册的《清代中央政权形态的演变》一文,史料翔实有力、结构完整、论述充分,被人誉为继孟森之后研究清朝八旗制度最有成就的论著之一[9]。
此外,徐韬指出李宗侗清史研究的贡献主要集中在对“原始文献的整理出版和相关历史专题的研究”上[10]19,对其研究清史的方法进行梳理,点明李宗侗“主张据《清实录》、起居注、内阁军机处档案、朱批奏折,按年月排比,再以私家著作校其同异,并作考异,以为长编,既便保存清代史料,亦可备日后修清史之用”[10]19的学术观点。
在史学史研究方面,许倬云指出:“古代史是玄伯师早期研究工作的重点,除古代史以外,他在中国史学史的领域也有着全盘的考察,将各种历史的体例及其演变,理清了其特质与来龙去脉。他的《中国史学史》,纲举目张,对于中国各种史籍的特质与演变的谱系,均有交代,至今我们还未有更为完整的著作足以取代他的大作。”[2]2点明李著《中国史学史》“通”而“全”的特色。
徐韬同样总结了李著《中国史学史》的特点:“一、特重中国古史与史官源起的探讨;二、对我国史学史上某些争议较大的问题,时有独到之见;三、贯注了开阔的现代史学视野。”在总结其特点时,举出典型例证并常用比较方法加以论述。认为“与金毓黻《中国史学史》比较起来,此书篇幅虽小,触及的范围却反较前者为广……在不多的篇幅里,还为学术史、地方史、家谱、年谱、传记等留出专节进行讨论。”[10]26
四、关于李宗侗的史学理论研究
早在上世纪20年代,顾颉刚就曾对李宗侗解决古史问题的看法作出评论。李宗侗在《古史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法》里认为:“直遗的作品直接出自古人,古人所能看见的,除了缺破以外,我们仍能看见。所以他的价值远非传抄错误,伪作乱真的载记所可比拟。”“所以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3]189这种说法不无道理,但过于绝对。之后不久顾颉刚发文《答李玄伯先生》,认为“李先生所说的‘用载记来证古史,只能得其大概;……要想解决古史,唯一的方法就是考古学;我们若想解决这些问题,还要努力向发掘方面走’,确实极正当的方法。”但“我以为无史时代的历史,我们要知道它,固然载记没有一点用处;但在有史时代,它原足以联络种种散乱的遗作品,并弥补它们单调的缺憾,我们只要郑重用它,他的价值决不远在遗作品之下。”[3]190顾颉刚对李玄伯的古史研究观点进行了修正,认为有史时代载记仍有很大用处,不能单说考古学才是唯一途径。在这一点上李玄伯确有偏颇,而顾颉刚的修正则很好地补充了他的观点。
黄远东介绍了李宗侗比较史学和社会史学的应用以及其对史学理论的探索。他认为:“李玄伯在中国古史研究上,不仅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注重考证,而且把社会史学和比较史学的方法引进古史研究,为我国史学研究开辟了新的途径。”[1]21在论及李宗侗的史学理论时他进一步论述说,李宗侗跳出我国古史研究的窠臼,力图“探索先秦的社会形态,证实了我国存在图腾制度,存在图腾社会,图腾社会是宗法社会的前身。至于宗法社会之前是否存在图腾社会,限于年代久远,史料稀少,学界还是存疑的,但是李玄伯的探索丰富了我国在这一块的研究,为后人的研究做了铺垫。”[1]27黄远东从中国史学理论的研究背景出发,以中国社会形态的争论为例,点明李宗侗在史学理论上是非马克思主义学派,用西方的史学理论解释中国的古史研究。
徐韬在点评《新研》时指出李宗侗史学理论的不足:“作为一部创新之作,该书也存在着自身的不足,尤其是理论上表现出比较明显的‘西方中心论’情结,书中言必称希腊、罗马,某些比较及对古文献的解释还存在着牵强比附的痕迹。”[10]18黄远东则认为:“李玄伯虽然没有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史,但也没有跳出西方的史学理论,陷入了‘惟希腊罗马论’,单线进化论的思想。”[1]45
五、关于李宗侗广育后学、献身学术的关注
至于李宗侗广育后学,献身学术的品行,学界也多有提及。许倬云回忆:“有一年,因为排课的时间冲突,玄伯师特地为李卉和我排一班的专题课,因为我不能不行,玄伯师并且派三轮车来宿舍接去玄伯师府上上课。”[6]36又如孙同勋所记:“时时不忘作育后学,即在因病卧床的时候,也时刻以返校上课为念。1962年先生第一次中风住院,我去看他,见他正坐在床边,拉自行车内胎。他说‘我正在运动,恢复手臂机能,以后你常来扶我走动走动,恢复腿部活力,好早日返校上课。’”[11]再如文长徐回忆:“先生平时深居简出,嗜好有三:一是看书;二是写书;三是记日记及剪贴报章杂志成册。其实,恩师年已七十余,身体并不十分硬朗,但老人家的每日一卷在握的读书习惯却是数十年如一日,未曾间断过。”[12]杜维运同样有记载:“先生的《史学概要》、《春秋左传今注今译》、《春秋公羊谷梁今注今译》等书,都是草拟于病榻之间。”
李宗侗作为老师,不仅对学生的学业十分重视,对学生的生活更是关爱有加;同时李宗侗以身作则,献身学术,广育后学,这些品质潜移默化地影响其学生。诸如许倬云、逯耀东、杜维运等皆在史界独当一面,这与李宗侗的悉心教导是分不开的。
六、目前李宗侗史学研究中存在的问题
目前学界关于李宗侗史学的研究取得一定成果,但同样存在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具体来说有以下三点:
1.对其史学方法的讨论尚有空间
李宗侗的古史研究方法受益于法国史家古朗士,许倬云对此有所介绍:“1924年返国执教于北京大学及中法大学,当时法国的古史专家古朗士,将民俗学知识引用于希腊古代史,获得丰硕成果。玄伯师借用这一研究方法,探讨中国古代文化的一些现象,为中国古史研究新辟了蹊径,例如他从寒食易火的风俗,与古人崇拜‘火’的观念中,取得民俗信仰的新解。”[2]1但古朗士具体如何写作古史致李宗侗如何学习运用,学界讨论尚浅。若要深入剖析李宗侗的史学,具体考察其史学方法从“西”到“中”的过程,则显得尤为重要。对其西学意蕴的关注更不能仅仅围绕“比较史学”“社会史学”这些大概念泛泛而谈。
2.对其史学成就的研究不够全面
李宗侗尚有很多史学专题未被学界重视。比如其《周代的政治制度》,透过西学的视域,引用翔实的史料,从邦国的起源、宗统与君统、周代的长子继承与兄弟分权、由君与贵族的分权到君的集权四方面展开论述;其《论夫子与子》详细考证《左传》《国语》《论语》《孟子》中的“夫子”与“子”,成一家之言;其《封建的解体》从政治、经济、人口、军事等角度论述封建解体的原因,体现其多维考史的史学视野;除此之外,诸如《士的演变》《续论夫子与子》《炎帝与黄帝的新解释》《春秋时代社会的变动》等文皆有创见,学界却鲜有人提及。李宗侗透过西学视域研究的中国古史与传统古史研究的区别并未引起学界的重视,这种比较研究是突出其史学价值的重中之重,同样是系统研究李宗侗史学所不能忽视的。
3.对其赴台后的史学工作关注不够
李勇教授认为:“1949年以来,台湾史学融纳大陆、日本和欧美多重因素,几经变革,其中绝大部分为中国新史学的重要内容,是书写中国新史学发展史不可或缺的。”[13]而李宗侗史学具有鲜明的新史学特色,关注其赴台后的史学工作同样是研究其史学不可或缺的。赴台后,李宗侗任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通讯研究员。他不仅开始关注台湾本土历史的研究,比如1963年李宗侗在《大陆杂志》刊文《社祭演变考略——台湾土地庙的调查研究》,而且其学术背景发生了变化。加强对李宗侗赴台后的史学工作的关注,可以更完整地呈现其史学;通过比较两岸学术背景的差异,更能反映一定时间段内大陆史学与台湾史学的不同。
纵观学界研究李宗侗的三个阶段,可以发现第一阶段学界重点关注李宗侗在古史研究领域的成就;第二阶段,以《李玄伯先生哀思录》出版为代表,多纪念性文章,多角度还原了李宗侗生前的学术生活;第三阶段,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大陆学者对李宗侗学术的关注日渐回温,一些系统研究李宗侗学术的成果相继问世。
学界对李宗侗学术整体上持肯定态度,对其经世致用、献身学术的精神更是推崇有加。至于其“西方中心论”的情结,我们当作同情之理解。其生活的时代背景和学习背景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史学思想和史学方法的走向。在其史学成就方面,学界多是直白介绍或简单评议,而没有针对具体的史学领域加以横向的联系及纵向的梳理,在介绍李宗侗与同时代学者的交流和超越前人之处则略显苍白。至于其史学方法、史学价值及局限性方面,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参 考 文 献]
[1]黄远东.李宗侗古史研究——以《中国古代社会新研》为例[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2013.
[2]李宗侗.李宗侗文史论集[C].北京:中华书局,2011.
[3]李宗侗.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历史的剖面[M].北京:中华书局,2010.
[4]杨堃.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J].中法汉学研究所图书馆馆刊,1941.
[5]芮逸夫.忆念玄伯先生[M]//李玄伯先生哀思录.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1974:20-21.
[6]许倬云.师恩难忘哭玄伯师[M]//李玄伯先生哀思录.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1974.
[7]刘家和.世界古代史上的宗教与社会(专题讨论)——从中西比较的视角论说中国古代宗教信仰与历史的关系[J].河北学刊,2008(2).
[8]杜维运.敬悼李玄伯师[M]//李玄伯先生哀思录.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1974:19.
[9]马起华.寂寞身后事——悼李玄伯师[M]//李玄伯先生哀思录.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1974年:28.
[10]徐韬.李宗侗学术初探[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10.
[11]孙同勋.忆玄伯师[M]//李玄伯先生哀思录.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1974:32.
[12]文长徐.哭恩师李教授玄伯[M]//李玄伯先生哀思录.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1974:10.
[13]李勇.中国新史学之隐翼[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