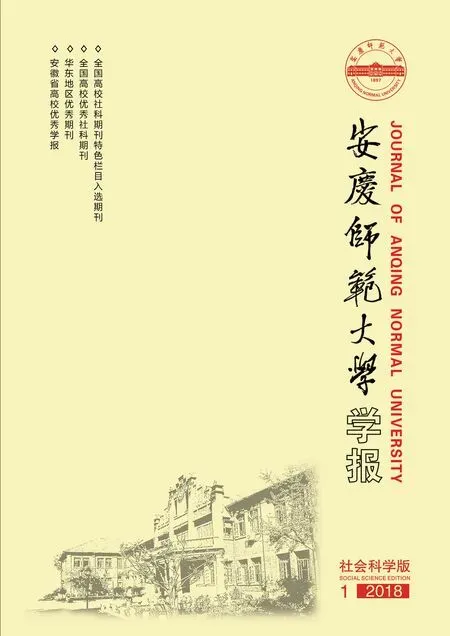魏晋南北朝“始有意为小说”刍论
2018-01-01李玉栓李思语
李玉栓,李思语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与传播学院,上海200234)
关于中国古代小说在唐代的发展,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认为,比起六朝小说的“粗陈梗概”,至唐代“演进之迹甚明”,并且“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1]。按鲁迅先生的说法,中国古代的小说作者到了唐代才真正具备这种创作自觉性,一个“始”字表明唐代之前并未出现“有意为小说”的现象,而且他认为这一点正是唐代小说有别于此前小说的“尤显者”。有关中国文学的自觉性问题,中外学者一直有所论述。王运熙先生认为“所谓文学的自觉,完全可以涵盖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2]63日本学者铃木虎雄则将魏代视为中国文学的自觉期。他们所说的自觉的“文学”还不包括小说,而对于小说的“自觉”,早在明代胡应麟就说:“至唐人乃做意好奇”[3],至鲁迅先生撰写《中国小说史略》又作了较为详细的阐释,之后这一论断成为人们对于中国古代小说体式成熟的一个通识。不过,对于这个论断,学术界也偶有不同的声音,一方面有人认为唐传奇的创作难以称其为“有意”[4]或“自觉”[5],另一方面也有人认为,早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个别小说如《幽明录》等,已经具备有意为小说的特质[6]。那么,小说“自觉”究竟始于何时?魏晋南北朝小说是否属于“有意”为之呢?笔者认为或许可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判断。
一、创作动机明晰
是否“有意”为小说,首先应从作者的创作动机进行判断。创作动机属于创作主体的审美心理,其中情感起着主导作用,“情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人的行为,成为人的活动和各种动作的持久的或短时的动机。”[7]唐前小说家的创作动机,历来被认为是受外部因素如宗教、史传文学的影响,“为时尚驱使”[8]275,其创作带有功利性。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有些以偏概全,实际情况是,推动魏晋南北朝小说家投身创作的,不仅有“补史之缺”的志向,更有个人赏玩娱乐的因素,这些因素支配着小说创作的方方面面,干宝、刘义庆即是显例。
干宝创作《搜神记》,即出于个人目的,自称此书是为“发明神道之不诬”,同时也是为了“收遗逸”和“游心寓目”。据《晋书》记载,干宝本是无神论者,父亲的婢女殉葬多年却不死,复活后不但结婚生子一如常人,更能预言吉凶,颇为灵验;后来,哥哥干庆病笃,昏迷数日后突然醒来,能对人讲天地鬼神事。此二事今日看来或有偶然的成分,亦可用科学来解释,但对一千七百多年前的干宝而言,耳闻目睹,不得不为之震撼,以至于从一个无神论者变成有神论者,并产生了编撰《搜神记》的想法。另外,干宝爱好阴阳数术,对神秘文化有浓厚的兴趣,谈生论死,无疑迎合了他的兴趣。干宝首先是史学家,然后才是文学家,但创作《搜神记》的动机与纂修《晋纪》不能完全等同,纂修《晋纪》是受命于晋元帝司马睿,是“在其位,谋其事”,编写《搜神记》则是出于个人情感和审美需要。仅从这一点来说,《搜神记》与《晋纪》等史书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刘义庆创作《世说新语》和《幽明录》的心理更为复杂,这源于他的职位与性格之间的矛盾。刘义庆出身皇室贵族,十五岁即在秘书监担任官职,为皇室效忠二十七年,直至去世,但刘义庆本身是个“为性简素,寡嗜欲,爱好文义”[9]的人,虽然屡任要职,但他并不热衷仕途,尤其是在目睹宗室之间的猜忌迫害之后,他希望远离皇室的钩心斗角,做一个自由的人。但是因为出身,他又必须担当一定的重任,这种无奈伴随了刘义庆大半生。晚年醉心于文学和佛教,反而得到了仕途中得不到的轻松,《世说新语》和《幽明录》即是在奉佛之余编写完成的。魏晋南北朝政权更迭频繁,人们的生活水平总体偏低,与刘义庆一样对现实生活抱有不满的人有很多,羽化成仙、因果报应等宗教因素恰好为他们提供了一种寄托情感的方式。所以,当我们把魏晋南北朝小说家们的创作置于鬼神信仰这个大背景下时,应该更加深入地思考这一现象的本质,正是因为每个人心中都有这样那样的情感,或仇恨不满,或悲观失望,或无可奈何,才试图寄情于“小道”,借书中人物之口,抒发自己对社会的看法,获得心灵上暂时的蕴藉,不说是“孤愤成书”,也必定是“心有戚戚然”。
炫耀才华兼及娱乐赏玩,亦能体现小说家们的创作动机。“若为赏心而作,则实萌芽于魏而盛大于晋。虽不免追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矣。”[1]33鲁迅先生亦承认志人小说的写作,虽仍有记录史实、供人揣摩的考虑,但欣赏和娱乐的特点已经很强。魏晋人尚清谈,“若不能清谈的,好似不够名士底资格”[10]。“清谈”这股风气,上自帝王,下至市井,可谓有雅有俗,兴盛一时。东方朔在这个历史时期颇受欢迎,出众的口才和满腹的故事仍使他在朝在野都极受追捧,正是这种风气的典型代表。而这一时期的志人小说,既是品评人物和崇尚清淡的结果,反过来又促进了这种风气的发展。裴启《语林》甫成,人们争相传抄,殷芸受梁武帝命撰《小说》,皆是例证。干宝在《搜神记·序》中也表示自己的书“有以游心寓目,而无尤焉”[11]19,说明在宣传鬼神之道以外,也可借之娱乐消遣。小道虽微,亦有可观之辞,既可自己取乐,亦可娱乐他人,更能展现才情。《世说新语》中有一些故事,如王浑妻调戏丈夫、山涛妻偷窥嵇康等闺阁事体,即“纯粹是出于趣味”,但也“不流于庸俗”[12]406,都能对人的心灵产生愉悦作用。南朝梁萧绮认为王嘉“搜撰异同,而殊怪必举,纪事存朴,爱广尚奇”[13]7,指出王嘉是出于“爱广尚奇”的目的编撰《拾遗记》的,可见“作意好奇”并非唐传奇的“专利”,在王嘉身上业已有所显露。
二、作品内容虚构
判断一部小说是否“有意”为之,还应当看其内容是实录的还是虚构的。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文学创作的虚构现象早已有之,在先秦的竹帛之上已经出现“虚妄之书”,史传文学的鼻祖《史记》也是“如实论之,虚妄言也”[14],那么在脱胎于史传文学的小说创作中存在着虚构现象自然不足为奇。小说之虚构,即胡应麟所言之“幻设语”、鲁迅所言之“意识之创造”。只不过,《史记》的虚构还是无意识的,是服务于政治人物和事件的,而小说的虚构则没有社会功利性,多是出于完善情节和塑造人物的需要。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小说家们常常以古代的“良史”为榜样,致力于“发明神道之不诬”,力求言之凿凿,“实录性”就成了这一时期小说的主要特征之一。但实际上,这不过是小说家自高身价的一种手段。小说家们很早就意识到小说和正史的不同,自高身价往往收获不大,反而束缚着他们的创作,使其才华和理想无处施展,于是他们在自圆其说的同时又给自己的创作留有余地。例如西晋人葛洪就在《西京杂记·跋》中说:“洪家俱有其书,试以此考校班固所作,殆是全取刘书,有小异同耳,并固所不取,不过二万许言。今抄出为二卷,名曰《西京杂记》,以裨《汉书》之阙。”[15]如果说葛洪“有小异同”的说法还有些保守,那么干宝的态度就更为鲜明:“虽考先志于载籍,收遗逸于当时,盖非一耳一目之所亲闻睹也,又安敢谓无失实者哉?……况仰述千载之前,记殊俗之表,缀片言于残阙,访行事于故老,将使事不二迹,言无异途,然后为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11]19很显然,干宝试图在虚与实方面为其小说创作进行辩护。他认为志怪虽然也是实录,以真实可信为目的,但失真、存疑之处在所难免,因为正史中也存在着这种情况。这种辩护显然是希望读者不要过分拘泥于历史真实,而要充分注意到自己作品的娱乐性,本质上这是小说家们在创作思想上对虚与实的认知和权衡。
具体到创作中,小说虚构的端倪早在魏晋以前就已显现。大体成书于战国中期到汉代初期的《山海经》,本是一部地理博物著作,但却充斥着虚构性和荒诞性,郭璞就说:“世之览《山海经》者,皆以其闳诞迂夸,多奇怪俶傥之言。”[16]秦汉以后的方士小说,虽出于宣扬宗教、自神其术的功利性目的,但为充分发挥作用,往往夸大其词,以至于“为数众多的方术之士,每人都伴随着一串奇闻”[8]133。到了魏晋时期,小说的虚构陆续受到作者和读者的关注。据《拾遗记》记载,张华编撰四百卷的《博物志》以后,将其献给晋武帝,但武帝认为此书“记事采言,亦多浮妄”,“惊所未闻,异所未见”[13]59,实际上就是说张华的创作中掺杂了太多自己的虚构。张华本事已不可考,后来王嘉创作《拾遗记》专门著录这一则故事,说明王嘉注意到了志怪小说中的虚构性内容,所以他自己创作的《拾遗记》也被人评价为“辞趣过诞,意旨迂阔”[13]7。
当然,魏晋时期的小说作品在虚与实的天平上还是摇摆不定的,小说家们在运用虚构手法进行创作时还不似后世那么熟练和稳定。他们常常将自己置于作品之外,偶尔跳出来说句“某年某月某日某人亲诉于我”之类的话,目的是为了证明所述故事的真实性,他们更不会像蒲松龄那样在文末满含激情地进行点评,因为这样做并不符合“补史之缺”的实录性要求。然而问题在于,在力求全面真实的全知视角的叙述模式下,作者赋予自己无所不知、无孔不入的本领,无需任何中介他们即可深入到人物内心乃至梦境,讲述其欲求、意愿,这反而显得可疑。如《幽明录》“刘晨阮肇”一篇,作者在故事的结尾交代刘、阮二位主人公“不知何所”,而他自己却又以一位知情者的口吻讲述了刘、阮二人误入桃源的前前后后,这显然是自相矛盾的。对于这种情况,作者是以“实录”的态度在进行记述,更没有明说这是一种“虚构”,不过他们似乎对此并不感到不近情理。易言之,这种全知视角与小说家们口头宣称的为正史“补缺”的动机背道而驰,但他们在具体的创作过程中却并不避讳这一问题,这或许可以看作是那个时代的小说家们在自我束缚中不断地完成着自我解放。
三、艺术手法多样
一部小说,如果是“有意”为之的话,其表现手法必定是多样化的,而一个优秀的小说家,能否熟练运用艺术手法则是其是否“有意为小说”的最好证明。综合《汉武内传》《搜神记》《世说新语》《幽明录》《拾遗记》等作品,它们在继承先秦诸子散文和两汉史传文学的基础上,艺术手法又有了一定的发展,尤其是以下几个方面表现得比较突出。
一是白描手法的运用。白描是塑造人物不可或缺的一步,简单的白描即可达到“以形传神”的目的,除了描摹人物外貌形态,肢体动作也是塑造人物的关键。说到塑造人物,不得不推重“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1]34的《世说新语》。刘义庆是白描的高手,他善于从日常生活中勾勒人物形象,而非简单地“纂辑旧闻”,机械地记录人事。比如《忿狷》第二则记述“王蓝田食鸡子”一事,“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举以掷地”,“下地以屐齿碾之,又不得,嗔甚,复于地取内口中,啮破即吐之”[17]895。对这一系列动作的白描手法,让王蓝田“性急”的特点欲然纸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相比之下,《语林》中记载此事:“王蓝田食鸡子,以箸刺之不得,便大怒,投于地”[18],就要寡淡得多。又如《贤媛》中记有“许允妇”三则,分别描写了“便捉裾停之”“作粟粥待”“妇正在机中,神色不变”[17]665-667四个动作,虽然着墨不多,但正因为有这几处白描,许允妇的镇定和勇敢体现得更加生动,动作描写在这里起到了锦上添花的作用。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任诞》中的刘伶、《雅量》中的诸季野、《巧艺》中的顾长康等等,每一位人物形象,都令人过目难忘。
二是人物对话的增多。语言的增多是作者主观能动的表现,是其有意虚构的结果。这里的语言,主要是指人物的对话。比起唐传奇中的人物对话,虽然魏晋小说中的对话少而短,多为作者借人物之口陈述事实,增添可信度,但它们也是故事情节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一些作品中还起着塑造人物的作用。例如《拾遗记》“石崇婢翔风”一则,石崇非常宠爱翔风,尝语之曰:“吾百年之后,当指白日,以汝为殉。”翔风回答说:“生爱死离,不如无爱,妾得为殉,身其何朽!”于是翔风弥见宠爱[13]60。这本是一个极其简单的故事,前人未见记载,王嘉本可以一句“翔风见宠爱于石崇”即可,但他偏要让二人对话,不仅将翔风受宠的原因和经过交代得清清楚楚,对两人之间的私密话语也描写得非常详尽。王嘉的本意或许是要证明事情的真实性,但在客观上却增加了故事的生动性,“此等段落,置于唐传奇中已毫无愧色”[12]404。而像《西京杂记》中“杜陵秋胡”一则,更是以长长的对话贯穿始终,仅翟公为秋胡辩护的一段话中就包含着“秋胡戏妻”、“曾参杀人”、“毛遂坠井”三个故事,这在当时及其后一段时期内的小说创作中都是不多见的,而《西京杂记》这么做,不仅丰富了故事情节,也更加突出人物的性格特点。
三是心理描写的进步。心理描写是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种更高级的手段。魏晋南北朝的小说作品多数缺乏“内心戏”,很少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直接的心理描写少之又少,但在篇幅较长的作品中,也能看到一些变相的心理描写,叙述者常常将人物的内心活动转变成他们的语言而加以刻画。如《搜神记》“紫玉韩重”一则,记述紫玉“意欲从君,谗言孔多。悲结生疾,没命黄垆。命之不造,冤如之何……故见鄙姿,逢君辉光。身远心近,何当暂忘?”[11]389这一段80字的歌唱,虽然不是直白的心理描写,但通过紫玉自己的歌唱将其内心的怨恨、无奈以及对爱情的向往,都表现得非常充分,不仅更具有感人的力量,而且给读者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间。类似的例子还有《拾遗记》中的翔风,在失宠后对石崇心怀怨恨,但惧其威严又不敢明说,也是借助歌唱(语言)来表达自己心情的:“春华谁不美,卒伤秋落时。突烟还自低,鄙退岂所期?桂芳徒自蠹,失爱在娥眉。坐见芳时歇,憔悴空自嗤!”[13]60南梁萧绮很敏锐地抓住了隐含在这段歌唱背后的褒贬,进一步阐释说:“是以先宠未退,盛衰之兆萌焉;一朝爱退,皎日之誓忽焉。清奏薄言,怨刺之辞乃作。”[13]61正道出了这段话中所表达的翔风的内心情感。
综上所述,创作动机属于文学创作的目的,作品内容属于文学创作的结果,而艺术手法则属于文学创作的方法,它们构成文学创作的三个维度,其中创作目的居于主导地位,决定着其他两个维度。如果同时以这三个维度去系统地考量一部文学作品,考量的结果也就具有一定的可信度。持此以衡之,魏晋南北朝时期部分小说作品的创作动机是明确的、大量内容是虚构的、表现手法也是丰富的,已经属于“有意”为之了。因此,鲁迅先生所说的至唐代“始有意为小说”的这一论断是值得商榷的。当然,鲁迅先生所指出的小说“至唐代而一变”、“演进之迹甚明”以及唐传奇“叙述宛转,文辞华艳”的特点等,不仅对唐传奇的发展状貌的概括是精确的,对唐传奇的小说史地位的认定也是极为审慎的,这些都已经为学界所公认,本文只是就唐代“始有意为小说”这一点谈谈笔者自己的思考和浅见,以就教于方家。
[参 考 文 献]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2010.
[2]王运熙,顾易生.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63.
[3]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371.
[4]彭磊,鲜正确.唐传奇“始有意为小说”辨——从小说之两类概念谈起[J].重庆社会科学,2007(7).
[5]刘金仿.唐人“始有意为小说”辨析[J].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2(4).
[6]王恒展.已始“有意为小说”——《幽明录》散论[J].蒲松龄研究,2002(4).
[7]彼得罗夫斯基.普通心理学[M].朱智贤,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421.
[8]李剑国.唐前志怪小说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
[9]沈约.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1476.
[10]鲁迅.鲁迅全集(第9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309.
[11]李剑国.新辑搜神记·新辑搜神后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7.
[12]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新著[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13]王嘉.拾遗记(外三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4]王充.论衡[M].长沙:岳麓书社,1991:53.
[15]刘歆,等.西京杂记(外五种)[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
[16]郑慧生.山海经[M].郑州:河南大学出版社,2008:10.
[17]刘义庆.世说新语[M].朱碧莲,沈海波,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
[18]王银林.汉魏六朝笔记小说大观[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5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