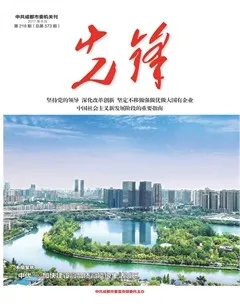丰富表达载体 塑造“天府个性”
2017-12-29王祖明
天府之国的成都,城市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成都市第十三次党代会明确提出传承巴蜀文明发展天府文化,努力建设世界文化名城,让天府文化成为彰显成都魅力的一面旗帜。发展天府文化,就是要根植于天府、魂系于天府,充分展现成都元素和原创,形成与其他地域文化有鲜明识别度的文化个性——创新创造、优雅时尚、乐观包容、友善公益。要塑造“天府个性”,建议做好两件事:一是实施成都天府记忆工程,二是打造成都故事展播品牌。
实施“成都天府记忆工程”
文化,既是精神层面的,也是物质层面的,需要有实体呈现、载体表达。习近平总书记讲,“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乡愁”是文化的记忆,“乡愁”的载体就在“山水”之间。要深入发掘天府文化的独特内涵,不断丰富天府文化的记忆内容,让生于兹、长于兹的人有更多、更深刻的“记得住的乡愁”,也让来成都、爱成都的人有全方位、多层次认知天府文化的途径。为此,建议从三方面入手,实施一项文化工程,可以命名为“成都天府记忆工程”。
第一,遗存文物保护利用。
成都有丰富的文博资源,除了四川博物院、成都博物馆集中展出的历代藏品,还有众多的民间博物馆,完全有条件打造“博物馆之城”。但文物本身是静态的,更何况很多宝物“养在深闺人未识”。挖掘天府文化内涵特质,需要深度做好文物研究和文明密码的破译、解读,把这些沉睡的文物唤醒,让博物馆里的古董“活”起来,担当巴蜀文明、天府文化的“讲解员”。
此外,成都还有金沙、宝墩和摩诃池、福感寺等文化遗址,有武侯祠、杜甫草堂、青羊宫、都江堰、青城山等名胜古迹,每一处都有很多历史故事,都是天府文化的“乡愁”,可以进行系统梳理、集萃整理,对每一处遗存都讲得出几个有代表性的、令人难忘的掌故。在此基础上,还可以通过提炼精选一批凸显文化特色的经典性元素和标志性符号,结合城市重大文化功能设施建设,着力打造一系列烙有鲜明天府之国印记的“文化地标”。可资借鉴的实例如西湖边上的断桥、雷峰塔。
另外,成都的“非遗”独具特色,是成都的一张国际名片,也是天府文化的重要表达载体,值得深入开发展示。
第二,地方文献集成汇编。
一个地方、一个时代的文化成就,既体现在名物实体上,也记录在文字典籍中。成都自古就是文化重镇,特别是“文翁兴学”以来,历代创造了灿烂的地方文化成就,并以“蜀學”的鲜明标记汇入中华文化的整体,也给天府文化厚植了养分丰富的沃壤、积累了巨大的精神财富。
在成都地方文化典籍编纂方面,有三件盛事:一是在东晋,常璩开创性撰写《华阳国志》,记述巴蜀地方历史、地理、人物等事迹。二是在宋朝,以蜀人为主体的地方士大夫编辑了一部诗文总集《成都文类》,所收诗、文、赋,上起西汉扬雄,下至宋孝宗淳熙年间,为历代骚人墨客歌咏蜀地山川灵秀、文物古迹繁盛的作品。三是在明朝,成都人杨慎编辑了一部诗文选集《全蜀艺文志》,“博采汉魏以降诗文之有关于蜀者,汇为此书”。这三部书,《华阳国志》距今1600多年,开我国地方志先河;后两部大型文献汇编,《成都文类》距今约1000年,《全蜀艺文志》距今约500年。近百年来,清末编过一部《成都通览》,浓缩了一个时代的城市记忆;3年前,成都市地方志办编了一部《成都精览》,通俗简介成都历史上的重要文明成果。但这两部书并不是文献集成。现在,我们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时代,有条件在古人成就的基础上,全面整理近500年来成都文化创造之大成,传承历史文化,弘扬现代文明,给后世再造一座天府文化的“千年宝库”。在文献题材、编辑体例上,可以不拘泥古人,可以在继承中创新,可以运用“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开阔思路,但对于历代有关成都的作品,特别是那些反映一个时期、代表一个作者的思想成就的作品,应该有心地搜集、汇总、甄别、保存,不留下历史的遗憾。
如何整理、汇编,提出几点思路:在时代方面,可以纵贯古今,从古蜀传说直到当代大事,力求构成一部完整的天府文明史大典;在内容方面,主要是写成都的、在成都写的,当然不仅仅是诗词文章,举凡凸显地方文化原创性的,都有编辑价值,使之囊括几千年的人文掌故、思想学术、山川形胜、历史风云等文化成就,同时也为天府文化的“乡愁”提供海量的记忆资源,为天府文化的创新创造提供可资启发的创意资源;在作者方面,可以是成都本土的,像汉代扬雄、明代杨慎和现当代的巴金、贺麟等,也可以是来到过成都的,自古“文人入蜀”,杜甫、陆游等都写了大量的成都诗文,当然在收录之列。至于文化载体的形式,也不限于文字作品,书画、音乐等亦可纳入。
第三,百姓文史创作征集。
灿烂的天府文化是天府之国的人们创造的,但历代流传下来的文史作品,大多是知识精英们创作的。如果说编纂成都地方文献,主要是汇集历代文化人的创作成果,那么目前建议做的这件事,则面向的是广大民众,侧重大众的、通俗的文化创造。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是鲜明彰显“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大时代,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更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作为城市的主人,每个市民都参与着城市历史的书写。鼓励市民写作个人的文史作品,意在激活普通群众的创意思维,激发蕴藏在草根民众之中的创造力,让每个人“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天府文化的创造与发展,离不开广大成都市民的参与。因此,不仅要大量地培育、发现“文化人”、文化名家,也要鼓励、号召更多的各阶层市民、底层写作者、“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讲讲他们在这个大时代里的小故事。相当于在文化事业发展上,也形成并保持一个“双创”的态势。这样既丰富了天府文化创新、包容的内涵,也发展繁荣了群众文艺事业,有利于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
对城市治理者来说,透过普通老百姓讲的和写的东西,可以多一些渠道、从各个侧面倾听百姓声音,了解市民所思、所想、所盼、所需,从而更有针对性地开展群众工作,更优质高效地办民生实事。同时,通过对面上群体和重点代表性人员的作品分析,也有助于掌握社情民意和社会思想动态,更好地行使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开展舆论引导应对。
鼓励创作百姓文史作品,也能为天府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增添现实的、鲜活的、源源不断的素材。只要管理有方、使用得法,就可将其中符合“双百”“二为”的作品,加以弘扬推广,使之获得传播展示的机会,转化为文化创造的正能量。
打造“成都故事展播品牌”
天府文化、成都故事的表达方式,还应该充分运用现代传媒手段,进行声音、影像、图画、场景等多媒体展示和传播。为此,建议在成都报刊台网等媒介上创建有鲜明天府风格、主讲成都故事的文化栏目或节目。这个栏目或节目可以综合借鉴《对话》《朗读者》《百家讲坛》《世界青年说》等,同时应有别于《李伯清书场》《小刚刚刚好》等“摆龙门阵”节目。建议命名为《方言》,主要有几点考虑:
其一,借用西汉扬雄的《方言》来取名。扬雄是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他的著作《方言》既是一部语言学辞书,也是“方言学”这门学科创立的标志。《方言》蕴含了创新创造的基因,其原创地在成都,“鼻祖”是成都人。这个品牌概念,成都拥有无可争议的发明权,是天府之國宝贵的文化遗产,可以继承创新,用好这块独一无二的“老字号”品牌。
其二,方言文化与推广普通话的关系。在全社会普及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通话,是一项国家任务,这与方言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并不矛盾。《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提出,“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护传承方言文化。”方言和普通话都是重要的文化载体。特别是像成都这样的移民城市,存在着正式场合讲普通话、非正式场合说方言的“双语”现象。既然是客观存在,当然不容忽视。在节目中,对方音方言和普通话加以系统地对比,可以帮助人们理性认识自己说的方言,提高普通话水平。
其三,方言差异与文化多元性。《方言》栏目不是纯粹用方言来表演,也不是展出各地方言的舞台,而是借用“方言”的元素来挖掘、复活文化记忆。“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方言表现出的地域、社群文化差异,保存着一个地方独特的社会心理和文化记忆,是更深刻的“乡愁”。方言差异还能引起很多诙谐、有趣的生活话题,真实呈现城市生活的多样性,给文化增添多维元素。
其四,品牌的创造性和开放性。《方言》栏目或节目,内容上完全可以突破“方言”的字面含义。比如,可引而申之,“方言”者,一方之事、各方所言;沟通各方、畅所欲言。这个“方”,可以是一个地方、一个方面、一个领域,或是表现生动、鲜活的群众语言,特定范围的新词新语,互联网的时尚用语,等等。节目策划要超出语言学范围,使之囊括社会生活万象,目的是“天府文化大家谈”,以各种方式讲述成都故事,包括历史往事、当代新事,将其打造为一个独特的文化传播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