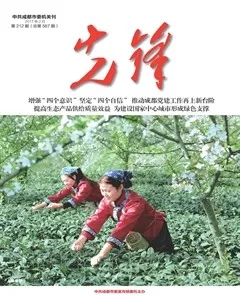印坛隐士曾默躬
2017-12-29陈沫吾
四川是孕育印人的宝地。清末民国时期的四川篆刻创作丰富,理论繁荣,印人灿若繁星,在我国篆刻史上应当有其辉煌的一页。然而,在这灿若星河的四川印坛,当今印人对成都篆刻家曾默躬先生却知之甚少。
“赫赫一大学问家也”
曾默躬(1881-1961),又名思道,字墨公,号苦行者、默居士,晚年又号大荒老人,斋号暾斋,四川成都人。出生于中医世家,早年毕业于四川省高等师范学堂。平生喜经史诗文,尤其酷爱书画篆刻。在时人眼中,曾默躬于诗文、书法、篆刻、绘画、医术、鉴赏无一不精,尤以篆刻为最。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曾默躬作为中医名师,担任了政协四川省委员会委员、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并被特聘为成都中医学院医师,参与了“全国中医学院教材”的审定工作,著有医论医案数十卷。时至今日,曾默躬声名何以湮没无闻,一是其与当时大多数文人、学者的慎重态度基本一致,不轻易出版自己的著述;二是他去世后,仅存少量书画、印章作品,以至于外间流传甚少,鲜为世人所知晓。
曾默躬一生坚持淡定于心、从容于行的做人品格,生活极为俭朴,常年穿一身粗蓝大布长衫,领口挂个眼镜盒,上系两枚汉代的五铢钱,脚穿草鞋,说一口地道的成都方言。身为大学问家却做人低调,自甘清寂,敦厚谦和,不好卖弄虚张。据曾默躬的后人回忆,先生一年四季,无论严寒酷暑或逢年过节,从无一日休息,年届80亦不懈怠。曾默躬早年与赵熙、谢无量、张大千等蜀中书画界的大家学者交往颇深。谢无量曾对曾默躬的弟子张正恒讲:“汝师,余之挚友也,赫赫一大学问家也,余极钦慕之。忆昔抗战之时,许多大学迁移川中,教授们常聚会于茶馆,研讨学术。一次,余邀汝师同往,众怪余岂可将一又土又俗的老头子带去,与彼辈西装革履洋布长衫学者之态格格不入,大伤了彼辈的雅兴。岂知待讨论到一些学问时,汝师引经据典,口若悬河,使彼辈黯然失色,一时四座哑然,惊佩难已,俯首礼拜,心悦诚服。”
齐白石称其为“神交友”
曾默躬篆刻初宗浙派、邓派,后追秦汉,继受吴昌硕、齐白石的印风影响,杂糅百家之长,在艰苦而漫长的艺术人生探索中,力求印外求印,以书入印,在商鼎、彝器、铜铭、汉砖、石刻、瓦当等文字间参悟刀法,从绘画章法、书法行气中参悟结构布局,完全痴迷和倾心于具有个性元素的写意印风创作。曾默躬的印,初看起来似乎粗疏、荒率,纵横歪倒、不衫不履,字里行间藏有几分醉意,仔细品味欣赏,却又精致、细腻,纵横有象,风神洒落,自信含蓄,以一种迥异于时流的独特识见,表达着拙朴天真中透着厚重之气的精神追求,最终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篆刻雄强遒劲,苍茫大器,古拙不雕,方寸之间意境深邃,冲切之中格调高古,魅力无穷、气象万千。
曾默躬的篆刻艺术作品风格面貌是多种多样的,但其追求的最高境界则是“刚健、笃实、光辉”。这一美学理念贯穿在他所有的书画篆刻创作之中。在书法方面,他数体皆精,尤擅章草;在绘画方面,其山水画作品宗宋元一派及清初四僧,花鸟画多以大写意为主,亦有工细之作。绘画题材常喜以松、竹、梅、兰、菊、荷以及佛像入图,每有所作皆显示出其真趣。
1933年,北平召开“全国印人展”,齐白石先生看了他的篆刻作品后,推崇备至。后来,齐白石先生在题《门人罗祥止印谱》中写道:“今之刻印者,唯有曾默躬删除古人一切习气而自立……,成都曾默躬为余神交友。”这无疑是从篆刻艺术的理念强调了曾默躬的篆刻创新意识极强,能摒弃传统印章中那些毫无生气的陈旧作派,并不拒绝对优秀传统的汲取,其不守成法的篆刻创新,正暗合了当时齐白石的艺术理念与兴趣。如今从其印谱中的一些作品看,不管是字形的表现形態、印面的空间布白、运刃的刀法等,都与齐白石有相契之处。
吴作人尊其为“一代宗师”
相较于邓石如、丁敬、吴昌硕、齐白石等大家的篆刻作品,无论在章法、刀法变化方面,还是印文的布局巧安排上,曾默躬都显示出丰富多彩的文化底蕴。尤其是从气韵天成,用刀如用笔,笔有尽而意无穷,雄浑高古,朴拙自然,豪放含蓄,刚健笃实、沉著典雅、创新意而超拔绝俗等审美要求上看,曾默躬之作更有其独到的艺术价值。曾默躬刻印从不看《六书通》,也不打印稿,完全达到了胸有成竹。刻印之前,他只略作思考,便信手挥刀而就,其布局、走刀都是在印面上随机应变,任其自然,故多天趣。这方面都较吴昌硕和齐白石不同,并得到齐白石的赞许。
曾默躬文字学功底深厚,用刀犀利爽快,无做作工匠之痕迹。他主张不刻意追求各大雅之堂的正宗流派印风,也不拘泥于明清文人的纯雅风气,无拘无束、我行我素,玩刀野逸,布局苍茫,破旧习陈法,因情生发走刀结字,不经意之作,元气淋漓,非胆识过人者难以为之。由此,曾默躬的篆刻作品用字结体浑融,笔画穿插渗透,有时印面斑驳古拙难以辨识,显得特别“杂、乱、滥”,大有黄宾虹山水画面的效果,可谓刚健笃实、元气浑仑、灿烂光辉。曾默躬独辟蹊径、标新立异的自然、苍茫、雄浑、高古的曾氏篆刻审美风格,在晚清至民国初年,我国篆刻艺术继秦汉以来出现以吴昌硕、齐白石等如林强手的第二发展高峰中,可算独占鳌头。
1958年,诸乐三教授从曾默躬的弟子张正恒处看过几枚印后,大为惊叹:“你老师的印刻得太好了,想不到四川会有这样的高人!将来有机会我一定要去拜访。”1963年,吴作人先生也从张正恒处看到曾默躬所拓印谱后,惊得瞠目结舌,连呼:“一代宗师,一代宗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