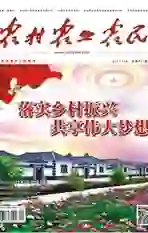城市与乡村应融合互补加速建设“人的新农村”
2017-12-28刘彦随
刘彦随
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而我国“三农”问题本质上是一个立体的乡村地域系统可持续发展问题。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为新时代我国农业农村农民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希望。
都说城市化伴有“城市病”,殊不知乡村也有“乡村病”,但二者有本质不同。前者是在快速发展进程中产生的,而后者是在逐渐衰落过程中产生的。两种病都得治,但“乡村病”更为紧迫。早在201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就指出,农村是我国传统文明的发源地,乡土文化的根不能断,农村不能成为荒芜的农村、留守的农村、记忆中的家园。
城市与乡村血脉相融、地域相连,是一枚硬币的两个面。然而,长期受“城市优先”战略的影响,城市不断扩张,经济快速增长,农民就业重在推进离乡进城和非农化转移,乡村功能重在强化社会维稳和农民生计安全保障,导致传统农业结构长期得不到改造、现代农业功能普遍得不到健全。
这样的情况就导致乡村仅仅是为了服务于城市,农业仅仅是服务于工业。我国传统体制的“三分”(城乡分割、土地分治、人地分离)弊端日益暴露,“三差”(区域差异、城乡差异、阶层差异)问题不断加大,这些都成为困扰当代中国“三转”(发展方式转变、城乡发展转型、体制机制转换)的重要难题。
十九大报告提出“城乡融合”,而不是往常讲的城乡统筹,恰恰体现了观念上的重大转变。
我国当首先致力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全面落实乡村兴人、兴地、兴权和兴产业,有效激发乡村活力、能力、动力和竞争力,系统推进城乡融合、协调、一体和等值化。当前,我国正处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重要时期,政府需要同步倡导城市化和村镇化,形成村镇化与城市化“双轮驱动”。
事实上,近10年来,国家对乡村建设的支持力度从未消减。我国针对农业农村发展问题相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也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有些乡村问题始终未得到系统考量和有效解决。其深层问题归结为“五化”,即农业生产要素高速非农化、农民社会主体过快老弱化、村庄建设用地日益空废化、农村水土环境严重污损化,以及乡村贫困片区深度贫困化。
随着工業化和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乡村衰落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劳动力要素的流失。仅在2016年,我国约有1.7亿农村人口离开家乡来到城市。有关团队经过多年实证研究发现,寻找工作和增加收入是他们进城的主要原因。在1990年至2014年间,我国农村的工作岗位减少了20%以上。
相比于乡村,城市工作的薪酬更高。
十八大以来,我国在农民工融入城市和农民工返乡创业方面都做出了很大成就。尤其在大力鼓励和支持农民工返乡下乡创业方面,据农业部最新统计显示,我国各类返乡下乡创业人员已达700万人,其中返乡农民工比例为68.5%。
但不容忽视的是,长期以来,我国农村教育、科技、卫生、文化等公共资源投入少,导致农村人口素质偏低、人才缺乏。乡村发展的本质是人的健康发展,只有农民自身素质和能力的不断提升,才能有效推进乡村的可持续发展。乡村振兴既要注重物质投入的硬件建设,更要重视提高乡村人口素质的软件建设,包括乡村基础教育、职业教育、就业培训、培智扶志等。
新时期亟须建立全覆盖的乡村教育培训体系,健全国家管治、城乡同治、村民自治的多层次乡村治理体系。要加快建设“人的新农村”,提升民众自觉学习意识、创业意愿,培养造就适应现代农业发展、新兴产业振兴、美丽乡村建设要求的新型职业农民。
对此,十九大报告中关于乡村振兴战略的论述提出了“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引发了业界的强烈关注。
土地是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然而,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带来了大量优质耕地的流失。同时,因耕地分散、细碎、小规模,农田基础设施不配套,导致耕地利用率低,一些地方有地无人耕、良田被撂荒已成为一种常态。针对土地利用低效和空间散乱的问题,围绕土地资源利用高效化和土地空间利用有序化目标,亟须科学开展推进农村土地综合整治,有序推进乡村地区组织、产业、空间“三整合”,加大对农村投资倾斜力度、内需拉动强度,塑造中国乡村振兴与城乡融合发展新动能、新机制。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区域农业与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