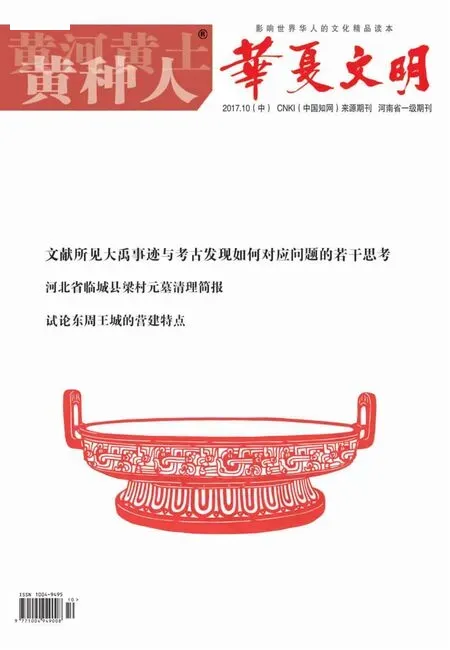文献所见大禹事迹与考古发现如何对应问题的若干思考
2017-12-26李伯谦
□李伯谦
文献所见大禹事迹与考古发现如何对应问题的若干思考
□李伯谦
一
禹作为第一个王朝国家夏的创立者,在古代文献《尚书》《论语》《左传》《管子》《楚辞》《庄子》《韩非子》《国语》《孟子》《墨子》《竹书纪年》《路史》《吕氏春秋》《史记》《淮南子》《汉书》《帝王世纪》等书中多有记载。综观这些记载,禹的主要事迹有五件:
一是帝舜时期接替其父鲧继续治水,大获成功。《史记·夏本纪》载“当帝尧之时,洪水滔天……于是尧听四岳,用鲧治水,九年而水不息……于是帝尧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摄行天子之政……乃殛鲧于羽山以死……于是舜举鲧子禹,而使续鲧之业”。《帝王世纪》载“十三年而洪水平”。
二是治水完成后在涂山庆功,大会诸侯。《左传·哀公七年》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三是受舜禅都阳城,建立夏朝。《孟子·万章上》载“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于阳城”;《古本竹书纪年》载“禹居阳城”;《世本·居篇》载“禹都阳城”;《国语·周语上》载“昔伊洛竭而夏亡”,韦昭注“禹都阳城,嵩高所近”。
四是继颛顼、尧、舜续伐三苗。《墨子·非攻下》载“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高阳乃命玄宫,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苗师大乱,后乃遂几”。
五是即位后,自己以身作则,颁立各种法令、制度管理国家。《论语·泰伯》云“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左传·襄公四年》云“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管子·桓公问》云“禹立谏鼓于朝,而备讯也”;《汉书·刑法志》云“夏有乱政,而作禹刑”。
除上所引,当然还有很多。
田野考古学传入我囯以后,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开展,与该段传说历史有关的遗址、遗物陆续发现。于是学术界开始思考:传说中的大禹事迹(包括夏朝)是否全为虚构,其中有无可信的史实素材,考古发现能否与其中某些传说相对应,又如何对应呢?
二
“九五”期间启动的国家科技攻关重大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代年代学研究”列为9大课题之一,下面设有7个专题,其中属于考古学的有4个,历史文献学的1个,天文文献学的2个,足见大家的重视。著名考古学家邹衡先生作为专家组21名成员之一,是“夏代年代学研究”课题组的组长,我作为专门负责考古学科的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之一也始终参与其事。根据各专题研究最后得出的结论,2000年岀版的《夏商周断代工程 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1]中的表述是:“夏代基本年代框架的估定包括两点:一是夏商分界,二是夏代始年。夏商分界已估定为公元前1600年……”关于夏文化的上限,学术界主要有二里头文化一期、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两种意见。新砦二期遗存的确认,已将二里头文化一期与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紧密衔接起来。以公元前1600年为商代始年上推471年,则夏代始年为公元前2071年,基本落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第二段 (公元前2132—前2030年)。现暂以公元前2070年作为夏的始年。《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即通称的繁本)经过近二十年的不断修改,近期即将完稿,查其由“文献所见的夏代积年”“夏文化遗存的发现研究与测年”“夏代天象的天文推算”整合得出的“夏代基本年代框架的估定”,表述与之基本一致,没有原则上的变化。不排除个别研究者有不同看法,但这一论断应该代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多数人的意见。
作为该课题的参加者,我同意这一论断,认为这是课题组辛勤劳动、刻苦钻研、周密思考、精心合作的结晶,是一个经得起检验的科学结论。回顾这一过程,我对开展这类课题研究有以下体会和感想:
第一,对任何学术问题,包括传说、文献在内,都应该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对文献进行可信性研究,分清楚哪些是可信的,哪些是附会的,哪些是后人添加的。
第二,对考古材料要进行缜密分期,按分期、分层、分单位釆集含碳样品并进行C14测定,建立系列样品测定基础上的考古年代分期框架,但C14测定数据只能作为历史分期的参考,不能直接用来分期,更不能用于判定文化性质。
第三,在分期基础上进行其文化内涵的文化因素分析,分清其可能的来源,进而探讨其与周邻或相关文化的关系。
第四,研究考古材料反映的社会发展阶段及其社会状况。
第五,将考古材料与文献材料及其他相关专题研究成果进行对比研究,看看其间有无可对应之处及其反映的历史事实并最后进行整合。
参加“夏商周断代工程”对我来说是极好的学习机会,使我对相关的其他学科有了较深入的了解,同时开阔了视野,学到了新的研究方法,提高了研究水平。在“夏商周断代工程”启动之前,1963年带学生到二里头实习,将我带到了夏文化考古研究领域。1986年我发表了 《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一文[2],将文化因素分析方法运用于二里头等遗址的分析,提出二里头文化是“太康失国”“少康中兴”以后的夏文化的观点,将夏文化的研究推前到了河南龙山文化。1981年我发表了《东下冯类型的初步分析》一文[3],提出东下冯类型是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类型向晋南传播发展与当地文化融合的结果的观点。1991年我发表了《夏文化与先商文化关系探讨》一文[4],提出两者是分布地域与文化特征不同、文化来源有别、发展去向不同,但又是关系密切的不同文化的观点,应该说对夏文化做了一定的研究。参加“夏商周断代工程”以后,我自认为有了不少的长进。这期间,围绕着夏文化问题我连续发表了7篇文章,均收录在2011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 《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5]中,其中重要的是,我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中“夏代年代学研究”的课题研究成果在《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6]前言中做出的“以王城岗大城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新砦’期遗存(或曰新砦文化)——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经历的三个大的阶段,约从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前16世纪,贯穿其起始至消亡的始终”的论断,完全代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多数专家的观点。
三
学术研究有阶段性成果,但很难有最终结论,夏文化研究也是一样。尽管“夏商周断代工程”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但仍有未涉及或未解决的问题。我认为,上述大禹所做的五件事中,除第五件禹“即位后以身作则、颁立各种法令制度管理国家”属于“形而上”范畴,不易把握;第三件受舜禅“禹都阳城”,已因登封王城岗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面积34.8万平方米大城的发现和 《登封王城岗考古发现与研究(2002—2005)》考古报告的出版得到证实。其他的“大禹治水”“禹会诸侯”“禹伐三苗”则是需要予以关注、认真对待的。
关于“大禹治水”,从文献记载来看,研究者代不乏人,取得了不少成果。而从环境考古入手的研究,则证实为大禹时期,即距今4000年前后,中原地区确有洪水发生,对此夏正楷等所著的 《我国中原腹地3500aBP前后的异常洪水事件及其气候背景》一文[7]和方燕明所著的 《从登封王城岗考古新发现看古史传说“大禹治水”》一文[8]已做了有说服力的说明。
关于“禹会诸侯”,我认为是大禹治水欢庆成功的重大事件,通过大会诸侯,大禹得到部众的肯定和拥戴,是帝舜禅位于禹的决定性原因。2007—201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王吉怀主持的安徽涂山禹会村遗址发掘取得重大突破,在那里居然发现了大会诸侯时留下来的祭祀台、祭祀沟、祭祀坑、燎祭面和与祭祀有关的大量陶器等遗迹、遗物[9],对此,我在《禹会村遗址——“禹会诸侯于涂山”的考古学证据》一文中予以论述[10]。
关于“禹伐三苗”,杨新改、韩建业[11]、何驽[12]、方勤[13]等多位学者已著文予以讨论,我支持他们的观点,并在《石家河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已进入王国文明阶段》一文[14]中表明了这一看法。我认为从“后石家河文化”内涵分析,确有和王城岗考古分期二、三期相类似的陶器。我没有参加过“后石家河文化”遗址的发掘和资料整理,但从初步观察的印象来看,来自王湾三期文化即通常所说的河南龙山文化的影响因素似不是主要成分。何驽在他研究“后石家河文化”即他命名的“肖家屋脊文化”论文中[15]说,异质性文化因素占58.4%,王湾三期文化煤山类型因素占41.6%。其实所谓异质性因素大部分即是由早中期石家河文化延续发展下来的因素,在时间上虽然较早中期要晚,但文化性质似乎还没有彻底改变。“后石家河文化”(此名由孟华平所首先使用,在长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 《长江中游史前文化结构》一书中首先使用)表明在时间上晚于石家河文化早中期,内涵上较前已有一定的变异,但整个性质似乎尚未被河南龙山文化所代替。在文化交互影响下出现的这种新情况、新现象如何命名,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但无论如何,这种现象表明,禹建都阳城后的确仍有伐三苗的举动,不过这样的征伐并未彻底排挤走三苗族群及其文化,而是与之融合形成了“后石家河文化”。
将考古学上发现的与“禹会诸侯”“禹伐三苗”有关联的遗存,同此前已做过研究并确认的“禹都阳城”登封王城岗大城、“羿浞代夏”新密新砦二期遗存、“少康中兴”至桀亡时期的二里头文化联系起来,在考古学上就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证据链,证明文献所记大禹事迹和夏朝历史是确实存在、符合实际的可信的历史。今后随着研究的深入,肯定会有一些增补,甚至不排除某些地方有所修正,但夏史的基本框架应该不会有大的改动。
四
C14年代测定方法是美囯化学家W.F.LibbY发明的,因这一年代学方法的革命性变革,1960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1965年以来,在夏鼐先生的倡导下,我国逐步引进和建立了常规和加速器C14年代测定实验室,做了大量考古和地质年代测定工作。“夏商周断代工程”进行过程中,专门负责年代学的首席科学家、专家组副组长仇仕华研究员倡导系列采样、系列测定方法,提高了测量精度,将常规法测量精度稳定在3%、加速器方法稳定在5%,使我国C14年代测定水平跃居世界先进行列。仇先生通过与考古课题组合作,采集和测量了大批数据,并对夏商周考古年代框架提出了自己的建议。C14测定的年代是绝对年代,但绝对年代也有一定的误差。通过考古地层学和器物类型学得出的分期是相对年代,但相对年代也有绝对意义。如何将两者结合起来得出更符合实际的年代数据,是需要继续摸索研究的问题。至于如何将C14年代与从文献记载推出的年代结合得出合理的结果,更是需要慎之又慎的。仇先生多次说过:C14测年不是裁判,C14不能决定考古专家如何分期。我同意仇先生的意见,作为一个考古工作者,应该尊重C14测年专家的劳动,应该参考C14测定的数据,但不能简单地将C14测定的结果作为判定考古学文化分期、性质的根据。在夏商文化分界的讨论中,二里头文化二、三期分界即一、二期是夏,三、四期是商,曾是一种主要的意见。而偃师商城发现以后,坚持这一观点者已经很少见到。遗憾的是,随着一些C14测量数据的披露,我们注意到,把二里头文化二、三期分界作为夏、商分界的意见,又提了出来。更有甚者,似乎有了新的C14测量数据,连二里头文化是否为夏文化也成了问题。这就把考古研究带入了误区,如果二里头文化真成了商文化,那么河南龙山文化自然就成了夏文化,但河南龙山文化的积年容纳不了据文献推定的夏的积年,夏代早期是否又要向前推到庙底沟二期文化甚或晚期仰韶文化呢?围绕郑州商城发现的大师姑、望京楼、东赵、西史村、曲梁等二里头文化城址又该如何定性,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这两处都邑又是何人所建,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岗文化的区别又该作何解释呢?牵一发而动全身,这些问题一个连着一个,在一个问题上出了差错,就会波及一大片。我觉得,提出这个问题无可厚非,但值得我们反思、值得我们认真研究的是,怎样看待C14测定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问题,在还没有拿出一个整体解决方案之前,尚不能对此前的研究结论予以全盘否定。
[1]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简本)》,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
[2]李伯谦:《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文物》1986年第6期。后收录《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
[3]李伯谦:《东下冯类型的初步分析》,《中原文物》1981年第1期,后收入《中国青铜文化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
[4]李伯谦:《夏文化与先商文化关系探讨》,《中原文物》1991年第1期,后收入《中国青铜文化分结构体系研究》,科学出版社,1998年。
[5]李伯谦:《文明探源与三代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2011年。
[6]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新密新砦——1999—2000年田野考古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08年。
[7]夏正楷等:《我国中原地区3500aBP前后的异常洪水事件及其气候背景》,《中国科学》D辑第33卷第9期,2003年。
[8]方燕明:《从登封王城岗考古新发现看古史传说“大禹治水”》,蚌埠市文广新局编印《禹会村遗址与淮河流域文明研讨会论文集》,2013年。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蚌埠市博物馆:《蚌埠禹会村》,科学出版社,2013年。
[10]李伯谦:《禹会村遗址——“禹会诸侯于涂山”的考古学证据》,《华夏文明》2016年第11期。
[11]杨新改、韩建业:《禹征三苗探索》,《中原文物》1992年第2期;韩建业:《中原和江汉地区文明化进程比较》,《江汉考古》2016年第6期。
[12][15]何驽:《试论肖家屋脊文化及其相关问题》,《三代考古(二)》,科学出版社,2006 年。
[13]方勤:《石家河:中国最早的区域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大河文明的嬗变与可持续发展》,长江出版社,2017年。
[14]李伯谦:《石家河文化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已进入王国文明阶段》,《华夏文明》2017年第7期。
(本文曾于2017年8月31日—9月1日在“登封大禹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作为发言交流,此次正式发表做了较大修改)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 赵建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