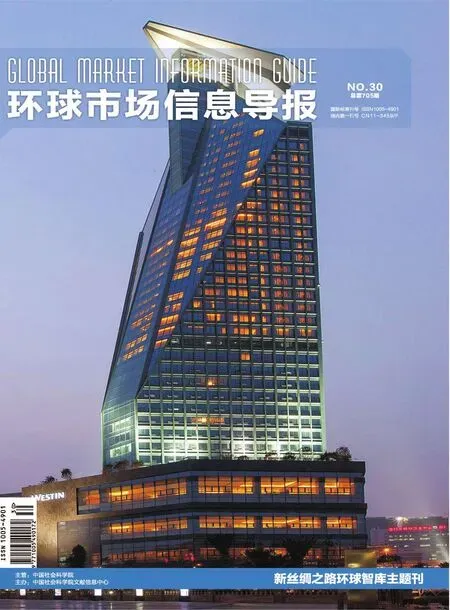试论妙善禅师与普陀山的复兴
2017-12-24陈阳
陈阳
试论妙善禅师与普陀山的复兴
陈阳
普陀山作为我国的四大佛教名山,声名显赫,然花无百日红,虽在清中后期受统治者所关注而名重一时,可近代以来已逐渐衰败,不负名山之实,而一个人的出现改变了这种局面,妙善禅师自执掌普陀以来,俢寺立法,外联海外寺友僧众,内定三统一之规,数十年的苦心经营之下,普陀山重回荣耀,如今已是佛光普照,可谓东海禅宗巨臂。然其前半生可谓坎坷,多番辗转直至普陀方觅得良木,失意的僧与失意的山相得益彰,共同走出过去迈向辉煌。
慧根深重,出家离尘
禅师俗姓吴名敬亭,江苏如皋县郭园镇人,清宣统元年己酉岁六月三十日生,兄妹四人,行老三。三岁时父亲因病辞世,整个家庭完全依赖母亲务农而维持生计,如此之下抚养四个子女成人。七岁时始读私塾,先生赞其聪慧,后因家庭经济原因,私塾就读仅四年之后,辍学居家务农,助母营生,家庭的不幸使其性情愈加坚毅。十六岁时经同乡介绍到“蒋恒兴”商店做学徒,店主蒋兰茂夫妇爱其忠厚能干,信任善待之。又因蒋郑氏虔诚奉佛,逢每月初一,十五由敬亭陪同至古刹法宝禅寺进香,妙善深受影响,自此与佛结缘。日后白天辛勤学工,夜晚则一念一拜礼观音,长年不辍。三年学徒期满之后,时年十九岁的妙善禅师感念蒋氏夫妇礼遇栽培之恩,继续留在蒋店辅助蒋氏之子,尤擅心算,闲暇喜读《三国》、《水浒》、《红楼》、《七侠五义》。两年之后,吴敬亭归家协助兄长开店,期间多人上门为其提亲,都遭其拒绝,每每夜晚则盘腿默念“南无观世音菩萨”。生活上十分节俭,乐于接济贫寒之人,不忍杀生,感念诸物生灵造化不易,见之买下放生。协助兄长经营前后历时两年,然而此与他的志趣不合,深感苦恼。
在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时值妙善禅师二十四岁,其“感于世事无常,人生多苦,而萌生出家的念头,四月十六日,留条于店中——看破红尘,决意出家,投入丹阳县地藏寺,礼寂宽和尚为师,七月,剃度于镇江焦山定慧寺的地藏殿,授之法名“心慈”,字“妙善”,视为禅宗大德龙池幻有禅师一脉六代弟子,于年底赴扬州天宁寺依让之和尚受三坛大戒”。自此,妙善禅师遁入空门,出家离尘,然而不管是因为幼年丧父助母营生而形成的坚毅性格还是私塾岁月显现出的非凡才智,抑或少年学徒历练的人生体悟,无一不彰显着这个年轻僧人的不凡。
战乱纷飞的年代,困苦无边不知光明何在的环境下,人们或扛起枪以战止战,结果是一个军阀倒下了另一个军阀又站起来了,定鼎之战遥遥无期;或浑浑噩噩,战战兢兢,惶惶不可终日,苟且存活。本来妙善禅师也应该是反抗还是忍受二者当中的一员,然而正是因为少年在蒋氏店中的与佛结缘,让他找到了另一条摆脱心中苦厄的路——皈依佛门,蒋氏可谓妙善禅师人生中的第一个贵人。
悟法高旻,始得禅机
妙善禅师圆戒後,出家的次年就来到了扬州高旻寺求法参学,“扬州高旻寺与镇江金山寺、宁波天童寺、常州天宁寺并称禅宗四大丛林,是当时长江流域四大禅宗道场之一,扬州八大名刹之一。”适时高旻寺在主持来果高僧的管理下,严明宗约,断绝经忏,惟以参禅悟道为指归,宗风大振,名闻于世。其依来果禅师参究“向上一著”,因戒行精严,参学精进,深受来果老禅师青睐,在七月十六日的“大进堂”仪式中,深感坐劳妄念,至此全消;两个月之后在禅堂加香,禅师站板之时,忽觉身心世界不知所在,有桶底脱落之感,由此大有所悟。
两年之后,27岁的妙善禅师受来果主持命进库房而任副寺,专司外出收租,几遇惊险。
又是两年之后,在高旻寺已经足足待了5年的妙善禅师,司职已位副寺,但他向道心切,不欲沉溺于寺务管理,果断暂离高旻来到了常州天宁寺——他受佛门三坛大戒的地方。无论是在扬州高旻寺的背景之下还是妙善禅师的慧根如炬中,参学名义下的他被天宁寺请为堂主。此时的妙善禅师在佛门的境遇恰如俗世所云的“春风得意”,在佛门站稳了脚跟,似乎找到了他所求的那一份安逸,正在远离他说逃避的“世事无常,人生多苦”。然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必先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经过了少年的苦其心智,时值而立之年的妙善禅师迎来的不是身体和精神状态的人生黄金期而是中年的劳其筋骨——他染上了肺病,不得不放下一切的追求,闭关方便。来果大师听闻将其急忙接回高旻,所作所为大有将主持之位传于妙善之意。
那个年代的肺病犹如今天这个年代的癌症一般恐怖,在平民百姓眼中可谓绝症,可是来果禅师没有放弃,高旻闭关养病期间,妙善肺病前后愈而复发,反反复复,长达5年的医药费用全赖来果大师解决。数年调养,1941年33岁的妙善三期肺病不药而稍愈,此时恩师来果却病倒了,他委任妙善常任高旻主持之职,为妙善传法授记,传他为临济正宗四十七世传人。而就在此之前的五月,同样位于扬州的长平寺,主持可端和尚送座于妙善,妙善大病初愈实不该过早操劳,而感念来果恩师再造之德不忍辜负恩师所托,兼扬州高旻和长平二寺住持,仅仅主持三年之后,妙善因劳心焦虑致使肺病再度复发。
恰逢此时,革命事业低潮,汪伪政权嚣张,年末汪精卫伪军整团进驻高旻寺,寺不复寺,妙善禅师不得已之下以赴扬州看病为由,挂印而逃。这一年恰逢禅师36岁,转眼间佛门岁月已度过十二载,一道轮回。在名刹高旻寺,禅师收获颇丰,不仅佛法日益精深得以契悟禅机还遇到了一个好师傅,如果说初入佛门的妙善是一匹伏枥的千里马,养在槽圈人未识,那么来果主持就是这匹千里马的伯乐,来果大师可谓妙善人生中的第二个贵人,正是在他的引导以及培养下,妙善禅师才得以有所成。来果禅师固然慧眼如炬,可妙善也同样历经考验,如果说妙善禅师在大进堂和禅堂进香时的略有所悟显露了他的慧根,有可造之才之相,让他进入了来果主持的视线,那么两年之后来果大师特许妙善为副寺进库房重地专司外出收租则是对妙善的特别考验。高旻寺的日常支出不仅有赖香客所捐,寺庙自身也必须有营生——放租以自力更生,乱世之际,放出去易,收回来难,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妙善禅师谈到这段岁月的时候,以几遇惊险概括。
当时的妙善禅师凭借着他的慧根与勤奋在佛学上已经略有所成,这是在内在的修为而言,而更为重要的则是心劫——禅师为避人间疾苦无常而入佛门,而佛渡有缘人之意并非以逃避为宗旨,避的了一时焉能避得了一世,更为主张的是直面内心,身在劫中以化劫才能根治。所以来果大师别有深意的虽让妙善监副寺却独独专司外出收租,如此又是两年磨砺,才算是真正达到了内外兼修,化解心劫,得法于高旻,深明禅机。
一苇南渡,芦山隐居
时势造僧,妙善禅师在那个年代为诸多无奈被逼,辗转流离,直至南渡东海。
一为避战祸,二为养病,妙善禅师挂印逃离了名刹高旻,一路向南,过镇江金山而不入,逢常州天宁而不语,直至杭州灵隐寺始停留数日,而后继续南下,二月直抵宁波鄞县的阿育王寺,稍作休整,两个月之后,妙善禅师从宁波渡船来到了舟山。初至普陀,妙善虽已名声在外,然其当时是出逃高旻,身份难堪,来到舟山可谓泥菩萨过江。普陀诸寺已形成了以法雨寺和普济寺两大寺为首的局面,妙善固然佛道有成,毕竟是一个外来的和尚,初来乍到的妙善大师求得是避祸与养身求法,得予其一小小的闭关之所,有一个圆照老和尚的关照,妙善彼时的身体状况正好借闭关之机得以修养,也全了钻研佛法之心,否则以其当时的健康状况实在难说困厄于寺庙杂事之中会有什么后果,佛语有云,得之我幸,失之我命,正是此理。
妙善禅师结缘普陀又是因何?禅师为避祸而挂印逃离江南名刹,一路南下为何最终选择了舟山?从地图上我们不难看出,自扬州经镇江过常州苏州,抵杭州又奔宁波,路途一番细算竟达近千里之遥,期间水陆纵横,当时又是个战乱纷飞的年代,而妙善禅师身体状况不佳,一方奔波之下来到宁波实属不易。这时摆在妙善禅师面前有两个选择,一则继续南下,再一番千里奔袭之下入福建,继而留在福建避祸或者下两广,可这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以当时的种种限制与妙善禅师的身体情况,实在难以成行再度南下;二则东渡舟山,宁波与舟山一衣带水,隔海两相望,省去了继续奔波的辛劳,而且舟山普陀也曾因康熙雍正几位帝王而盛极一时,一直盛传着观音的传说,民间盛传为海外仙山,妙善未入佛门之时就极其信仰观音,虔诚至极,正好可以再续前缘。两相比较之下,东渡舟山就成为了一个必然的选择。
一九五零年舟山全境得以解放,而妙善禅师谢绝了国民党方面共同赴台的邀请,坚决留在了舟山。后妙善禅师受共举被宗教部门指定为普陀当时两大寺之一的法雨寺代主持。此时天下初定,在新中国的三年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全国上下一片欣欣向荣,一度满目创痍的中国大地止了战乱开始恢复元气。妙善禅师新晋法雨主持,肺病多年修养大有好转,转而拜访浙江各大名山古寺,台州天台山是佛教名山,天台宗创建于此,名声可谓如雷贯耳,一九五三年禅师朝礼天台山。
一番奔走之下,禅师离“家”多年,思望之情难禁,谁曾想当年扬州一别竟是十年,而此时的来果大师已年届七旬,早在三年前就因病离寺去往上海求医,恩师病危的消息传到了妙善耳里,禅师当即前往上海,在上海的静七茅篷,师徒二人时隔十年后再度重逢。二十年前,妙善禅师还是个初入空门的小沙弥,转眼间已是东海之滨的一方门户人物。当年十月,来果大师终难敌岁月,驾鹤西去。妙善禅师固然悲痛,更是寄情普陀,回山之后领众募化一笔资金,重修殿堂僧寮,使法雨寺面目一新。
然而在那个国家统一社会却依旧动荡的年代,因为禅师对于粮食统购统销政策略有看法,在知天命之年被划分为右派,禅师因为右派之称的特殊之处,随法雨寺众僧人劳动时,被分配到古佛洞挑挖黄沙,后又被分配到佛顶山种菜砍柴,直至被“发配”到余姚芦山寺农场务农。
禅师在芦山那个小农场一呆就是二十年,除了那个生他养他的故乡,芦山竟然是他一生迄今(到一九七九年平反离开为止)待的时间最长的地方。芦山务农二十年,禅师被迫远离寺院,手中握着的不再是佛珠而是锄头,眼前也由敲打的木鱼变成了耕耘的稻田,修的是禅心,摒弃外在的形式,佛不仅是口中言,贵在心中存,彼时的禅师非农非禅,亦农亦禅。在普陀闯出一片天的禅师竟然再度被赶出寺门,与当年扬州高旻情形何其相像,可谓“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行愿无尽,重振佛国
被下放了近二十年之后,禅师等一众普陀僧人得以重换僧装重回山寺。时值一九七九年,这一年禅师年已七十又一,佛门春秋不觉间四十又七夏。此时的妙善禅师已经度过了一个平常人的大半生,以他人之言谓其行将就木之人尔,谁曾想到,前半生历经沉浮的禅师真正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一个经过“苦其心智,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的人迎来了他的“天将降大任”。
古稀之龄的禅师经众僧推选为普陀全山主持,而此时摆在他面前的是一座座文革风雨后残破不堪的普陀山寺,他要做的则是再现普陀四大佛教名山的荣光。经国家拨款支持,普陀山开始了漫长的寺庙重建工作,随后为顺应国家宗教政策,普陀山恢复佛协,妙善禅师理所当然的被推选为会长,以其威望与资历,一时执浙江佛教诸山诸寺之牛耳。在投心于继续修缮普陀山寺的工作同时,禅师还注重与国内外佛教人士和教会的沟通交流,譬如“一九八四年,应居美华人居士应行久和金玉堂的邀请,妙善禅师会同上海龙华寺的明旸主持和玉佛寺的真禅主持首次出访美国”。一年之后,修缮数年的普陀山正式对外开放,而彼时的修缮并未完全结束,直到一九八八年,普陀诸山寺基本修复,普陀山佛学院也在禅师的极力组织督办之下落成,而妙善禅师则因为这些事迹当选为浙江省政协常委,并于一九八九年当选为普陀山佛教史上第一位全山总方丈。
妙善禅师志在光复普陀之名,提出了标志普陀供奉的观音法相,建设南海观音铜像以为象征。且又佛门以济世度人为己任,广大香客信众需要关怀,故建立一所医院,名普济,取普世济民之意。进一步深入思考部署普陀佛国的明天,普陀山历经数百年,大小庵院众多,往往各自为政,寺院管理混乱,要实现普陀山的真正复兴就得解决这种沿袭已久的分散性管理模式。几经思量,禅师提出了对普陀山影响深远的“三统一”管理政策——人员统一调配,经济统一核算,修建统一进行。普陀山的重振就在这寥寥数语下日趋圆满,此后一直将其作为普陀建设的金玉良言秉行遵守,真正做到了全山“一盘棋”。
经过两年的建设,作为普陀重振的标志——南海观音铜像的建设完成,民生工程普济医院也宣告竣工,一九九七年十月三十日南海观音像开光,普济医院正式开业。自此普陀山汇八方信众,聚四海宾朋,海内外观光游人络绎不绝,一时人山人海之相,普陀尽显四大名山之风采,再现明清繁华。至此禅师十年全山主持,年近九旬,终了重振佛国之心愿,终现普陀再兴之夙愿。三年之后,新的千年纪元之际,妙善禅师在春节之后的第二十天(新年的二月二十六日)圆寂,世寿九十二岁,僧、腊戒各六十八夏。
斯寺斯僧,斯海斯音
禅师一生,长于江淮,名于江淮,然其身在东海,功在东海,顾其一生,可谓在普陀山行五要事:一、寺院管理,将历史上一向各自为政的寺政实行了三个统一;二、建立佛学院和佛教文化历史研究所;三、以法会友,广结善缘,与日韩新加坡等海外佛教形成良好关系,普陀之名驰名海内外;四、创办全国佛教界第一所僧人养老院,使出家人老有所养;五、建立新兴人文景观,如五百罗汉塔,西天铜殿,南海观音像等,招揽了大批的海内外游客。五事无一不是创举,难言绝后,但定是空前。
禅师深具禅意,普陀诸寺的统一意味犹如成吉思汗一统草原诸部,草原的统一促使了大蒙古国的诞生,为大元的所向披靡打下来坚实的内部基础,而普陀诸寺内部声音的统一,为普陀名显于世同样打下了内在的基石。而佛学院的建立则是为了在传承弘扬佛门文化的同时做好了持久战的准备,纵使他倾其一生重现普陀荣光,然身后之时则无能为力,最好的办法就是培养佛门人才,使得普陀后继有人,是所谓的传承,巍巍中华数千年的文明从未断绝,正是传承从未断绝。言对外的交流如此之繁,一谓繁华向荣二为频繁之意,也是前所未有的,古来中国的门派之见不可谓不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如此多的闭门造车,自上至下屡见不鲜,最为滑稽的不过鸦片战争之时,偌大的清廷不知英军火器舰艇为何物,惶惶如丧家之犬。而禅师久居东海之滨,看潮来潮去,日落月生,深明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道理,这是一份世界性的宽广眼界。
如此之下,我们看到的是普陀不仅矗立中华,更是达到了其余寺庙从未达到的声显海外的成就,普陀重建直至荣光焕发的那一天,海外的援助从未停止过,正是那一份胸怀使然。谈及僧人养老院的建立,更是让人不禁拍手叫好,僧人侍佛终生,然终须六道轮回,晚年生活多无家属过问,如此更需他们的家——寺院给予温暖与关怀,否则一生伴佛,年老之时却无人过问岂不让人心寒,佛亦不舍吧?禅师此举开僧人养老院设之先例,为万万僧人求得安享晚年,功德无量,当为佛门永记。诸多人文景观的设立可谓是佛门文化的具现,更是留给万世众生俗世之人精神寄托的物化,人文景观与自然景观的搭配协调也契合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市场化的策略,此举或为有心人言为好大喜功,然斯寺斯僧,斯海斯音自有待后人评价,笔者亦不妄言。
(作者单位: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