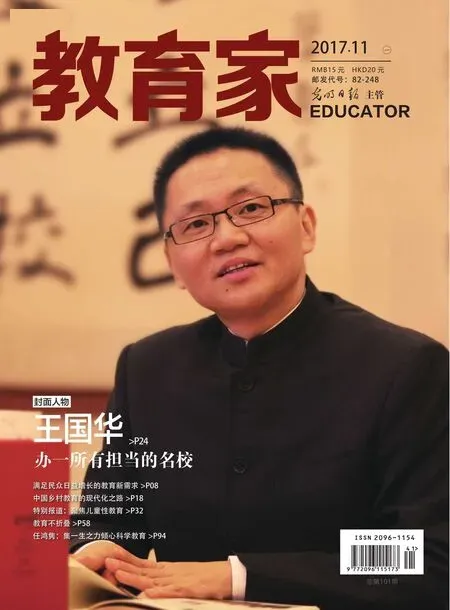任鸿隽:集一生之力倾心科学教育
2017-12-20孟令豹
文 | 本刊记者 孟令豹
任鸿隽:集一生之力倾心科学教育
文 | 本刊记者 孟令豹
作为中国科学社和《科学》月刊的创建人之一,我国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以其远见卓识意识到科学教育是增强民智、救国富国的出路,他疾呼“科学教育,此迩日学界最注重之一问题也”,他就是为我国近代科学教育的研究与发展倾注一生的任鸿隽。
科学救国
陈衡哲在《任叔永先生不朽》一文中表示:我是于1914年秋到美国去读书的。一年之后,对于留学界的情形渐渐地熟悉了,知道那时在留学界中,正激荡着两件文化革新运动。其一,是白话文学运动,提倡人是胡适之先生;其二,是科学救国运动,提倡人便是任叔永先生。
作为一位正直的爱国者,任鸿隽的科学救国思想的产生与其生活成长经历、社会环境有着紧密联系。在新文化运动特别是五四运动时期思潮的影响下,面对国家积贫积弱、人民生活苦不堪言的状况,任鸿隽留学日本时便积极参与社会政治活动,试图通过参加革命救国;辛亥革命失败后,留美学习期间的所见所闻是其提出科学救国设想的重要助推力。
1912年12月,任鸿隽以对辛亥革命有功劳的名义进入美国康奈尔大学文理学院进行学习。科学的发展给西方国家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带来的巨大影响,让任鸿隽深切地感受到科学对物质文明、人类健康、知识进步和道德建设都有巨大的作用,中西国势差异在于科学。
任鸿隽看到西方国家利用蒸汽、电力等技术,快速提高生产效率,“一日有十年之获,一人收百夫之用,交通运输,一日千里。”那些科学上拥有实力的国家在“一战”期间,正是凭借先进的科学和坚船利炮不断向外扩张。而且,科学思想在西方国家的学术、思想、行为方面也起着指导性的作用。
因此,任鸿隽意识到,在世界各国生存竞争剧烈的环境下,假如没有科学,几乎无以立国。“言近世东西文化之差异者,必推本于科学之有无。盖科学为正确智识之源,无科学,则西方人智犹沉沦于昏迷愚妄之中可也。科学为近代工业之本,无科学,则西方社会犹呻吟于憔悴枯槁之途可也。科学又为一切组织之基础,无科学,则西方事业犹扰攘于纷纭散乱之境可也。”
面对国人对科学知之甚少与漠不关心的态度,任鸿隽从1914年就发起“科学救国”运动,在1936年明确指出科学是现代国家的立国之本。他在《科学教育与抗战建国》中指出,要中国现代化,首先就要科学化,抗战需要科学,建国亦需要科学;在《关于发展科学计划的我见》中强调,当时国内的当务之急是“加速”发展科学,且发展科学应作为国家十年乃至二十年发展的首要政策,要把发展科学作为国家立国与发展的生命线。国家要把发展科学确定为“国策”,为其制定一个具体而完整的计划,做出专门的预算,委任专家担任科学事业的管理者。基于科学人才的严重短缺,国内力图科学救国,必须要“栽培自己的科学人才,造成自己的科学环境”,相关机构可重金聘请外国权威学者来华进行引导,派遣留学生到先进国家进行学习,积极培养科学人才。当然,科学救国和革命救国二者并不矛盾,因为“科学家用革命的精神,革命家用科学的知识,共同去改造社会”,二者相结合于救国运动之中。
科学思想
任鸿隽指出,科学精神至少有“崇实、贵确、察微、慎断、存疑”五个特征,并非所有科学家均具有这五种精神,但缺少这五种精神绝成不了科学家。
根本上理解科学的学理价值是任鸿隽特别看重的,在他眼里,科学是一门学问,不是一种艺术,是运用一定的方法,进行有系统的研究而获得的关于客观事物内部规律的相互关系的知识体系,其本质是事实,不是文字,其目的在于求真理,发现事物关系的法则。他曾多次深入地探讨科学的内涵: “科学者,智识而有统系者之大名。”“科学者,发明天然之事实,而作系统之研究,以定其相互间之关系之学也。”“科学是根据自然现象,依理论方法的研究,发现其关系法则的有统系的智识。”
任鸿隽在《科学研究之国际趋势》中指出科学具有永久性、普遍性、广大性与国际性等基本特性。科学的重要作用是无时无处地不存在的,对工业、实业、文化、社会、道德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不过,他强调,科学之所以为科学,不在于它的材料,而在于它的研究方法,他还异常重视科学的研究方法及其效用。
对于广义科学与狭义科学的分类,任鸿隽在《说中国无科学之原因》中指出,“广义言之,凡智识之分别部居,以类相从,井然独绎一事物者,皆得谓之科学。自狭义言之,则智识之关于某一现象,其推理重实验,其察物有条贯,而又能分别关联抽举其大例者谓之科学。是故历史、美术、文学、哲理、神学之属非科学也,而天文、物理、生理、心理之属为科学。”
创办期刊社 1915年1月《科学》月刊正式问世,公开出版。以任鸿隽为代表的五四时期留美学生组建科学团体,大力宣传科学的伟大力量,阐述科学救国的思想;译述、介绍西方科学技术,传播西方最新的科学知识。同年,任鸿隽与留美同学杨杏佛、赵元任等在美国创办了中国科学社,任鸿隽任社长。其后经改组成为一个纯学术团体,分别设立期刊编辑部编辑《科学》、书籍译著部编译图书、图书部筹设图书馆、分股委员会管理分股事宜与年会学术交流等,任鸿隽任其董事会董事长和社长。
任鸿隽在《科学》发刊词指出,“世界强国,其民权国力之发展,必与其学术思想之进步为平行线,而学术荒芜之国无幸焉”,“学术门类亦众矣。而吾人独有取于科学。”而当时的中国“不独治生,退比野人桔窳,即数千年宝为国粹之经术道德,亦陵夷覆败,荡然若无。民生苟偷,精神彤质上皆失其自立之计。虽闭关自守,犹不足以图存。”任鸿隽为民族与国家命运而疾呼: “继兹以往,代兴于神州学术之林,而为芸芸众生所托命者,其唯科学乎,其唯科学乎!”
著述与翻译 任鸿隽撰写论文、专著和译著300多篇(部),内容涉及化学、物理、生物、教育、政治、文学、科学思想、科学组织管理和科技史研究等多个方面。与科学相关的内容占据大部分,而这其中有多与科学方法、科学精神等有关。譬如,任鸿隽在《科学》杂志上发表的大量文章包括叙述科学通论的《科学与实业》《科学方法论》《科学与教育》等,以关注化学为代表的相关专门科学与科学的应用,介绍科学史的《外国科学社及本社之历史》等,倡导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与发明》《何为科学家》《发明与研究》等。
《科学》自创刊到停刊的40余年间,共发表译自外文的科技文献将近600篇。其间,任鸿隽作为主要撰稿人之一,发表了与其学习的化学专业有关且出自实验实证研究成果的译文多篇,如《科学之应用》《化学于工业上之价值》《工业上氢气之制法及用途》等。他还记录翻译了英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罗素与美国著名地质学家葛利普当时来华的演讲,并将译文刊登于《科学》杂志。
任鸿隽独立翻译出版的译著有《教育论》《现代科学发言谈》《大宇宙小宇宙》《爱因斯坦与相对论》等,与人合译出版的译著包含《科学大纲》《科学与科学思想发展史》等。
朱嘉春在《任鸿隽的科学翻译活动》中指出,除了翻译实践以外,任鸿隽还撰文讨论译名和科学翻译标准等与科学翻译密切相关的问题。其科学翻译体现着他所说的“科学精神”,对原著的选择都是经过深思熟虑后做出的。任鸿隽在译书时,并不一定将整本著作完整译出,而常常采用“编译”“节译”等手段,将原著中主题相关的内容一起翻译并结集出版。
科学教育
教育与科学之间是关联性强、相互促进的关系。科学教育可以促进科学发展,科学也决定科学教育的内容。科学教育是以全体青少年为主体,以学校教育为主阵地,以自然科学学科教育为主要内容,并涉及技术、科学史、科学哲学、科学文化学、科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整体教育。科学教育的目的是让人们掌握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学会科学方法,体验科学探究,理解科学技术与社会关系,把握科学本质,养成科学精神,全面培养和提高科学素养;培养具有科学素养的合格公民,发展社会生产力,改良社会文化,促进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在现代文明中交融贯通。
任鸿隽指出,要用科学教育来培养我们特别需要的人才。“所谓科学教育,其目的是用教育方法直接培养富有科学精神与知识的国民,间接即促进中国的科学化。科学是二十世纪文明之母,是现代文明国家之基础。所以要中国现代化,首先就要科学化”。
任鸿隽指出科学教育主要包括三种内容:普通理科教程、技术科目与社会教育中之科学宣传。推进科学教育,使之配合于抗战建国事业,达到克敌兴邦的目的需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第一,训练好的师资。提高师资训练班的训练标准,不仅要注重教材内容,还要注意教授方法。在职的中学理科教师应时时不忘自我教育,非但要每天教人,还要自己教自己,自己求长进,本着“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之意,重视自己的教业,寻求诲人不倦的乐趣。尤其对于教授法应时时加以揣摩,把干燥无味的科学知识讲授得生动活泼,使每个学生都能产生兴趣。第二,供给好的教材。为学生提供编好的教本,制好的标本,做好的仪器,办好的实验室,否则,就根本就谈不上科学教育。第三,对于推进科学教育有绝大关系者,就是科学研究工作。
任鸿隽一生致力于发展中国的科学事业,将推进科学作为毕生最主要的工作,为促进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无愧于杰出的科学事业的组织领导者之一。综合任鸿隽著作中关于科学教育思想内容,我们可以将其大致归纳为科学与教育相互关联性、科学教育重要性、科学教育内容、科学教育方法等几个方面,其中也有强调科学教育要与科学精神教育、人文教育相结合的思想内容。
这些内容为近代中国开展科学教育提供指导并指明了发展方向、规范和丰富了科学教育的内容、推动了近代中国教学方法的变革、促进了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结合等;诚然也为当前我国开展科学教育的探索与实践提供诸多经验启示。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动劳动密集型经济转向知识密集型经济的今天,对公民的科学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对科学教育的开展也提出了新的目标,科学教育的受重视程度逐步提升。任鸿隽的科学教育思想启示当今我国社会开展科学教育需要提升对科学教育的重视程度,加强跨部门协作开发科学教育资源的能力,建立与完善师资培训系统,改进与丰富科学教育的课程设置、教材内容、教学内容与方法、评价体系等。
当然,任鸿隽的科学教育思想中存在一些不足之处,譬如在一定程度上夸大科学的效用,未认识到和平稳定的国家环境对科学教育发展的巨大影响等。但作为中国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之一,任鸿隽为中国科学和教育事业呕心沥血、奋斗毕生;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教育家的科学教育思想独具魅力,闪耀着无法磨灭的光辉。

任鸿隽(1886年—1961年),著名学者、教育家、科学家。他学识渊博,著述宏富,一生撰写论文、专著和译著等身,内容相当广泛,涉及化学、物理、生物、教育、政治、文学、科学思想、科学组织管理和科学技术史等多方面。作为中国最早的综合性科学杂志——《科学》月刊与最早的综合性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的创建人之一,任鸿隽生性淡泊,不慕荣名,为促进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我国现代科学技术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注:本文部分内容引自樊洪业、张久春选编的《科学救国之梦——任鸿隽文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