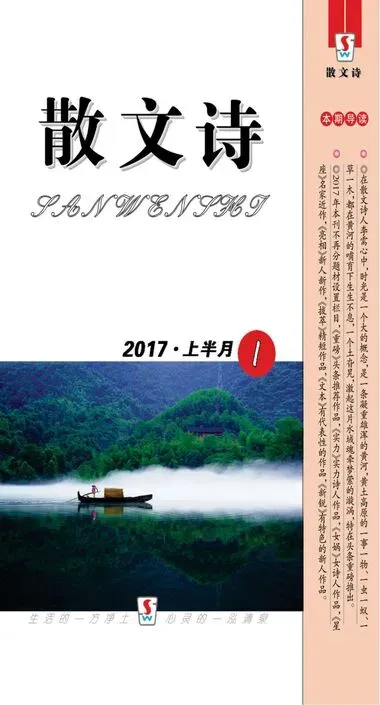柳堡风
2017-12-07江苏王垄
江苏◎王垄
柳堡风
江苏◎王垄
柳堡风
当我一次次在柳堡风中苏醒,仿佛对生命有了全新的体验。
比向往要近的村庄,好像是肉身206块骨头的集中。
没有人拒绝这自由的飞翔。
农舍保持着尊严。大地的宽容,在日月的更迭中显现。
我喜欢,在这古朴而新颖的内省里静坐。柳堡,如行走民间的华佗,用辽阔、茂盛的庄稼、草木,以及上等的流水和鸟鸣,给我煎熬灵魂向上的偏方。
每一棵树,都镌刻着地理性标志。谁要尝试去除那独特的胎记,谁就会在二十四小时之内,找不到江山,找不到万物,找不到祖先,找不到自己。
青铜从风俗里起身,矗立着乡土文明的头颅。绿色的风,吹过情感的湖泊,缓慢地驶向梦境。
仁义似金,道德如银。第四种宗教,被柳堡认可。留住千年不腐的根,这是柳堡风教会我的唯一选择。
泥土的气息,灯火的味道,老家的心跳。
方言俚语,还在繁衍。
朝霞夕光,依然延续。
柳堡的信仰,在风里传承,就像开阔的道路,带给我们更多的忠贞和陌生。
草木
做一株草木,随了柳堡的姓,叫做柳堡的名,多好!
精神从根部上升,灵气在身上集中。
不求多么高大、伟岸,在绿色的底层,与大地保持最近的距离。风,是最干净的一缕。叶子因阳光和雨水的豢养,有着青春的肤色。
生长于野外,自由在荒地。植物中的隐士,与四季同步,让节气做了生态的奴隶。
花开,或者叶落,总顺着柳堡的脾气卖萌。星星,鸟语,在林阴间斑驳。一张张和蔼可亲的面孔,安静地忽略了生死、枯荣。
依稻麦为邻,傍瓜果成友。
柳堡的草木,以缠绕的藤蔓、执著的根须,热恋着乡土。是什么让它们表现得如此神圣,我看见它们,就看见了柳堡的亲人。
善良的羞耻,可以借一双绿眼审视。我旁观着柳堡的草木,柳堡的草木却思辨着整个人间。
简单,平淡。世界归于一,命运类似草木。
俯下身体,仔细聆听柳堡草木的心跳。繁华如烟,名利虚空,唯有草木教会我们健康、爱情和欢乐的真谛。
线装的柳堡
新潮的柳堡,过于喧嚣。血压升高的夜晚,梦,都难得做圆。
那陈旧泛黄的岁月,像是一本线装的古书。我在木刻年画的志趣中,遇上了小村吉祥女巫。这怪怪的癖好,不会比喜欢一个名字,还要执著。
沉湎于老式的爱情、老套的传说,不能自拔的我,任天空被白云拐跑,河流让鱼儿抢先注册。
我甘愿在风车下打盹。野兔、野鸭,还有不可一世的田鼠,在乡村的大舞台上,或自由穿梭,或翩翩起舞。
往事的踪影,无法分配给死亡。
记忆保存的那些种子,在拓荒者胸怀,生命力蓬勃。
我只是对黑白的影像沉醉着迷,我催促彩色的镜头快快切换到过去。
早期的雨水,下在干涸的心田。那条叫母亲的河流,驮着我寓言般的乞求,在纸醉金迷的城市,向童年的乡村回溯。
耕牛,已走出田垄的画框。
越来越稀罕的野草,提醒我赶紧把柳堡的故事收购、存贮。
还有一百米的距离,我们就能走进那一首经典的老歌。但是,小学课本上的那些音符,也许下辈子才能再次触摸。
瓢
我用瓢舀起柳堡的净水,或白花花的米。
幸福,允许小容量地放纵。
这分娩于瓠子或者葫芦的家什,在母亲的手上,成为柳堡最后值得信奉的事物。
时光和梦想在瓢里积淀。一只反扣的空心的木鱼,发出铜钹的声音。一种孤寂,柳堡的缸和坛子听得最清。
与庄稼一样来自于土地以及根与藤的民歌,保持乡下孩童一般的肤色。父亲制瓢的日子,是一种过程,也像一种仪式。
游弋在回忆里的瓢,仿佛盛满了柳堡前世的月光。
我触摸过一种土老帽的气息,也领略了近似宝盒的神秘。
柳堡的瓢,以完美的曲线和外形,摇曳成和诗一样深邃的思念。
把内心的贫困舀干,瓢把它纯粹的名字,安置在我们精神的家园。
在金黄色的深处,瓢,如同诡异的符号,携带柳堡的吉祥与祝福的隐喻。我的胸怀被瓢的目光打磨得精细而宽广,那些与瓢有关的段落,贯穿于我中年的血脉——
“任凭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