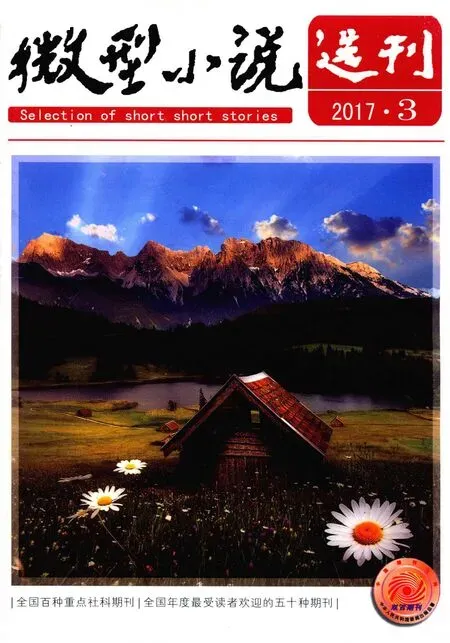假如不曾错过
2017-12-06□王溱
□王 溱
假如不曾错过
□王 溱
我杵在十字路口,手插兜,兜里的硬币闹腾着,叮当作响。
我是该先迈左脚,还是先迈右脚?一低头,却看到黑色的皮鞋上有一块白色污渍,形状奇怪,像卓别林的脸,戏谑地冲我挤鼻子。我掏出纸巾,可还没弯腰,一股人流就把我卷进了车站。
人很多,像争食的鲤鱼,挤得变了形。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留意到那块碍眼的污渍,甚至都不知道脚有没有着地。我就这样任由鲤鱼们拱着,渐渐靠近列车。穿制服的扑克脸女孩劲还挺大,歪着嘴把我们塞进车里,门紧贴着我凸起的肚腩关上了,险些夹到衣角。
“这车开向哪儿?”
我问左边穿西装的一个男的,他好像很饿,不停地往嘴里塞着三明治,从齿缝挤出来的话被食物裹着,难以辨认。
我问右边一个花枝招展的女的,她往惨白的脸上费劲地糊着粉,刚一张嘴就唰唰往下掉,呛得我直咳嗽。
“不知道,你什么时候想下就下吧。”一个声音响起,很浑厚,像喉咙内置了个扩音器。
“这车不报站?”我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但随即就紧紧闭上了,一股大蒜味迎面扑来,热辣辣的。
大蒜味来自一张镶着金牙的嘴巴,它的主人脖子很粗,嘴唇也很厚,没想到他接下来说的话却精细得像诗:“你知道吧,我有一大片地,本来是种大蒜的,现在被人种上了楼房。”
出于礼貌,我屏住呼吸“哦”了一声。
他忽然有点失落:“没了大蒜,我要唱歌给谁听呢?”
唱歌?给大蒜听?我脑里浮现出一幅很滑稽的景象:一个粗脖子的汉子扯着嗓子对着成片的大蒜吼叫,绿油油的观众们挥着长长的叶子打节拍,开演唱会一样。
他当然不会知道我在想什么,顾自说着:“我没了地,却有钱,钱也一样可以买大蒜。可买来的大蒜都死了,谁愿意唱歌给死尸听呢?”
我不知道该不该接话,幸好车到站了,吃三明治的西装男塞下最后一口,第一个冲出了车门,整个车厢的人黄蜂般嗡嗡往外冲,把我凌空挟持到车外。我抬头一看,一幢幢金灿灿的大厦高耸入云,那些人一路小跑,纷纷钻了进去。
我感到一阵头晕,又退回车厢里。
接下来的几个站,陆陆续续有人下车,每个站的景象各不相同,有热闹的棒球赛场,也有静寂的钓鱼池。渐渐地,车厢里没几个人了,那个大蒜男还在。
“你不下车?”我问。
“没到站呢。”他说,“我要去的地方是一片大蒜地,你知道吧,那是我的梦想。”
梦想?这倒提醒了我,我曾经也是有梦想的,小时候晒谷子的水泥地,就是我梦想的舞台。后来换成学校音乐室,那刷了油漆的木地板,嗒嗒嗒,嗒嗒嗒,前踢踏,后踢踏,跺跺步,再来个漂亮的拖滑,畅快极了。我还记得,为了偷偷溜进音乐室,我没少翻墙爬窗户,有一次从墙上摔了下来,到现在鼻子还是歪的。
后来,我拥有了装木地板的房子,但我的脚一动,肚腩就跟着颤动起来,更要命的是,口袋里的硬币像是要掉落出来,搞得我都不敢跳踢踏舞了。但我还是坚持把皮鞋擦得锃亮,走起来嗒嗒嗒,节奏鲜明。再后来,我把鞋钉也给拔了,在单位里老是发出嗒嗒嗒的声响总是不合时宜的,不明真相的老局长总以为有人敲门,深受其扰。
事情就是这么巧,我刚想着,车门开了,车外是一片泛着光的木地板,没有尽头,仿佛世界就是一个巨大的练舞场。我有些激动,却又拿不准了,你看,一个人都没有,我表演给谁看呢?
很快,它就消失在车门后。我瞥了一眼大蒜男,竟有点心虚,赶紧蹲下假装擦掉皮鞋上那块污渍。他看了一眼,说:“多好的皮鞋呀,怎么脏了呢?”
接下来时间似乎过得很慢,等了许久车都没有停站。我有些恐惧了,这车到底开向哪儿?
终于,车停了,外边是一条安静的街道,一排很有年代感的房子。我望了望大蒜男,终于敌不过恐惧下了车。你看,这样的街道,养老正好。
一下车我就发现了一块牌子,上面密密麻麻地写着站点名称,终点站写着—“死亡”。
我想起大蒜男,他还在执着地等着他的大蒜地呢,我赶紧查看剩下的站点,压根没有大蒜地。
我掏出口袋里叮当作响的硬币,买了支笔,在后边余下不多的几个站点中间,硬是挤上一个大蒜地站。
摸摸歪鼻子,我笑了。他即将抵达的那片大蒜地肯定是鲜活的,打着欢快的节拍。
(作者地址:广东省广州市越秀区应元路15号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 邮编:5100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