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果与驼铃
2017-12-05秦川
秦川
《红人》不是把花展示给世人看,它给人看的是果。它结出的果,不是水蜜桃,不是脆香梨,是坚果,坚硬、粗糙,然而实在。
《红人》的人物出场,犹如是在一片广袤的沙漠上,远远地从地平线的一端,出现了一个点,苍青的,模糊的,蠕动着,扩散着。先是吴阿兴、徐菊娣,然后是李洪生、小辣椒、杨书记、顾明远、王炳金,再有吴人杰、李国祥、孙雪娥、徐建秀——聚点成线,成阵,成驼队,随着一点悠扬的驼铃声,在粗礪、坚硬的朔风里,呜咽出一种苍凉、一点惨烈。写主要人物,是先有轮廓,几笔简单的勾勒,然后有点染而成的面目,慢慢近了,面目清晰了,再精描细刻,眉眼就鲜活了,身心也灵动了。写吴阿兴,出场时“他的脚陷在稻田里,人显得又矮又小的,很寒碜。‘典型的乡巴佬杨书记望一眼,蓦地在心里就下了这个评语。他好像已记不起这个曾经在公社文艺汇演中扮演过《红灯记》中鸠山的这个人了,他想让人家走,然而,在他眨眼的一瞬间,他眼前这个吴阿兴突然让他想起了田书记对提拔农村干部的要求来了:矮一点农民一点实在一点”远处的吴阿兴是个略具面目、貌似老实的农民。然后,作者将他放到政治的风浪中,将他安置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20世纪70年代)搞大寨田的历史事件中,让他沉浮,让他俯仰,让人物慢慢由远而近,走向舞台正中,在人们的眼皮底下做尽喜怒哀乐,尽显人生百态。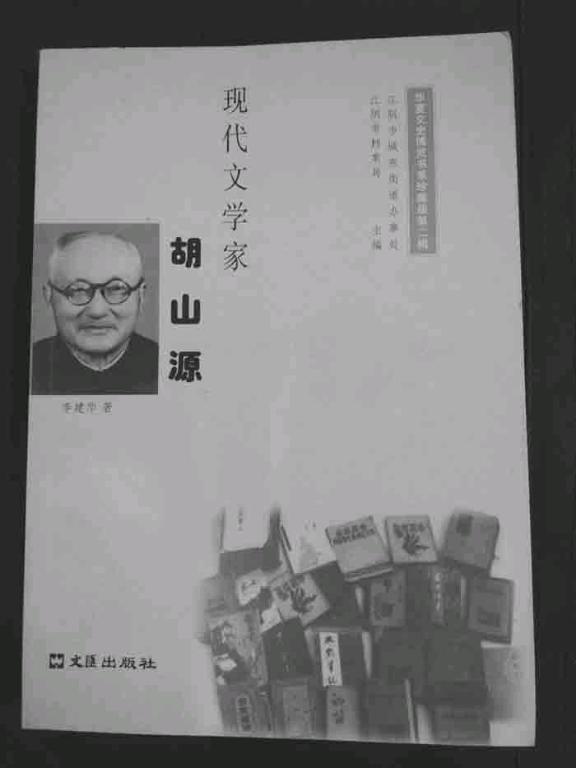
一个不失农民本色的农村基层干部形象,就这样由模糊而清晰,由浅淡而浓厚,而终于笔立于读者眼前:在人事兴废上的融通与权变、在劈山造田事件上让大家填饱肚子的一根筋、在权力争斗中的农民式的善变与狡黠,在民兵营长遇难后亲自从山上将尸体背回村里的笃诚,农民的小奸小诈、小损小坏与困难当头、当仁不让的大无私、大质朴浑然交织成一个真实、立体、可感、可触的人物形象,使得这个名为“红人”的人物身上可信地透着卑微,又于卑微中彰显着不那么响亮的理想色彩,仿佛无边沙漠中的一点驼铃,断断续续,若有若无,终究跳跃着生的色彩,闪烁着灵的光辉。
然吴阿兴当“官”是有其生存悖论作引,付出自己的代价会是一种必然,且他个性很难在尔虞我诈的官场真正得志,他与上级永远是隔着一道钢筋水泥墙的,尽管上级会用虚伪的表象作掩饰,所以当他认清楚这一点,他的整个身心就被割裂了,因之在屡屡陷入人生的困顿而终于发疯。作者拥有细腻、温情、善良与爱的呵护、关照和呼应。每当我读到他这我们安排的小说结尾:“室外阳光带着一片暖意,这是立冬后出现的头一个晴朗的好天。这样的好天,钻出土壤的麦苗,就会急着自摇枝叶往高放绿,不多久,江南这一片透明的原野,就会变得跟草原一样美丽和漂亮。”这辉映成趣意境隽永的语词充满着憧憬,行文之外仍然萦绕着驼铃的梵音,它会成为生命永恒的乐章,就像我面对春天里的第一朵花,这似锦的地方,让我感到心旷神怡。每次读,每次都让我很感动。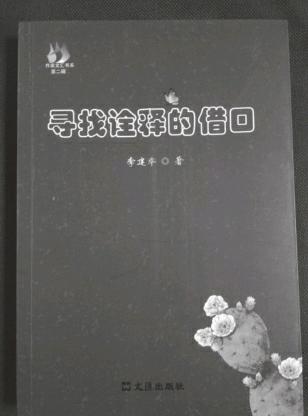
也许,只有他才能够细致入微地感觉到这悲悯之中存在的美。《红人》的本质所钻探和揭示的远不只是这些表象的令人触目惊心的题材和画面,对当代新典型的中枢神经还是有敲山震虎作用的,小说可以当作一件提案的附带,可以说,这枚坚果不是普通的坚果,是山核桃,坚硬的外壳经过一番捶打后,是富于营养的果肉。在叙事的视角上,作者挥舞着一支出入自由、仿佛跳着踢踏舞的如意笔,很快就由开篇的旁观者的视点滑入了全知视点,一会儿钻入“小辣椒”的内心,一会儿深入吴阿兴的内心,一会儿又刻画徐菊娣的内心,叙事者变成了一个全知全能的声音,连吴人杰的梦都呈现在读者眼前。同时,作者的主观意识也借着这个抽象的、全知全能的声音泄露出来:“人犯贱就犯在对某人抱有幻想。”“人的成长有时仅在一个节骨眼上,有悖常规的荒谬的卑贱的虚空的难以言喻的,从这中间悟一悟,人就长出了一节。”然后,这种过于自由的转换有时给读者的阅读也会带来一丝遗憾。
小说开头描绘了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劳动画面,是旁观者爱悦的眼光:“秧田基本栽完了,远远近近的田野,仿佛是丹青洇湿出的一幅意笔风景画……”很快,作者顿然滑入了全知全能视角:“每个人都很欣慰,为自己充当大地画家而自我感动……”这种全知视角恰恰违背了审美的真实,好比作者对着窗玻璃哈了一口气,读者看到的是窗玻璃上覆了朦胧的一层水雾,热度却有了。end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