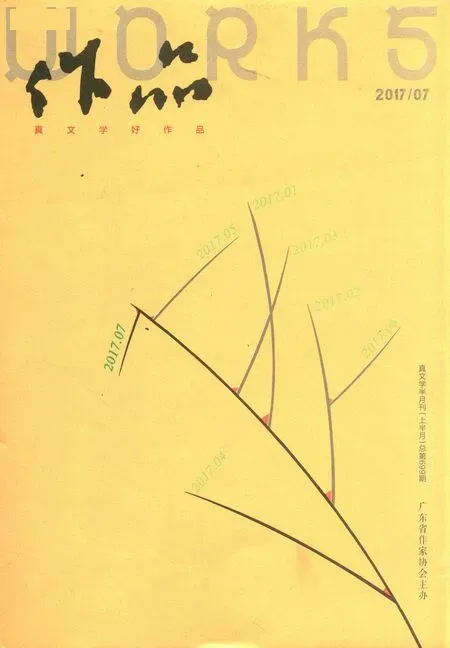抵达或归来
——简论《抵达》诗人的诗歌创作
2017-12-05文/黄涌
文/黄 涌
抵达或归来
——简论《抵达》诗人的诗歌创作
文/黄 涌
黄 涌 诗人、书评人,现供职于《安庆晚报》副刊部。
作为一本民间诗刊,《抵达》是不带有任何地域色彩的。尽管创立之初,其主要成员都落居于安徽合肥,但这本诗刊显然被赋着了更为广阔的诗歌视野。
安徽是诗歌大省,合肥因系其省会,历来优秀诗人辈出。这里曾经诞生过一本影响全国诗坛的刊物——《诗歌报》。但合肥的诗歌民刊却一向寥落,不成气候。诞生于2008年初的《抵达》诗刊,无疑填补了这一空白。
当然,就民间诗刊而言,创立很容易,坚持却是一件颇为费劲的事。《抵达》诗刊是以自身特有的美学和诗学追求,打破了时空内固定的诗歌态势,不仅在安徽,乃至在整个诗歌界烙上自己独特的印记。
十年来的漫长坚守历程,抵达诗群成员,虽然有离开的,但更多的是选择了坚守。大家都奔着共同的诗心而来,也为着共同的诗心而坚持。
所谓抵达,强调的是“抵达诗意”——当诗人不再忠实于诗意的时候,诗意往往会从我们生活中宕开,而强调“抵达诗意”,正是以汪抒、江不离、尚兵等抵达诗群创始者所希望的重新找回切入诗的正确方式。
一
汪抒是一位“老诗人”。说他老,是因为他成名较早。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已经是合肥本地远近闻名的诗人了。
本世纪初,网络诗歌论坛的出现给了很多诗人施展才华的空间,汪抒也是其中之一。汪抒很快就成了各个论坛惹人瞩目的“名诗人”。我大约也就是那时候因着论坛而陆续读到汪抒的大部分作品。
汪抒懂得如何去接近“一首诗”。他行旅、喝酒、写诗,他明了“生活不仅仅是苟且,还有远方和诗”。
汪抒的行旅诗和传统的羁旅诗相较,诗里淡了些乡愁,也少些离愁别绪,他更注重书写生命在异域空间与时间流逝中的存在感受与体验,呈现那种新异的变动不居的存在之思。用汪抒自己的话说,就是“旅行的全部意义在于另一个新我的诞生和迅速成长”。这种存在之思是对相对静止的常态的存在的回眸、观照、审视、检省、浸透、消解、提炼、重构与锻铸,是与既往的存在之思的对话与交流,碰撞与拆解。同时,在这个过程中,“我”与外界也形成了相互观照与交流。这种观照与交流,由于是发生在当下的历史条件下,凸显了主体与外界尤其是物质世界的既向往又紧张、又亲近又疏离和似了然实陌生的特征,是在实现着剧烈的异化与同化、冲突与融合,从而不断完成着新的相互建构与生成。因此,汪抒的这些诗创作冲动就迥异与传统的羁旅诗,审美特性也与之有明显的区别,表现为立意新颖,境界远阔,包蕴丰厚,诗意内核坚深。从这点上说,汪抒的这类诗是一种当代意义上的新的羁旅诗,并业已取得了可信可观的创作实绩。
汪抒饮酒诗,传承了古代的宴饮诗。所谓“珍重主人心,酒深情亦深”,古人写在觥筹交错之间,那一种人生的况味与情谊:或借他人的酒杯,浇自己心中的块垒;或劝君更尽一杯酒,一抒离别珍重的情谊,等等。
而汪抒不仅书写了诗友间的唱和,书写了曲觞流水的风流韵事,还记录了宴饮所在地的风土人情、历史地理、人文掌故……此中自然有相互欣赏的品行、才华,感染的性情、心绪,倾吐的款曲、幽情,更有一己难以言表之兴怀,无法抚平之慨然。
正如他的诗中写的:“这就是一个适于畅饮的夜晚,谁虚度谁就会永远失去。”显然,宴饮与宴饮诗一样,在他的诗人生涯中已成为弥足珍贵、不可或缺的生命存在形式,是他“在”的一种获得与确认,是具有着生命哲学的意义。
值得一提的是,汪抒上述两类诗,有一个共同的审美向度。他就是要在旅游和宴饮中努力追求和真正实现他的平民人生理想和生活情怀,追求和实现他的“与尘世融洽、随意的痛快之身”。在艺术上,既有很好的现场感,有很及物的叙事,同时,又有一种提升,将内心里的,或者更恰切地说是生命深处的某种东西,那些关乎存在的意味,加以激发,得以敞开,获得照亮与辐射。在艺术形式和表现手法上,也更多地借鉴了西方现当代诗歌,从而在审美理想与艺术范式上实现着对传统诗学的突破与超越。
读汪抒的诗作,我们能感受到诗人的眼底风光日渐辽阔,几乎无事无物不可入诗。如今的诗淡化了以往的神秘主义倾向,转入细节上的写实,或抒写关注求索,或缅怀往事,或抒写自性的苏醒,或沉静禅悟,或沉痛悼亡,或行旅送别……
在汪抒的近作里,能看到他的诗歌探索与实践向两个方向伸展,犹如夏日缓缓打开的折扇,一者深刻晦涩,自省隐秘之诗,一者是清晰直白简单朴素的日常之诗。一端是开阔圆融,叠叙铺陈,句法参差变化,注解式的句子延展司空惯见,采取引述法有英国经院诗歌的身影。而另一端则是简洁硬朗,筋骨尽显,呈现又一种截然不同的面貌,但这些诗在纹理清晰中,语义是自由跳荡的,二者同样都可以如绕梁余音,不绝于读者心耳。
汪抒自如驾驭极简与极繁的两种诗歌处理法,凸显了他在文本尝试上的义无反顾,以及语言操控上的圆融纯熟。他的诗语言能滑翔或飞散,自然随意却又异常精致。细节再现上有令人叹服的卓越才华,能赋词语以新意,特别是动词使用上愈见灵活。我确信传统诗学和语法的绳索已无法束缚汪抒语言的自由伸张之力,汪抒诗语言的外壳已开始松动,内质之香正不断溢出。
二
江不离的诗里流露出更多的是“任性”。他的诗节奏明快,口语化强,朗朗上口,给人以烟火气。
读江不离的诗,我常常对他诗中的“反诗性”有着强烈的兴趣。因为在江不离那里,而所谓的“诗意生活”,就是普通生活的一种。只有普通到生活当中,诗意才有了不寻常。江不离的“反诗性”在于反对刻意营造着“诗意”。
阅读江不离的诗歌,我们往往会产生一种想见其为人的冲动。因为,他的诗是将“现实中的人”绘进诗里。
他的诗取材自由,不附庸风雅。他勤于思考,长于隐语,想象丰富。其用语简朴硬朗,组合间常横出奇变,我们经常可以从诗中发现那些奇异的转向。
江不离的诗在看似粗疏的表达里却有魏晋士子的风雅脱俗,细读起来又难能可贵的不张狂不颓废,构思处理的巧妙幽默处让人读来不禁失笑并叹服。他的笔下似乎尽是些光怪陆离的被词语压迫变形的人与事,可事实上,那些恰恰是最逼真的现实写照,那些正是被现代化、被都市化、被物质化压抑变形了的人与事的精准再现。由此,我们不难读出江不离在他的冷淡揶揄中所包含着的对生活无比炽烈的关怀热爱,以及黑色幽默中他对现代性的深入思考。
如其他艺术形式一样,诗,始于内心的骚动。或许一开始,诗更是高度技术化的语言,而最终,诗歌所蕴藉的人类精神将倒映纸上。在平凡的一生中,我们诗人所要做的或许就是对诗歌的不离不弃,倾心于其,最终能由术而入道。
江不离的诗,直面简单而重复的人生,它不具备寓言性。它是现代社会文化的暴力形象。江不离要完成的是在表述方面的清晰性和公开性。
他生活的丰富和放纵的坦率的样子,也就是现代人对传统文化堕落的脸孔。枯燥、乏味,加上兽性,泯灭了人对尊严、崇高所铺的祭坛。人的预知和敏感也在完全模式化的现实人生面前磨得轻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写作会和传统文学产生僵持和厮杀的冲突。当然,失败者肯定是江不离。他是在收拾失败以后的残破句子。这里,来二两小酒,然后在酒意中连自身也被散落成杯杯盘盘。
人都是清醒、明智的,都是在意义的世界里教诲、被教诲者。但人抵抗不住生命的盲目性。人享受着阳光、空气,但无法享受哪怕是感冒的病痛。丰富的社会性,撕裂人的理想状态。现代抒情诗的绝望,也就是在撕裂的世界面前丧失了语言。赤裸的简单人生是靠诚实来发言。我在江不离的诗行里可以找到现代诚实世界的紧迫感。
三
很多时候,尚兵都在独自写作着。他不知道自己会写出什么,甚至不知道他的作品要呈现这个世界以何种面目。但是他明白,语言在本质上并不能呈现内心、反映思想,语言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游戏。
他拒绝向读者妥协,他知道任何的妥协都是为了向某种权威屈服。而真正的写作,从来就不曾屈从于权威。
多年的写作经验告诉尚兵,一个好的诗人应该懂得如何去使用语言。而任何轻而易举被我们可以理解的语言,都是建立在既定的语言秩序里,能够被反复复制和模仿的。在一个同质化的写作年代里,诗人还能成为语言的魔法师吗?诗应该怎样发展下去,才能形成我们这个时代独特的声音呢?
当尚兵意识到自己写作,只适合于独自探索。他渐渐明白,现实中所带来的阅读困境,是远在他写作之上的。这个世界更多的读者,关心的是诗与现实的联系,关心的是诗思想,诗与诗人的关系……当词语不再指向意义所维持的秩序,词语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尚兵的写作并不是要割裂词语的意义,而是打破语言和语言之间既定逻辑。按照罗兰·巴特的解释,尚兵一直探索的是一种可写性文本,即文本本身包涵着多重理解的可能。这是一种参与性写作,目的是让诗回到文本中来。
我们生活在一个经验和知识双重贬值的时代里。当技术的革新改变着我们对外在的世界和内在精神图景的认知,我们就会逐渐明白,任何的艺术,最终取决于我们对现实的果敢。
尚兵试图就此发明语言被命名的另一种可能性。他拒绝让语言与世界发生关系,拒绝语言与物自身保持意义上的关联。他知道,最早与世界葆有关系的就是词语,因为词语是来命名物的。词语通过语言的逻辑来解释着这个世界,而一旦词语间语言逻辑被打乱,意义也就不再出现。
在尚兵看来,局部的诗意,正是为了有效避免整体诗意化而作出的某种必要努力。因为当代读者受长期诗意驯化的影响,过于强调诗的外在品质:时代的声音,悲悯的意识,政治的鼓点,民族的心跳……而忽略了诗首先是因为语言而存在着。诗人如果没有驾驭语言的能力,其他的都会被很快缩小。
尚兵是拒绝被整体诗意化的诗人,他更关注的是语言自身所具备的诗意。所以,在写作过程中,他刻意取消整体性呈现出的诗的意义。
他觉得,当读者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他诗歌里的局部句式时,整体性的意义就被割裂开来了。
从精神本质上看,尚兵的写作源头又对应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图景:即我们更为关注的我们作为分子的存在,而非整体性的集合,但是,我们总渴望找到我们整体存在的依据。
四
作为一本民间诗刊,《抵达》诗刊里所汇聚的诗人,远远不及三位创刊者。但是汪抒、江不离、尚兵的写作无疑为诗刊奠定了总体的美学取向。以他们为原点,一批批抵达诗人聚拢在这本诗刊周围,他们以自己不同的诗歌视角的表达传达着诗意的存在。
相对来说,墨娘在诗写过程中所持有的态度是缓慢的。一直觉得,慢是一种凝结,它可以更客观地让你审视和沉淀,慢更是一种修正,能够使作品本身更趋向于理想和完美的最佳状态。作为诗人的墨娘显然是深谙诗歌“艺术思维”的真谛的,她的诗作既有优雅高格的品位,又能从生活中的普通人的“细小之事”着手,通过对平凡生活的描摹以及各种人生况味的表达与追索,彰显人性的美善,体现一个诗人的悲悯情怀,同时也使诗人自己在书写中完成了一次又一次与内心的对话。
从语言、言语角度来谈及李庭武的诗歌,我认为他的诞生状态或形成状态并非总是再现物像原有的朴素画像,他的语言有秾丽的一面,同时也有亚稳定的弹性。形成言语的额外撑出实际上会唤醒一种新的构形,那么言语在诗中就是诗人的姿态签名。反过来说,敞开主题与封闭主题的歧路呈现,两者都靠语言、言语的竞技,尤其像他写的雾霾类的诗篇,支付碎片思索的津贴无法避免,因为题材的大众性仿佛醉醺醺的步态,太多深受其害的饮酒者会踩踏它们的晃动拟像。
冰马所置身的精神流浪境地恰恰给予诗人最多的创作养分,我们同样可以清晰地读出诗人冰马的尴尬,读出当代诗歌遭遇的尴尬——她呈现的极度边缘化与附庸化的特征。有时,你不免去想,边缘或许正是诗的本相,而附庸则是对诗歌永远的误读,令人悲哀的事实之镜一面恰恰是——纯粹的诗歌总是身处媚俗的大众之外,身处权利的搏杀之外;另一面则是,繁荣之后总是衰落,身处这个经济畸形繁荣,诗歌空前衰落萧条的时代,等待每个真正诗人的不是霓虹里的狂欢,更多的是黑夜一般寂静无边的独自思索。
丁一口语化叙事诗写风格逐渐成型稳定。他近来的诗歌语言精炼,诗句简短,叙事干净,诗风质朴内敛。在他的一些优秀诗作里,他常常是将主体的情绪、意志与思想尽量隐藏起来,在看似诗歌语言的留白处,却传达出深沉而绵长的温情,具有着纯粹口语诗苍劲质朴的诗意。而他的另一些诗作,语言斩截,语句短促,爱憎分明,呈现出鲜明的直白性、置辩性与战斗性,力道强劲而锋利。他的诗写笃实坚硬,沉稳厚重,有抱朴守拙的执拗与韧性。因此,在我以为,这样的诗写倒也是自成一格,是一种本分、自觉、清醒的诗歌写作。
更年轻的诗人中,秦士红诗中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气息。不知道是什么一直在她的诗行里缭绕着,读来诡异、精灵,有时疼痛得让人暂时不得不放下她的作品。而卢顺琼的诗作一如其性格,坦率、张扬,甚至凌厉。
五
六年前的一个秋日,阳光正好。在汪抒的相邀下,我来到了合肥某处。
这是一个被“抵达”的地方。
在一个小饭店里,我们安顿下来。然后,喝酒,谈诗,谈诗人。
这是一场不期而遇的酒会,也是一场不谋而合的“诗意抵达”。诗和远方胜过了眼前一切的苟且。饭桌上,汪抒拿出了厚厚的几本《抵达》诗刊摆放在我的面前,然后继续喝酒、聊诗。我知道,那里有一种坚持,更有一种笃信。我的脑海里,忽然闪出茨维塔耶娃那句诗来:
活着,像泥土一样持续!
(责编:郑小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