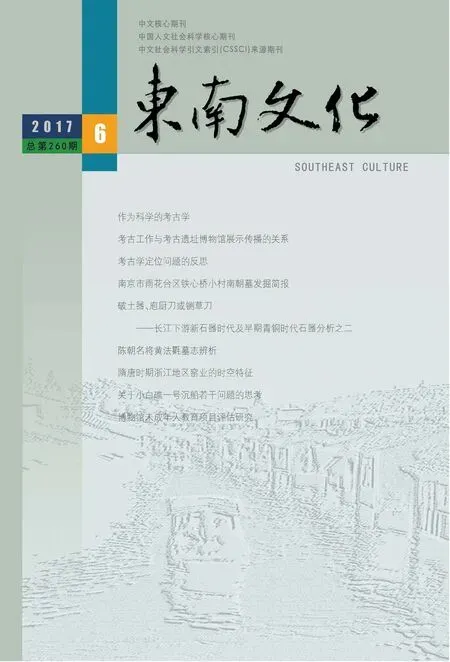湖北剧场五代杨吴墓出土木俑研究
2017-12-02赵川
赵 川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 四川成都 610064)
湖北剧场五代杨吴墓出土木俑研究
赵 川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 四川成都 610064)
湖北剧场五代杨吴墓出土了一方买地券和三件木俑,其中一件木俑身前、身后及右侧密布墨书文字。通过文字的释读和与其他相关墓葬的对比研究,可以认定带字木俑为代替生人承当殃咎的“柏人”,另外两件木俑系在地下世界侍奉墓主的奴婢。柏人具有明显的道教性质,与西汉时期的告地策存在性质上的差异。目前所见出土柏人的墓葬形制简单,规模小,墓主身份较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唐五代北宋时期墓中随葬柏人的墓主的群体特征。
湖北 五代墓葬 柏人 奴婢 道教
2000年1月,武汉市武昌区蛇山南麓湖北剧场扩建工程的施工现场发现了一批墓葬,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发掘、清理了5座墓葬及多处水井、灰沟等遗迹。M1出土1方买地券和3件木俑,其中1件木俑身前、身后及右侧布满墨书文字(图一)[1]。据买地券记述,可知该墓下葬年代为五代杨隆演武义元年(919年)。简报仅附有木俑的线图,未释读其身上的墨书文字,对同墓出土的另外两件木俑的性质亦未作任何判断。王育成先生《考古所见道教简牍考述》一文将带墨书的木俑定名为“柏人”,对文字作了释读,并指出此柏人为“道士在以天帝使者名义施行解除之法”[2]。笔者认为王先生对墨书木俑性质的判断及文字的释读大致可从,但也存在值得进一步探讨的余地。该文对另外两件木俑的性质未加分析。笔者不揣浅薄,特撰此文,以对该墓出土的3件木俑进行研究。不当之处,敬请方家批评指正。
一、柏人俑文字校读与研究
带墨书文字的木俑为整木雕成,头浑圆,头顶绘发髻,上雕一平顶冠,冠上绘有冠饰,脸部墨绘眼、鼻、口和胡须。斜肩,肩以下平直,颈部绘有衣领,胸前绘交叉人字形。木俑墨书文字自名为“柏人”,因此王育成先生将该俑定名为“柏人”是符合实际的。笔者结合相关材料,参考简报所附线图与王育成先生的释文,将木俑墨书文字订正释读如下:
天帝使者……蒿里父老、土下二千石、安都丞相、武夷王:今有……早终,令还蒿里。若……聓(婿),柏人祗当;若呼长男……[柏]人祗当;若呼长女、中女、小女,柏人祗当;若呼女聓(婿),柏人祗当;若……,柏人祗当;若呼兄弟、姐妹、如(姑)姨……女,柏人祗当;若呼□□,柏人祗当;……柏人……父,柏人祗当;若呼……[柏]人祗当;[若]呼……别亲家人口,柏人祗当;若呼四邻人口,柏人祗当;若呼□□相送男人、女人;柏人祗当;若呼师人,柏人祗当;若呼金银钱……帛,柏人祗当;若呼[复]连、注煞、破财之鬼,柏人祗[当];……大逆不孝顺,柏人祗当;若呼五空六耗、钱财不裹(果?)……当;若呼……不利……盗窃、水陆不虞,柏人祗当;[若呼]……凶祥……之……,柏人祗当;若呼一切凶万(厉)……,立是柏人祗当。如有一件不依从者,命天帝使者……有淫(阴)罪,急急如女青诏书。
墨书的大致意思是,死者下葬之后,如果与死者有关系的生人被呼讼,家中遭遇复连、注煞、破财之鬼,发生大逆不孝、五空六耗之事,或家人遇到盗贼,出入不顺利,这些不吉利的事情都必须由随葬的柏人代为承当。

图一//湖北剧场五代杨吴墓出土的带字木俑
“若呼□□相送男人、女人;柏人祗当;若呼师(?)人,柏人祗当”。“□□相送男人、女人”,即死者下葬时送葬之人。“师人”,本指占卜算卦之人,《水浒传》第六十一回,吴用假装卖卦之人给卢俊义算命,卢俊义归家之后,其妻曰:“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自古祸出师人口,必主吉凶。”[3]但柏人墨书将“师人”放在送葬之人的后面,应指的是葬师。宋张洞玄《玉髓真经》卷四《形象穴髓》“伏虎形”:“又有一种白虎形,其形龙身而虎面,龙爪而虎皮,与龙均为神物……得龙形真者,主孝子、师人、地仙有灵应之梦。”[4]而据《地理新书》记载,葬师入行是有严格限制的,且丧家也必须根据家庭和丧主自身情况选择葬师,该书卷十五《择师法》:“将葬,必先择师,师必得其人。不得其人,不可以葬。故虽巫史,必择其德行忠信、术通古今、状貌完具、识量分明者。勿使僧道行事,以其绝嗣之象,具悉受戒,[于]鬼神畏之,不享其祀。又工商杂类、流贬失官、刑伤凶恶之人,蛮夷戎狄、乐事部曲,并丑陋残疾酗酒凶服者,亦不宜用。凡葬师若不知六壬式者,名曰冒术,必受其咎,主人获殃。凡式以大吉,加师行年、主人年命,上见河魁、天刚,此师不可用也。”[5]明确对葬师的品行、职业、知识、行年等方面做了严格的规定,尤其是僧道之人不能充当葬师,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葬师的群体规模。
“[复]连、注煞、破财之鬼”。“连”字之前所缺一字应为“复”或“伏”,实际上“复连”为常见的道教用语,或别写作“伏连”,又作“重复”、“注祟”等。《道教大辞典》认为乃“结核病”之别名,又名“骨蒸病”[14]。《灵宝无量度人上经大法》卷五十三“度复连蛊注亡魂真符”:“复连死魂之对,或家亲劳疾而传,或屋宇伏尸之染,或气传而夫妇俱死,或飞尸则亲姻皆亡,号曰复连,互相缠绕。”[15]张勋燎先生认为复连即前死者的灵魂在阴司遭受折磨,不堪其苦,遂回到阳世祟害生人,索取生人魂魄代替自己受苦,以求自身解脱所致,看起来是一种前后重复的行为。伏连之说,最早源于痨瘵之类的传染病,后其范围不断延伸扩展,认为各种非传染性疾病,疾病之外的天灾人祸,如火烧、水淹、坠崖、击杀等,以及其他各种不同原因造成的死亡和祸殃,都是前死者伏连为害所致[16]。“复连之鬼”又可分为“血亲之鬼”和“其他之鬼特别是刑杀横死之鬼”[17],但其害人的方式都是一样的,即按照注鬼自己同样的死亡方式祟害生人以其作替身。虽然复连最终会对生人导致种种不利,但此处“复连之鬼”与“注煞、破财之鬼”相比则各有侧重,不可混一。
“……盗窃、水陆不虞”。王育成先生释读为“盗贼水陆不虞”,“窃”字摹本残泐不清,然根据残存笔画与文意,可辨识其为“窃”字,而非“贼”。此处“若呼”后面的文字应系呼讼所产生的结果,“……盗窃”和“水陆不虞”,前者指遭贼窃之灾,后者言路途不顺,显然是两种不同性质的灾害,因此应该断句为“……盗窃、水陆不虞”。江西省吉安县敖城乡泮圹村北宋开宝七年(974年)石室墓出土的石质柏人,身上刻文有“水、火、盗贼欲至,仰百(柏)人斩之”[18],即出现水、火灾害,遭遇盗贼,都希望墓中柏人能一并抵挡、斩杀,以保安宁。因此,“[复]连、注煞、破财之鬼”、“大逆不孝顺”、“五空六耗钱财不裹(果?)”、“……不利……盗窃、水陆不虞”、“……凶祥……之……”、“一切凶万(厉)……”虽都放在“若呼”之后,看似作为征呼的对象,但从义理上讲应为征呼所产生的结果。
江西鼓泽县北宋元祐五年(1090年)墓柏人券:“恐呼生人,明敕柏人一枚,宜绝地中呼讼。若呼男女,柏人当。”[19]柏人放在墓中以替代生人,“宜绝地中呼讼”。到后来,由于征呼的范围从生人延伸至世上一切跟生人相关的人和物,因此柏人的替代范围也就相应地扩大。江西南昌北郊唐昭宗大顺元年(890年)熊氏十七娘墓中出土柏人券:“坪(地)中神呼生人长男、长女、中男、中女,并仰柏人当知(之)。地中有神呼主人大□、小□行年、本命、六田(甲),并仰柏人当知(之)。地中有神呼主人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等者,并仰柏人当知(之)。[地中有神呼]奴婢、牛马六畜,并仰柏人当知(之)。地中有神呼长孙、中孙、小孙、曾孙、悬(玄)孙本命□□久亲……行年者,一切已(以)上,并柏人当知(之)。”[20]被“征呼”的对象更多,而柏人也一并当之。湖北剧场出土的柏人俑身上的文字虽然部分漶泐不清,但仍可从前后文所记内容大致将征呼的对象分为与死者有关之生人、财宝、恶鬼、灾难,而放置柏人的目的就在于替代生人承当复连征呼、守护财宝、抵御恶鬼和灾难。本件柏人俑身上文字中新出现了送葬之人、葬师,就连是盗窃、“复连、注煞、破财之鬼”也在其列,这是以往发现材料中所少见的[21],值得注意。
二、无文字木俑研究
除墨书柏人之外,湖北剧场M1还出土有木质买地券1方以及男俑、女俑各1件。木俑皆为扁圆整木雕成。女俑小头,无耳,颈与肩连成一线,身着长服,两袖合于胸前,高26.2、厚2.7厘米;男俑头较女俑大,左耳残缺,颈与肩区分明显,两袖合于胸前,高26.7、厚2.9厘米。像该墓柏人1件、木俑2件、买地券1方的随葬器物组合在湖北、江西等地区的晚唐五代北宋墓葬中亦有所发现。
湖北武昌阅马场杨吴墓M1随葬品中有买地券1方、木俑2件。木俑用一圆杉木一剖为二而成,剖面作俑的背面,正面利用杉木的圆面稍加刻饰显出首身性别之分,制作简单,人形抽象。男俑,头戴高帽,长28.2、宽4.8厘米。女俑,头梳发髻,身穿长裙,脸部刻出线条表示眼、鼻、口,长26.4、宽6厘米[22]。该墓与湖北剧场所出无字木俑一样,均是一男一女,且男俑比女俑高。两墓均为竖穴土坑墓,所出买地券文字亦基本一致。阅马场杨吴墓M1发掘简报虽未附木俑照片和线图,但从对器物的文字描述来看,其形制应与湖北剧场M1所出的男女俑极为接近。
江西南昌晚唐熊氏十七娘墓(890年)为竖穴土坑墓,棺全长3.1、宽0.7、高1.6米,墓中出土木质柏人1件、竹侍俑2件、木质买地券1方,还出土竹武士俑2件[23]。两件竹侍俑照片较模糊,难以分辨其是否是一男一女的组合。
江西吉安敖城乡泮圹村北宋墓(974年)为长方形石棺墓,墓室长 3.19、宽 1.09~1.24、高 1.34米,墓中出土石质买地券1方、石质柏人1件、侍俑4件,此外还出土有伏听俑1件、文吏俑8件、青龙1件、白虎2件、玄武1件、朱雀1件、卧虎2件、鸡1件,皆石质[24]。四件侍俑高矮不一,制作简单,其年龄、性别均难以判断。江西两座墓葬年代相距有84年之久,但柏人、买地券、侍俑的随葬品组合却依旧未变,这种组合与湖北两座五代杨吴墓的情况极为相似,应加以综合考虑。
关于柏人和买地券,目前学术界已经有比较细致的研究成果[25],但对同时出土的侍俑则鲜有涉及。这些侍俑是跟同出的柏人俑一样也用于代替生人受殃,还是仅仅是表示让死者在另外的世界能享受侍奉的明器化俑?是否还有其他的宗教意义?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加以考虑的。
上海图书馆藏敦煌文献017b(以下简称“上图017b”)《葬事杂抄》:“准姓宜用今月廿五日,右检前件,日合金鸡鸣,玉狗[吠],[上下不]呼。木奴欹,木婢簸。此日殡葬、斩[草],[神]灵安,宜子孙,大吉。”[26]明吴国仕辑《造宗命镜集》卷六《用日法》:“葬埋日要合鸣吠。歌曰:‘识得山家合日家,冢瓦婢其支(簸)木奴欹,分金更与山家合,自免凶灾发福多。’凡葬日辰,要与坐向相合,阴阳相符,分金合得坐向,乃吉。更遇大葬,所宜山向为鸣吠尤吉。若葬日不与山家相值,分金不相干渉者,终难发福。”[27]“木奴欹,木婢簸”跟前面“金鸡鸣,玉狗吠”一样,都是就为丧家选择下葬吉日的标准而言的。隋唐五代宋元时期的墓葬中较常见金鸡、玉犬随葬,并多以陶俑的形式出现,也发现有用零星的木板画[28]、阴线刻砖[29]等形式。与此同时,金鸡、玉犬亦常见于风水堪舆文献的择日卜葬之术中,除前揭之上图017b《葬事杂抄》之外,P.2534《阴阳书》卷第十三《葬事》:“丙午日,水,成,地下丙辰,金鸡鸣,玉犬吠,上下不呼,此日葬及殡埋,神灵安宁,子孙富贵。起殡、发故、斩草、起土、除服,大吉。”[30]笔者目前所见,传世的堪舆风水文献如上图017b《葬事杂抄》将木奴、木婢与金鸡、玉犬用作选择吉日的标准者,并不多见。考古发掘的墓葬中具有人形特征的俑类在种类和数量上都相当可观,人们往往忽略了对其可能存在的具体不同的意义或功能上的深入考察。在墓中放置金鸡、玉犬的同时,又放入柏人与侍俑的做法,文献也偶有记载。明陈继儒辑《捷用云笺》卷六《祭清明文》:“今日具陈祭礼,炷上明香。……再请……墓内金鸡、玉犬神君,柏人神君,木奴、瓦婢神君……再动真香,普同供养。”[31]就考古发掘情况来看,唐宋墓葬中金鸡、玉犬与侍俑伴出的现象也比较常见,兹不一一例举。
上图017b《葬事杂抄》中的“木奴”与“木婢”,分别在“奴”、“婢”前加一“木”字,指出了奴婢应为木制,并非当时社会生活中真实存在的奴婢,而是木制明器。“奴”为男,“婢”为女,即侍俑可分男女,将其放于墓中应是为了让它们在地下世界侍奉墓主人。当然,既然奴婢是木质,也就不可能真正地起到侍奉死者的作用,只能是当时人们对人死后在地下世界生活的一种期许。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群麴氏高昌(460—640年)的墓葬75TKM99墓道中出土3件木俑,包括2件男俑、1件女俑。一件男木俑(75TKM99:15)很粗糙,仅刻出头、身、腿,粗眉大眼,上身墨绘,身上墨书“奴白头内”几字,可知该木俑应为放置于墓中的男奴明器;女俑(75TKM99:14)长脸,披发,身着长裙,裙上部为白色,下部为粗黑色和红色相间的竖条,应即女婢[32]。巧合的是,湖北剧场M1和阅马场杨吴墓分别出土的两件无文字的木俑也均为一男一女,当属“木奴”与“木婢”无疑。晚唐五代宋元墓中常随葬俑类明器[33],材质包括陶、土、砖、石、木、竹、竹、铁等,虽然上图017b《葬事杂抄》只是交代了“木奴”和“木婢”,没有提到其他材质的俑类,但我们在具体分析墓中出土木俑的功能时不能仅仅局限于其材质,还要对器物组合等方面加以考虑。如江西南昌晚唐熊氏十七娘墓出土木质柏人1件、竹侍俑2件、木质买地券1方,虽然侍俑是竹制,但从器物组合和功能分析,亦可归于上图017b《葬事杂抄》所指的“木奴”与“木婢”。
就本文所讨论材料而言,虽然柏人和两件侍俑都是由木制成,形制也较接近,但两者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张勋燎先生在系统研究墓葬中所出代人材料后认为,柏人乃道教代人性质的遗物,它与中原和西北地区早期天师以人参或桐人、柏人持代生人的习俗有一定渊源关系,其所承担义务除了汉晋时期习见的杜绝冥讼引起的鬼神传呼死者家中生人造成的危害外,尚包括为死者家中生人子孙罗致各种福运[34]。黄秀颜先生认为,墓中放置柏人的目的“大概就是为了代死者受谪,承当冢讼征呼”[35]。就目前发现的柏人而言,除张勋燎、黄秀颜两位先生所揭示之意义外,尚未发现其有侍奉死者的功能。因此,笔者认为湖北剧场M1、阅马场杨吴墓以及江西南昌熊氏十七娘墓中出土的未带文字的人形木俑应为用于在地下世界侍奉死者的侍俑,与代生人承当殃咎的柏人在性质上是不一样的,是不能混同的。相类似的情况亦见于新疆等地发掘的麴氏高昌(501—640年)至唐代的墓葬中,如吐鲁番高昌延寿十年(633年)元儿墓葬随葬衣物疏中明确记载有“锡人十□,奴婢十具”[36],将具有代人性质的锡人与奴婢并列,亦可证明两者在当时并非一回事。因此,在分析对墓葬出土俑类的性质、功能时,应充分考虑到材质、形制以及有无文字等因素,不可因为形制相似就将性质和功能不同的俑贸然归为一类,柏人和普通侍俑形制、大小较为接近,制作均较粗糙,导致我们很容易将两者混淆,这是在研究晚唐五代到宋元墓葬出土俑类时需要注意的。
三、相关问题讨论
简报指出带字木俑身上的“文书性质就是一篇与买地券相异的‘告地丞书’”[37]。笔者认为,柏人墨书文字在性质上与买地券文字相异之观点不误,但言之为“告地丞书”则仍有进一步探讨的余地。
首先,本文所讨论的柏人的部分墨书文字漶泐不清,前面部分可释读为“天帝使者……蒿里父老、土下二千石、安都丞相、武夷王”。陕西户县朱家堡东汉墓(133年)出土解注瓶朱书文字为:“阳嘉二年八月己巳朔,六月甲戌,[直]除。天帝使者谨为曹鲁伯之家移殃去咎,远之千里……”[38]。山西某地出土陶瓶朱书文字作“熹平二年,十二月乙酉朔,十六日庚申。天帝使者告张氏之家三丘、五墓、墓左、墓右、中央墓主、冢丞、冢令、主冢司令、魂门亭长、冢中游击等,敢告丘丞、墓伯、地下二千石、东冢侯、西冢伯、地下击犆卿、耗(蒿)里伍长等:今日吉良,……”[39]。张勋燎先生认为,“天帝使者”应该是“行术的‘道中人’、‘道行人’神化自己,自封为天帝代表者的自称之词”[40]。具体到本文所讨论的柏人而言,其身上的墨书也应该是以天帝使者的口吻写成的,后面的蒿里父老、土下二千石、安都丞相、武夷王等神祗是“天帝”发号施令的对象。西汉时期“告地丞书”多为死者自告[41],或与死者相关的有一定地位之人[42],或如台湾林富士先生所言之“巫”[43]。此时道教还未产生,且目前也尚未发现年代可早至西汉时期的“天帝使者”的材料,因此告地策的告者与天帝使者在性质上是不同的。
其次,墓中放置告地策系向地下鬼神通告殁亡之人掩埋下葬,并祈求得到地下鬼神接纳死者的户籍,使死者在地下安宁[44]。如湖北荆州高台秦汉墓M18告地策“谒告安都,受名数,书到为报,敢言之”[45],荆州谢家桥1号汉墓告地策“谒告地下丞以从事”[46]。而晚唐五代宋墓中放置的柏人则主要是用于代替生人承受来自地下的征呼,使之免受殃咎。虽然两者都带有保佑死者安宁的目的,但是在具体方式上是有差别的。此外,柏人还能替代生人免受因冥讼引起的鬼神传呼死者家中生人而造成的危害,这也是告地策所不具备的。因此,告地策和柏人两者在性质上有着明显的差异。
目前随葬柏人的晚唐五代宋元墓葬发现得不多,且全部分布于南方地区,柏人一墓一件,除个别刻写在石板上,其余均为木质,不见过去用桐、松以及铅、锡等金属材质的例子。这种转变的发生,张勋燎先生认为一是由于柏木防腐性能好易于保存,二是跟道教观念中柏木受天地之灵气、具有辟邪致福的作用有关[47]。
相对于柏人,这一时期墓中随葬侍俑的情况较为常见。侍俑不限于木质,还发现有石、竹、陶等材质者。侍俑从外貌的年龄特征上可见有老少之别,形象上看均为汉人。各墓随葬数量不一,但多呈偶数形式出现。湖北武昌两座杨吴墓出土的侍俑均为一男一女,但有的墓葬出土侍俑则难辨其性别。有的墓葬男女侍俑数量并非各仅1件。文献还记载有出土两件女俑者,唐牛僧孺《玄怪录》:
国初,有曹惠者,制授江州参军。官舍有佛堂,堂中有二木偶人,长尺余,雕饰甚巧,丹青剥落,惠因持归与稚儿。方食饼,木偶引手请之。儿惊,报惠,惠笑曰:“取木偶来。”即言曰:“轻红、轻素自有名,何呼木偶?”于是转盼驰走,无异于人。惠问曰:“汝何时物,颇能作怪?”轻素曰:“某与轻红是宣城太守谢家俑偶。当时天下工巧,皆不及沈隐侯家老苍头孝忠也。轻素、轻红,即孝忠所造。隐侯哀宣城无常,葬日故有此赠。时轻素圹中方持汤与乐家娘子濯足,闻外有持兵称敕声。夫人畏惧,跣足化为白蝼。少顷,二贼执炬至,尽掠财物。谢郎时颔瑟瑟环,亦为贼敲颐脱之。贼人照见轻红等曰:‘二明器不恶,可与小儿为戏具。’遂持出,时天正二年也”[48]。
两件木俑轻素、轻红均为女俑,由沈约家的工匠制作,后赙赗给宣城太守谢朓随葬,在墓中侍候谢朓的冥婚之妻乐氏,两俑于天正二年(553年)为盗墓贼盗出。谢朓死于永元元年(499年),牛僧孺记载江州参军曹惠与两俑之事发生在唐朝初年,距两俑下葬已一百多年。牛僧孺生于大历十四年(779年),卒于大中二年(848年),有学者认为《玄怪录》乃其早年作品[49]。该书所记之事虽玄怪诡谲,然至少能部分地反映中晚唐时期人们的精神观念。轻素、轻红两件木俑与本文所讨论的一男一女两件木俑在性质上是一样的,都是为了在地下侍奉墓主而被放入墓中。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发现的出土柏人、买地券和侍俑的晚唐五代宋元墓葬形制简单,规模小,除北宋彭司空柏人券所在墓葬的情况不详外,其余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或长方形石椁墓,墓葬长度均在4米以下。葬具以木棺为主,个别墓葬以石椁为葬具。葬式均为土葬,未发现有火葬。墓内随葬品少,种类单一,除了文中所列器物之外,有的墓葬还随葬有少量的其他俑类以及铜镜和铜钱等。墓主有男有女,为当地较富裕的平民。而该地区同时期的一些等级规模较高的墓葬,除个别出土有买地券和侍俑外,尚未发现有出土柏人者。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晚唐五代北宋时期在墓中以柏人随葬的习俗主要流行于社会地位低下的平民群体中。
综上,湖北剧场M1出土的3件木俑中,带墨书的一件木俑应为代替生人承受复连殃咎的柏人,另外两件木俑系用于在地下世界侍奉墓主的奴婢。柏人具有明显的道教性质,与西汉时期的告地策存在性质上的差异,但两者之间也有一定的关系。目前晚唐五代北宋墓葬发现的柏人均为一墓一件,大多为木质,所在墓葬形制简单,规模小,墓主身份较低。目前发现的明确为五代时期的墓葬数量不多,湖北剧场M1年代清楚,保存相对较好。如笔者以上推断不误,则该墓出土的木俑和买地券为我们研究五代时期南方地区社会中下层人群的丧葬观念和对地下世界的认识,以及道教在南方地区的传播情况提供了新的材料。
[1][37]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武汉市博物馆:《湖北剧场扩建工程中的墓葬和遗迹清理简报》,《江汉考古》2000年第4期。
[2]王育成:《考古所见道教简牍考述》,《考古学报》2003年第4期。
[3]明·施耐庵:《水浒传》下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第810页。
[4]宋·张洞玄:《玉髓真经》,《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一〇五三册,“子部·术数”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84页。
[5]宋·王洙:《重校正地理新书》,《续修四库全书》编纂委员会编《续修四库全书》第一〇五四册,“子部·术数”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19、120页。按:“鬼神”前“于”字漶泐,此据集文书局影抄金明昌三年(1192年)本补。参见宋·王洙等《图解校正地理新书》,集文书局1985年,第481页。
[6]周祖谟:《广韵校本》,中华书局2011年,第53页。
[7]黄征:《敦煌俗字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552页。
[8]黄征:《魏晋南北朝俗语词考释》,《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3期。
[9]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第5卷,中华书局1997年,第863页。
[10][20][23]江西省博物馆:《江西南昌唐墓》,《考古》1977年第6期。
[11][24]王吉永:《吉安发现一座北宋纪年墓》,《考古》1989年第10期。
[12][19]彭适凡、唐昌朴:《江西发现几座北宋纪年墓》,《文物》1980年第5期。
[13]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37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204、205页;郎俊彦:《北京图书馆藏北宋“彭司空买地券”考释》,《四川文物》2008年第2期。
[14]中国道教协会、苏州道教协会编:《道教大辞典》,华夏出版社1994年,第466页。
[15]《道藏》,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册,第912页。
[16][40]张勋燎:《东汉墓葬出土解注器和天师道的起源》,张勋燎、白彬编《中国道教考古》第1册,线装书局2006年,第49—51、365页。
[17]刘仲宇:《道教法术》,上海文化出版社2002年,第73页。
[18]王吉永:《吉安发现一座北宋纪年墓》,《考古》1989年第10期。
[21]江西彭泽县湖西公社湖西大队北宋石椁木棺墓出土的柏人文字中有:“若呼□师名字,柏人当。”由于简报所附器物图版文字不全,且不清晰,故此处“□师”是否也是指的葬师,姑且存疑。见彭适凡、唐昌朴《江西发现几座北宋纪年墓》,《文物》1980年第5期。
[22]武汉市博物馆:《阅马场五代吴国墓》,《江汉考古》1998年第3期。
[25]关于唐宋时期墓葬出土柏人研究,笔者所见,较重要的成果有:王育成《中国古代人形方术及其对日本的影响》,《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97年第1期;张勋燎《墓葬出土道教代人的“木人”和“石真”》,《中国道教考古》第5册,线装书局2006年,第1446页;余欣《厌劾妖祥:丝路遗物所见人形方术探赜》,余欣《中古异相:写本时代的学术信仰与社会》,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关于唐宋时期买地券的研究,学术界多集中于针对材料的选辑、券文文字释读和相关问题的讨论,综合性的研究较缺乏,可参见〔日〕池田温《中国历代墓券略考》,《东洋文化研究纪要》第86号,1981年;陈柏泉《江西出土买地券综述》,《考古》1987年第3期;陈柏泉《江西出土墓志选编》,江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韩森著、鲁西奇译《传统中国日常生活中的协商:中古契约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高朋《人神之契:宋代买地券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
[26]文书底卷照片参见上海图书馆、上海古籍出版社编《上海图书馆藏敦煌吐鲁番文献》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28、129页。关长龙:《敦煌本堪舆文书研究》,中华书局2013年,第477、478页;赵川:《上海图书馆藏敦煌文书017b〈葬事杂抄〉研究》,《南方民族考古》第11辑,2015年。
[27]明·吴国仕辑:《造宗命镜集》,崇祯三年(1630年)吴氏搜玄斋刻本。
[28]甘肃武威地区博物馆:《甘肃武威西郊林场西夏墓清理简报》,《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3期。
[29]曹腾騑等:《广东海康元墓出土的阴线刻砖》,《考古》编辑部编《考古学集刊》第2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71—180页。
[30]文书底卷照片参见上海古籍出版社、法国国家图书馆编《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5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88页。释文参考关长龙《敦煌本堪舆文书研究》第492页。陈于柱先生认为,“鸡、犬在人间生活中具备司时和警备的功能,从而能够以冥器的形式进入墓葬,为亡者‘知天时’和‘知人来’”。但需要进一步思考的是,隋唐宋元墓葬出土金鸡、玉犬,是否能表明丧家在选择葬日时遵循了“鸣吠日”或“鸣吠对日”的相关规则,或者,在葬日选择上遵从了“鸣吠日”或“鸣吠对日”相关规则的墓葬中也是否会(至少大部分)随葬金鸡、玉犬?至少从目前考古发现而言,情况并非如此简单。作为明器的金鸡、玉犬与“鸣吠日”不能简单地混为一谈。就这一问题,笔者拟另撰文讨论。陈于柱:《武威西夏二号墓彩绘木板画中“金鸡”、“玉犬”新考——兼论敦煌写本〈葬书〉》,《敦煌学辑刊》2011年第3期。
[31]明·陈继儒辑:《捷用云笺》,明书林长庚馆刻本。
[32]新疆博物馆考古队:《吐鲁番哈喇和卓古墓群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6期。
[33]白彬先生将墓葬中出土的俑分为三类:仪仗类,包括武士俑、文吏俑、小冠俑、帷帽立(骑)俑、风帽立(骑)俑、笼冠立(骑)俑、铠甲骑俑、骑马乐俑、马、牛、驼等;仆侍类,包括男女仆侍俑、舞乐俑、庖厨俑等;镇墓类,如十二生肖俑、镇墓兽、铁猪、铁牛、“金鸡”、“玉犬”等。笔者认同这种分类方法。就目前考古发现而言,社会中下层官吏和平民墓中随葬俑类往往组合简单、数量较少,仪仗类基本不见,仆侍类和镇墓类亦发现较少。白彬:《隋唐五代宋元墓葬出土神怪俑与道教》,《中国道教考古》第6册,线装书局2006年,第1611页。
[34][47]张勋燎:《墓葬出土道教代人的“木人”和“石真”》,《中国道教考古》第5册,线装书局2006年,第1446页。
[35]黄秀颜:《地券与柏人:宋元江西民俗刍探》,《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新第6期,(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97—128页。
[36]照片、释文并见中国文物研究所等《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一册,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421页。
[38]禚振西:《陕西户县的两座汉墓》,《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禚振西:《曹氏朱书罐考释》,《考古与文物》1982年第2期;张勋燎:《东汉墓葬出土解注器和天师道的起源》,《中国道教考古》第1册,线装书局2006年,第259页。
[39]陈直:《汉张叔敬朱书陶瓶与张角黄巾教的关系》,陈直:《文史考古论丛》,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第390—392页;张勋燎:《东汉墓葬出土解注器和天师道的起源》,《中国道教考古》第1册,线装书局2006年,第294、295页。
[41]黄盛璋:《江陵凤凰山汉墓简牍及其在历史地理研究上的价值》,《文物》1974年第6期;裘锡圭:《湖北江陵凤凰山十号汉墓出土简牍考释》,《文物》1974年第7期。
[42]杨定爱:《江陵县毛家园1号西汉墓》,《中国考古学年鉴(1987)》,文物出版社1988年,第204页;李京华、俞伟超等:《关于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座谈纪要》,《文物》1975年第9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江陵凤凰山一六八号汉墓》,《考古学报》1993年第4期。
[43]林富士:《汉代的巫者》,(台北)稻香出版社1999年,第84页。
[44]黄盛璋:《邗江胡场汉墓所谓“文告牍”与告地策谜再揭》,《文博》1996年第5期;鲁西奇:《汉代买地券的实质、渊源与意义》,《中国史研究》2006年第1期。
[45]黄盛璋:《江陵高台汉墓新出“告地策”、遣策与相关制度发复》,《江汉考古》1994年第2期;荆州博物馆:《荆州高台秦汉墓——宜黄公路荆州段田野考古报告之一》,科学出版社2000年,第224页。
[46]杨开勇:《谢家桥1号汉墓》,荆州博物馆:《荆州重要考古发现》,文物出版社2009年,第191页。
[48]唐·牛僧孺撰、程毅中点校:《玄怪录》,中华书局2006年,第40页。
[49]唐·牛僧孺撰、程毅中点校:《玄怪录》,“前言”,第7、22页。
(责任编辑:刘兴林;校对:黄 苑)
Wood Figures Unearthed from the Tomb Dating Back to the Wu of the Five Dynasties Located at Hubei Theatre
ZHAO Chuan
(Archaeology Department of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Sichuan 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0064)
A property deed and three wood figures were unearthed from a tomb at Hubei Theatre,which dates to the Wu regime of the Five Dynasties.One of the three figures was covered with ink characters in front and back as well as its right side.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se characters and the comparison with other related burials suggest that the characters-bearing figure functioned as abairen,which was to bear the suffer⁃ings and punishment for the living ones.The other two figures represent servants to the tomb occupant.Bai⁃ren is a Taoist practice,which differs by nature from gaodice(registration to the other world),a practice pre⁃vailed in the Western Han time.The tomb is of simple form and small scale with the occupant being identi⁃fied as with relatively low social status,which is to a certain degree representative of the deceased who were buried with bairen-s in their tombs in the late Tang,Five Dynasties,and Northern Song times.
Hubei;Five Dynasties tombs;bairen;servants;Taoism
K871.43
A
2016-01-11
赵 川(1990—),男,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学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道教考古、汉唐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