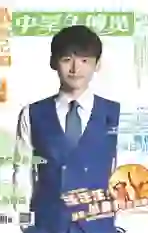苦难的生活里,总有细碎希望和快乐闯入,所以才活着啊
2017-12-01围子
初中的时候,从学校回家要过一条铁路。
铁路下面住着一对疯母女。
每天放学,我最恐惧的事情,就是路过她家门口。
疯妈妈会扑上来打人,疯小孩儿会咬人的胳膊和大腿。
一个女同学有一次被疯母女抓住,她说她们没打她,只是抱住又松开,母女两人哈哈大笑跑向另一个人。
虽然我从来没被抓到过,可是那条必经之路成了我当时重复的噩梦。
每次路过铁路道口这一侧的时候,我都和伙伴警觉地左看右看,直到确定了不会被她抓到的路线,才像离弦的箭一样,蹿出去,惊叫着,马尾辫甩得眼睛生疼。
后来因为太多家长抗议,疯小孩儿的奶奶就把她们关在院子里,每天放学都能见她们抓着漆黑的大铁门的栏杆,伸着头往外看。
有时候疯妈妈和疯小孩儿一人举着半块馒头,互相追逐,尖叫着笑的声音,传出几条街。
初二那年的冬天,听人提起,高速路口旁边的地里,有一个人冻死了。因为酒醉,就在雪地里睡下,第二天下午被发现的时候,硬得像一整块冰。
那个冻死的人是疯小孩儿的爸爸。
他是个赌鬼加酒鬼,赌输了就喝,喝醉了继续赌。
再后来听说疯小孩儿家里的事是弟弟读初中的时候,有一天妈妈问我:“你知道这次你弟弟他们学年第一的女孩儿是谁吗?是张新!”
这是我第一次把疯小孩儿和她的名字联系起来。
在我初中的记忆里,疯小孩儿就是个代号,没有年龄、没有上学这样的社会规则。竟然忽略,她是和我弟弟一样年龄的一个小女孩儿。她会长大、会读书、会遇见青春的烦恼和喜怒哀乐。
我惊异地发现自己对这个女孩儿莫名的好奇和好感,就在一个下午经过她家的时候,和她打招呼,然后我们成了朋友。
至此,我才把她后来的生活连起来。
她的整个初中,上上停停,奶奶每一次生病,叔叔婶婶都会让她留在家里照顾。中考前,奶奶去世,她以为自己读不了高中了,没想到还是拿了一个漂亮的成绩,进了重点高中的重点班。
高二的時候,情窦初开,她和学校国旗班的一个男孩儿互生好感,两个人关系发展迅速。一天男孩儿的爸妈一脚踹开她班级的门,指着她的鼻子骂她:“接受资助上学还不好好学习,狼心狗肺。”
那些站在道德制高点的辱骂,轰得她额头乱响。她在和我讲起这件事的时候,身子抖成一团,我把她搂过来,那是我摸过的最冷的一双手,一瞬间,我都觉得自己掉进了一个封闭的冰块里。
叔叔把她从学校接回来,所有人都说她是因为谈恋爱被开除。她把自己关在奶奶去世的那个小平房里,那里好久没人打理,风一吹窗子呜呜作响。她说夜半常常能听见妈妈在窗外喊她,可是跑出去,月亮有时候是上弦月,有时候是满月。
就在那个时候,我把《活着》这本书送给她。
不知道怎么安慰她,就幼稚地想用书劝说:“世界上,好多人都在经历各种各样的悲苦挫折。”
说实在话,我当时心里满满当当都是“生活怎么可以这么折磨一个人”的愤慨,和怕她活不下去的恐惧。
我没办法身受那种没完没了的晴天霹雳,只是在她身边看着都觉得不公平。
我抑制不住那种同情,可是我知道,她需要的不是同情。
我不知道她需要什么,也不知道我能为她做什么。
直到最近我再把《活着》这本书翻出来的时候,仔细看余华的序,才恍然,我们在别人的生活里提炼出的几个词:苦难、悲怆、不公、坎坷,都不足以形容他们的一生。
而生活的丰富,在于每一天都由无数细碎的小事件组成。
比如福贵让“妓院的女人背着他跑到丈人家门前打招呼”时的嚣张和戏谑;比如在倾家荡产时想起“家珍也曾是一个清纯迷人的女学生,也曾是大家闺秀”时的悔悟;比如“长根乞讨的时候捡来一根红头绳,揣在胸口几天拿回来给凤霞戴上”时的情义;比如 “二喜拼命疼凤霞”时的放心;比如福贵看见那只“待宰的老得快要走不动的牛的那一滴泪”时,用攒了一辈子的钱买下它……
余华说“福贵”是那种能够看到自己过去的模样的人,他能准确描述自己年轻时候走路的姿态,甚至可以看见自己是如何衰老的。
我更愿意理解为,他从来没有刻意记得,而那些事的发生就在昨天。
无论悲怆,还是快乐,所有的一切都发生在昨天。
因为仅仅是发生在昨天,所以细碎的快乐可以抵御晴天霹雳的痛苦,它们中和、混淆,又让人觉得明天没有那么无望。
张新也是一样。
她是疯小孩儿,是妈妈眼里最好的玩伴,是奶奶的依靠和骄傲,是老师眼里的第一名,是同学眼里不敢忽视的存在,是国旗班那个男孩儿第一次心动的女孩儿。
她的生活从来不是外人的一句理解、懂得,以及同情可以概括的。
那些微小的快乐和骄傲、满足,就像手心的掌纹,像皮肤上密密麻麻的横竖交错的菱形格,虽然比不上生活里那些天翻地覆的大事件般惊天地泣鬼神,可是它们才构成了一个人最基本的相貌和纹理。
喜忧参半,好坏堆积,才构成了一个人完整的一生。
所以,你知道吗?最难的不是活着,是承认那些痛苦背后并存的快乐,并且心安理得地接受它。
编辑/围子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