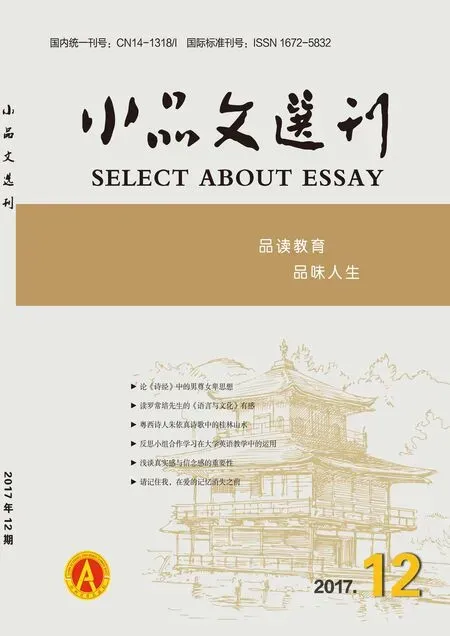《埃里汪奇游记》的反讽特色探析
2017-12-01何莹莹
何莹莹
(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 杭州 310018)
《埃里汪奇游记》的反讽特色探析
何莹莹
(浙江工商大学 浙江 杭州 310018)
18世纪英国小说家乔纳森·斯威夫特(Jonathan Swift,1667—1745年)是举世公认的讽刺大师,被高尔基誉为“世界伟大文学创造者”,其代表作《格列佛游记》更是以生动有力的讽刺风格受到世界范围内读者的热烈追捧。一个世纪以后,另一位英国小说家塞缪尔·巴特勒(Samuel Butler,1835—1902年)笔下诞生了另一部讽刺意味强烈的经典作品《埃里汪奇游记》①(Erewhon)。只不过,这部小说和它的作者一样,一开始并未得到文坛足够的关注。后来戏剧大师萧伯纳读了长篇小说《众生之路》,不禁发出惊叹,称赞他是“十九世纪后半期英国最伟大的作家”。20世纪英国作家E.M.福斯特也充分肯定其才华,尤其对他在小说中运用的拐弯抹角的讽刺叙事手法赞誉有加。1835年,巴特勒出生于英国诺丁汉一个再传统不过的基督教家庭。虽然从小就耳濡目染基督教宣传的仁爱、和平信念,但却从未真正承认基督教给世人带来过任何实质性的作用。于剑桥毕业后还得遵照家族传统去伦敦一个教区做牧师,算是继承父亲和祖父的衣钵。巴特勒的家庭背景虽谈不上如英国贵族那般富贵荣华,但也称得上有头有脸。毕竟基督徒的光环始终笼罩着,他的父辈们又都世代接掌圣职。尽管有着本可以安然度过一生的资本,巴特勒最终还是选择了与“众生之路”背道而驰的另一条人生道路——只身远赴新西兰。他身处的维多利亚时代(1837—1901年)是英国最为强盛的时期,但巴特勒在他生平仅有的那些作品里却并不热衷于向读者展示“日不落”帝国的繁华盛景。
倘若《众生之路》是一部令巴特勒“赔了夫人又折兵”的小说,那么《埃里汪》至少让作家本人有过少得可怜的出版收入。整部小说其实是男主人公冒险旅程中的回忆录。19世纪60年代,一个道地的英格兰男人怀揣着发财致富之梦、远离家乡寻找畜牧宝地,结果意外踏入一个名叫“埃里汪”的国度,并在这个有着许多怪异法律制度的国家经历了不少奇遇。《埃里汪》绝非一部简单的游记或是乏味的回忆录!巴特勒为读者虚构了一个遥远的国度埃里汪,看似十全十美的虚构社会内部实则隐藏着诸多弊端,为的是含沙射影地讽刺现实中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英国社会。整部小说描绘一个虚构之国的所见所闻,其法律制度、人情世故一应俱全,书名及地名“Erewhon”正是“nowhere”(乌有乡)颠倒拼写所得。这个国家早已不是托马斯·莫尔(St.Thomas More,1478—1535年)笔下的理想国度,而是社会现实的化身。讽刺手法的运用,使这部小说的讽刺意味极其浓厚,成功塑造出了讽刺的乌托邦图景。而巴特勒对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现实的反讽则是通过社会的方方面面体现出来的:
1 荒唐学院的荒唐
小说叙述者初次见到荒唐学院的真容,是在一位名叫西姆斯的音乐银行出纳的邀请下。所有埃里汪国民几乎都仰望着他们的荒唐学院,而但凡有点社会地位和知识储备的人都以熟练运用荒唐学院教授的“假设语言”而感到自豪。“假设语言”来自于荒唐学院的门面学科“假设学”,简而言之就是关于可能性的学科及语言表达。学院里赫赫有名的教授始终持有一种观点,认为仅仅教给孩子他所熟悉的只能使他获得关于宇宙的狭隘而浅薄的概念。因此,“当务之急也许是教给他现在在宇宙中还找不到的所有事物。让他看到这些可能性,从而为应付各种意想不到的事作好准备。”②这也是之所以设立假设学体系的原因。不得不说,这些教授们确实是名副其实的“知识分子”,只有对假设学语言有着超越常人的掌握才能作出如此理所当然的诡辩。在青少年们的黄金时代,他们被父母强制送去荒唐学院学习实际上毫无用处的假设语言。孩子们没有选择的权利,就像出生时选择父母、选择家庭那样无能为力。
熟练掌握并运用假设语言侃侃而谈的埃里汪人会成为公认的绅士,就像在巴特勒的国家英国,那些满腹古典作品、时刻把理性挂在嘴边且只为理性所引导的人将会是当之无愧的绅士一样。一切那么理所当然,又那么可笑至极。孩子在本该实实在在去干事的年纪被剥夺了自由的权利,束缚在校园里做着无用功。巴特勒所提倡的是充分发挥学生自身价值的世俗教育,而不是坐在高等学府的课堂里整日听教授讲着对古典作品的研究,平庸度日。对这一点,巴特勒本人是有直接发言权的,因为最初的他也是英国保守教育体制下的牺牲品。在剑桥的学习期间,巴特勒内心才逐渐意识到英国乃至整个欧洲当时教育的闭塞,最终刺激他抛弃家族理想转而奔赴新西兰生活。
在现实英国,也上演着同样的教育体制闹剧。而牛津、剑桥这样的历史名校恰恰是教育问题最严重的场所,里面充斥着像埃里汪荒唐学院教授一样的伪科学学者们。他们的知识始终停留在过去,长期脱离现实生活,由此变得古板偏激,和荒唐学院的教授如出一辙:“我很难真正明白当我与西姆斯待在一块时所见到的人(正话反说,其实很能理解),因为如果他们哪怕只是有点怀疑照他们所说的‘露出了马脚’,就什么也别想从他们那里得到。”③倘若让他们明确表达对某一观点的直接看法,那简直难于登天,他们会一直周旋,所有的话语都保留自己全身而退的余地,以免影响到自己的声誉。
没有荒唐,理性不复存在;没有理性,荒唐缺少意义。巴特勒带有讽刺意味地把理性这一原本指导欧洲文明进步的理念和荒唐放在一起,其讽刺意味得到了进一步加深。作者借叙述者之口强调埃里汪的荒谬与自己没有半点瓜葛,殊不知正是内心波涛汹涌表面还要波澜不惊的直观表现。在那份事不关己的泰然背后其实是他无尽的忧世情怀,一切都在巴特勒的反语中体现出来。他强调埃里汪的荒谬与他无关,其实他当然清楚埃里汪的背面就是他所处的英国社会,又怎会无关?另外,“深深植根于英国人秉性之中的有助于使自己幸福的观点”、“所受的教育完全不同”、“欧洲孩子与父母的关系更和谐”等等此类都是作者在正话反说。巴特勒运用反语来增加小说的趣味性,也在轻松诙谐的氛围中幽默地嘲讽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社会的现实教育状况。
2 《机器之书》的秘密
维多利亚时期的英国先后经历两次工业革命,资本主义经济的壮大更是把大英帝国推向了发展的巅峰,光明的前途使整个英国都沉浸在无与伦比的成就感中。与此同时,人们成为了疯狂揽财、一心圈钱的工具,一颗颗被铜臭味和机油味腐蚀的心灵将英国社会推入了新的危机。巴特勒先人一步,意识到工业进步和经济飞速发展后将带来的严重隐患,这也是他在《埃里汪》创造一部《机器之书》的目的。他试图唤醒沉浸在科学无限发达、技术无限进步思想中的民众,警告他们不要成为机械的奴隶。
在叙述者初到埃里汪时,他便被当地人逮捕了,稍后立即从村庄转移到当地的一个市镇。他被带到了地方法官那儿,又是摸脉又是检查肌肉,体格和健康状况无疑令当地人相当满意。而在检查包袱时,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们不久就注意到了我的手表……我打开后,看他们的表情极不愉快,弄得我莫名其妙,我不知道里面有什么触怒了他们。”④“我”清楚地看到了法官脸上对手表表现出的憎恶之情。让“我”知晓埃里汪禁止机器来龙去脉的那本重要的书《机器之书》,便是这位古董商的馈赠。早在此前五百年,埃里汪就发生了由机械师和反机械师发动的关于机器的内战,其直接的触发原因正是叙述者费尽心力为读者翻译的那部《机器之书》。“无法保证——用他自己的话说——机械的意识最终不会发展,因为现在机器只有很少的意识。软体动物也没有什么意识。仔细想想,在最近的几百年中,机器取得了多么异常的进步!植物王国的进步又多慢!”⑤《机器之书》的作者意在广而告之的论点是:机器会产生意识,从而超越现在的人类,主宰包括人在内的全世界。
英国维多利亚时期最值得载入史册的成就毫无疑问是举世闻名的工业革命,经历工业革命洗礼的大英帝国进入了经济发展的全盛时期,而鼎盛的背后却是危机四起。“一极是不停的财富积累;另一极是穷困的增多和加重。通过十九世纪的工业化运动,这种逻辑以越来越大的力量迫使正在扩大的社会各部门接受。”⑥财富的强大力量暂时性地压下了社会底层的怒气,整个大英帝国像是安上了制造财富的马达,日夜不停地开始逐利。没有哪个英国工厂主能够抵制金钱主动靠近,因此也就没有谁能够拒绝机器带来的巨大便利。
只有在巴特勒创造的埃里汪国度,凭着对机器进一步发展成魔的惧怕,真正消灭了整个国家的机器。这种文学中的想象也是巴特勒对达尔文进化论的一种戏谑。“如果巴特勒论点的最终来源是达尔文的进化理论,那么埃里汪奇对机器的禁止就恰恰是将进化论转为反面的尝试了。”⑦在奇境埃里汪,他可以选择让激进的反机械主义者发动战争、彻底消灭国家一切机器的流通。他在小说中拥有这种超能的特权去阻止危机的逼近,而回到现实中的他却无能为力,仅靠语言已无法将英国人从对机器的盲目崇拜中拯救出来。一处是对工厂和机械无限制的推崇,一处则是由于害怕机械吞噬人本身而销毁所有机器。一实一虚,一真一幻的对比下,正是巴特勒想要表现的人与机器的博弈。巴特勒采用了机器和人自身的鲜明对比,他仿照斯威夫特在《格列佛游记中》对比小人国、大人国的方法,把机器和人的进化放在一处讨论,强调机器和人的位置在目前看似是一仆一主,但并不意味着这种关系将永恒不变,人类将永远是机器的掌控者。他通过含沙射影的方式,向人类社会发出警告:埃里汪的机器影射的就是人类世界的科技,科技的高速发展和人类对科技无止境的过度依赖会带来可怕的影响,沦为科技世界中的奴隶是人类谁也不希望看到的一幕。
3 结语
莫尔笔下幸福洋溢的“乌托邦”国度把千百年来人们对理想境界的想象第一次具体化、细节化了。看看书中的精神天堂,再回头看看自己身处的英国乃至整个欧洲,社会的各类矛盾不断被激化。经济的爆炸式增长并未带给所有人共同的富裕生活,反而使处于劳动阶层的民众受尽压迫和剥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因争夺财富而战事不断,造成的最直接影响就是民不聊生。正是现实矛盾的催生出巴特勒的忧世情怀,也催生出重在讽刺的《埃里汪奇游记》。毫无疑问,巴特勒和斯威夫特等讽刺小说家一样,对现实都有着通透的认识。也正因为对现实的深刻认识,他们才能在文学的想象世界中以一种幽默诙谐的方式针砭时弊。在小说中,巴特勒交替运用反语、对比、夸张等多重讽刺手法,通过小说中“荒唐学院”和《机器之书》等内容的介绍,嘲讽维多利亚时期英国社会教育问题和机器泛滥的现象。于他而言,讽刺是一面能帮助他和像他一样的维多利亚时代一员认识自我、看清现实的镜子。通过埃里汪与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对比,借以表达自己对现实的控诉,警醒人们对地狱般未来时刻保持清醒的危机感。
注释:
① 又名《埃瑞璜》或《乌有乡》
② [英]塞·巴特勒.埃里汪奇游记[M].彭世勇 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145
③ [英]塞·巴特勒.埃里汪奇游记[M].彭世勇 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154
④ [英]塞·巴特勒.埃里汪奇游记[M].彭世勇 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43
⑤ [英]塞·巴特勒.埃里汪奇游记[M].彭世勇 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158
⑥ [法]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M].吴艾美 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90
⑦ 王闯.达尔文的进化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D].河南大学,2010:8
[1] [英]塞·巴特勒.埃里汪奇游记[M].彭世勇 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2] 李志斌.欧洲文学的乌托邦情节[J].外国文学研究,2009.
[3] [英]卡莱尔.文明的忧思[M].宁小银 译.中国档案出版社,1999.
[4] [法]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M].吴艾美 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86.
[5] 王闯.达尔文的进化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D].河南大学,2010.
[6] 托马斯·莫尔.乌托邦[M].戴镏龄 译.商务印书馆,1996.
[7] 武跃速.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个人乌托邦倾向[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
何莹莹(1992.9-),女,浙江杭州人,在读研究生,浙江工商大学,研究方向:外国作家作品研究。
I054
A
1672-5832(2017)12-003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