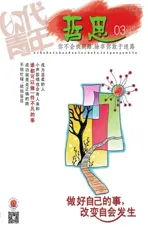有你相伴,寒夜渐暖
2017-12-01方脸张
◎方脸张
有你相伴,寒夜渐暖
◎方脸张
我终于还是没能见到她最后一面。收到姥姥的病危通知时,我正在为一份能留在新加坡的Offer忙得焦头烂额。我有信心拿到它。只是接到了电话后,我直接改道去了机场。这是我来新加坡的第四年。
我妈把我打包送到姥姥家时,姥姥的麻将搓得正起劲。牌友们见状准备收桌,她点了一支烟,说,没事,继续。那年我5岁,第一次见到她。如果不是爸妈离婚,两个人都不愿意管我,我是不会知道自己还有个姥姥的。
那天我像个无人问津的小丑在门外站了很久,一直到她的牌局作罢,她才看了我一眼。后来我听到她和妈妈在屋里谈话,妈妈最后说了一句“上梁不正,你也别嫌下梁歪”便挎上她的小皮包摔门走了,一走就是好些年。
据说姥姥在她那个年代是特立独行的楷模。17岁的时候爱上了来村子里唱戏的戏子,便瞒着太太跟着戏子跑了。两年后,她两手空空,戏子不知去向,唯一带回来的就是一个大肚子。
没有人知道姥姥那两年去了哪里,又遭遇了些什么,而戏子就像从未出现过的一场梦,消失得干干净净。这个一直以来无比安静的村子从姥姥回来的那一刻便醒了,霎时间四起的谣言支撑起一张巨大的网把姥姥围在了中间。得亏姥姥性子足够泼辣、坚强,以死相逼留下了我妈。然后她又在村子里开了一家小卖部,独自把我妈拉扯大。那时我总在想,如果姥姥没生下我妈多好,那样就不会有我了。
哭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徒劳且多余的动作。很多朋友都问我,你怎么都不会哭啊?感动了不哭,受委屈了不哭,疼也不哭,我只笑不说话。其实我也哭过的,爸妈离婚的时候哭,在被丢到姥姥家的前几天哭,在被别人喊“没人要的小孩”时歇斯底里地哭。可是没有一个人因为我哭而给我一颗糖。我永远都记得,姥姥边搓着麻将边说“除了哭什么都不会”时鄙夷的神色。说来也怪,那样的鄙夷,成了我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想要活得更好的理由。
那场雨来得那么大,那么突然,令人猝不及防。我至今都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会选择去等,不是等雨停,而是在等雨伞。一直等到整个学校只剩下我一个人,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可她始终没来。我走在瓢泼大雨中,仿佛全世界的雨此刻都淋在我的身上,真冷啊。我回到家时,姥姥正坐在麻将桌边谈笑风生,她抬起头冷冷地看着我说,像个傻子,下雨的时候都不知道用力跑。
我像母亲当初一样狠狠地摔了房门,只不过我是把自己锁在了房里。我恨她,所以后半夜她进屋抱着我时,我狠狠地推开了她。我不要她施舍的那些温暖,我拒绝她成为我生命的羁绊。
只是若干年后,当我独自走在异国他乡的冷雨中,竟也不觉得有多难过,原来我早就学会了在雨中奔跑。
刚上学的时候,他们在背后叫我没爸没妈的野孩子。渐渐长大了,他们又开始叫我小贱人。不计较,不哭闹,关上耳朵不去听大抵是我最擅长的事。可还是会有挑事者找上门来,他们把我围在中间,话也越说越难听。我从不曾想过她会以那样的方式来到我身边,六十多岁的她依旧泼辣,呼啦啦地冲进人群,把我护在身后。她点了一支烟,吸了一口,说,你们这群小杂碎,要是再敢欺负我孙女,老太太我揍得你们屁股开花。
那天回家后,她坐在沙发上,烟一直没停过,却也再没说其他话。我迷迷糊糊睡着后做了个梦,梦到她拉着我的手说,快点长大吧,长大就好了。自那以后,可能是出于对我姥姥的忌惮,再没有人敢对我动手动脚。可谣言似风,从不曾停过。那些风吹过我的肌肤留下肉眼难寻的细小的伤口,在受伤结痂这样的往复中,为我穿上了一身无坚不摧的铠甲,算是岁月赠予我的唯一礼物。
在姥姥家的第七年,我再一次见到了我的妈妈。她依旧年轻漂亮,穿着时髦的衣服,开着小车。我看到她的时候,她正有些谄媚地讨好着姥姥,见到我便立刻热情过度地唤我的名字,声音好听又刺耳。我知道自己要走了,终于可以离开姥姥了,可我却始终觉得心里空落落的,还带着点心慌。姥姥在马路边送我们,车子开动时,她递给我一筐鸡蛋,说是院里的母鸡生的。以往她每天都给我煮两个鸡蛋,我不知道她原来已经存好了这么一筐。
我随着妈妈到了省城,那里除了有妈妈,还有她的新家庭。我成了一个入侵者,每天过得小心谨慎。辗转难眠的夜里,我会想起姥姥,想起她板着冷若冰霜的脸为我做红烧排骨,想起每个夜晚她搓麻将的声音,想起她带着烟草味的怀抱。可我从没想过她会来。姥姥说她来看看她的新外孙,来城里享享女儿的福,来的理由有千万种,却唯独没有我。她从不承认自己会想念我,就像我也习惯把这种想念放在深夜一样。
高中毕业后,我几乎怀着重生的心情选择去新加坡读书。走的那一天,姥姥从老家赶来送我,她硬塞给我一个小手帕。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姥姥局促的样子,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手帕里包着一千块钱。姥姥没什么钱,打牌赌注都是很小的,那个把妈妈养大的小卖部也早已落寞。淋雨的时候我没哭,受委屈的时候我没哭,当我站在机场看着妈妈扶着颤颤巍巍的姥姥离开时,眼泪落了下来。
爱这种东西从来都比不爱更能伤人,而那用手帕包住的一千块钱温暖了我以后的大半个岁月。
医护人员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正为了Offer忙得焦头烂额,是一个国内的陌生号码。
“喂,你好,请问你是哪位?”这个世界上怎么会有那么奇怪的人打电话问别人是谁?我刚准备挂断,电话那边又传来一个声音“我们这里是医院”。
我挂电话的手堪堪顿住,那边又继续说道:“患者的手机上只有这一个电话号码,不过患者生前似乎打过很多次都没有打通,我觉得不像国内的号,便加了区号试试,请问您认识她吗?”
“患者”“生前”等词汇在我眼前绕啊绕,生理先于我的心理做出了反应,眼泪倾盆而下。
“小姐,患者由于突发心脏病抢救无效死亡,请问你可以联系国内的其他亲属吗?”电话那边继续问道。
我挂断电话,推掉Offer,订机票,去机场。40分钟后,我站在了机场的大厅里。新加坡—中国,一个我逃离时看来那么近的距离,竟然生生地走出了阴阳相隔。
“患者生前好像打了很多次”,姥姥究竟是怀着怎样的心情一遍一遍地拨打我的电话呢?相隔这么远的距离,也许她只是想再听听我的声音吧。我来新加坡4年,没想到第一次回去竟然是为了给她服丧。飞机落地的那一刻,我像是回到了4年前。姥姥来送我的时候说,累了就回来,姥姥做你喜欢吃的糖醋排骨等着你。
回去后我才发现,姥姥家的冰箱里放着不止一份糖醋排骨,一直在等着我回家。姥姥她真倔强,她总是不说好听的话。在她身边的那几年,她把温暖藏在手心里,推搡着我勇敢前行。我蹲在她的灵前吃着不知道变没变味的排骨时,才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她最爱我,以至于要教会我没有伞的孩子更要学会奔跑。
“天黑的时候我又想起那首歌/突然期待下起安静的雨/原来外婆的道理早就唱给我听/下起雨也要勇敢前进……”一直以来都觉得老歌好听,越老越有韵味。近年来总是爱回忆一些以前的事,大多是细碎的,连不成章节。某天突然又听到孙燕姿的这首《天黑黑》,一些模糊的人和事开始具象。我看见了那一年奔跑在雨中的自己,眼睛里没有泪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