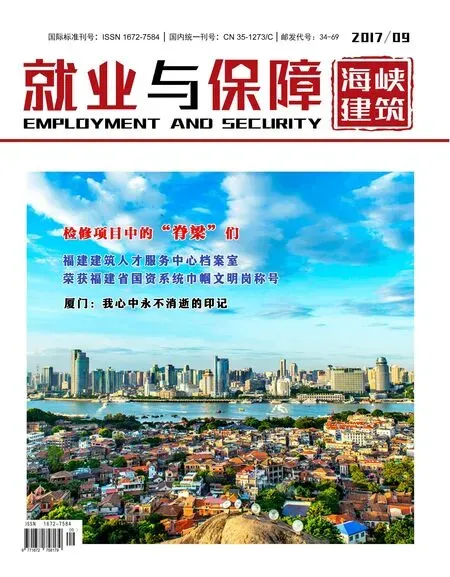厦门:我心中永不消逝的印记
2017-12-01王柏霜
王柏霜
厦门:我心中永不消逝的印记
王柏霜

厦门鼓浪屿(王福平 摄)
对于一座城市念念不忘,一定可以说出无数理由。
说得很煽情:“这座城市是我的初恋。”
说得很文艺:“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让我一辈子都刻骨铭心,难以忘怀。”
有另一种说法则很戳心:“一座城市令你念念不忘,大抵是因为,那里有你深爱的人和一去不复返的青春。”
厦门于我,就很戳心。
(一)
厦门大学,我的诗歌起步之地。
我像一个风华正茂的大学生那样,做着平常不过的文学梦。
芙蓉湖那时还是一口杂草丛生的池塘,我们坐在池边对月吟诗,旁若无人。
梯形教室,我们的青春诗会正在热烈举行。
印刷厂,我们编辑的《采贝》诗刊泛着油墨香正准备出厂。
我无数次梦回如今的白城环岛路至演武桥头原来的那座海宾茶室,想起一泡清茶、一包鱼皮花生与诗友欢聚的诗意人生,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那个将我的诗抄在精美笔记本上的学姐,你在哪里?我暗恋的女生,你现在好吗?我大学毕业离开厦门时那四位联合送我影集的美女们早就各奔东西——我真的很想念你们。
而我已经第几次站在我曾经住过四年的芙蓉四门口那棵凤凰木之下留影?
我已经记不清了。
(二)
鼓浪屿。1985年12月25日圣诞节。
四男一女五个采贝诗社社员晚饭后一起到鼓浪屿三一教堂听唱诗班唱颂歌。圣诞活动结束之后已近午夜,不知是谁提议,夜宿鼓浪屿,明早看日出,获一致赞成,似乎还带着一股临时冲动后的激情。
大家到小卖部买了一些饼干、花生、饮料提在手上,没多久就攀到“天风海涛”附近,意外发现当晚日光岩附近风很大,气温很低。大家打消上日光岩的念头,找到一处避风处,坐下来,边吃零嘴,边天南海北地聊天,时间倒也过得很快。
随着夜越来越深,鼓浪屿上的气温也越来越低。同行中只有一位社员带着一件厚军大衣,让给唯一一位名女社员,其他男社员轮流讲笑话,冷了就起来跳脚转圈……那个夜晚的鼓浪屿,因为这几个傻瓜而变得不得安宁。
好不容易熬到第二天天亮,气温回升,风也变小,一脸倦容的社员们抱着最后的一丝激情登上日光岩,期望欣赏到一轮红日从东边的海上升起。可大家放眼望去,目之所及一片白茫——是个大阴天。大家失望至极,灰溜溜再回到学校。
当天,四个男社员因为吹多了风受了寒,嗓子哑得说不出话来。
2011年6月11日,我站在鼓浪屿安海路8号杨桃院子里,诵读自己写的那首《躺在时间的河流上》,我感叹着时间真的像河水一样流逝得那么快速。
(三)
对于诗歌初学者来说,能发表作品是一件梦寐以求的奢望。
或许是我的诗歌生涯之幸,遇到了当时《厦门文学》的诗歌编辑陈元麟,在他的手上,正式发表了我平生第一首诗歌。虽然是一首短诗,但给我的创作带来莫大的鼓舞。
后来还有一首长一些的诗歌《梨园戏》发表在《厦门文学》1988年1月号,并被收入《百年厦门新诗选》。
1985年,我的另一首诗《着色的信笺》被收入《南方——抒情诗·朦胧诗选》,这本定价0.96元的诗集由福建文学讲习所主编,作为“南国文学丛书”由厦门鹭江出版社出版。诗集收录了当时名声如日中天的舒婷、北岛、顾城、欧阳江河等著名朦胧诗人的作品。
该书的“内容提要”是这样写的:“这是一本富有南国意味的现代抒情诗集。老一辈诗人及崛起的诗群的诗人们,运用寓有深意的象征手法及多层次的空间结构,表达了对祖国山河的爱恋与对社会、人生不倦的思索。作品风格各异,意境幽远,发有深思。”
重新阅读这样的文字,让我有时光回流的穿越之感。
(四)
菲律宾《世界日报》2007年8月30日这天,刊载了一篇题为《采贝三友》的文章。在“编者记”里写道:“1984~1986年间,编者在厦门监建目前已嫌老旧的‘西堤别墅小区’建筑群,工余常找鹭岛文艺界人士聊天;经陈元麟先生介绍,认识厦大中文系文艺组织‘采贝诗社’诸社友,并经常联系。”
这里的编者,是菲律宾著名诗人、摄影家云鹤先生;“采贝三友”之一,就是本人。
我与云鹤先生的交往是非常纯粹的忘年之交,堪称我诗歌生涯的奇迹,是诗歌成就了一段跨越时光与地域的诗人之谊。
2014年,我在一篇怀念云鹤先生的文章中写道:“1986年始,云鹤先生开始在菲律宾《世界日报》文艺副刊发表‘采贝诗社’成员的诗歌作品,并一直同‘采贝诗社’部分成员保持密切的联系,尽他所能选登诗社成员的诗作,这对一个初学者来说是莫大的鼓励,对当时多少带有一定发表冲动和欲望的诗歌与作者来说,云鹤先生利用他的文艺副刊为‘采贝’人提供了一个难能可贵的阵地和平台。”
厦门大学“采贝诗社”在云鹤先生的扶持下,声名远播东南亚等华文盛行的海外地区。2005年,我自己编印的那本《不雨之秋》诗集,共选入69首诗歌,大部分都在《世界日报》文艺副刊发表过。
斯人如鹤去,殊在意料外。想到云鹤先生突然仙逝,顿觉心痛不已。如今,云鹤先生的太太秋笛女士继承他的遗志,仍时不时地从博客中选取“采贝三友”的诗作,发表在菲律宾《世界日报》的文艺副刊。
衷心感谢秋笛女士!
(五)
在厦门,我有一门亲戚。
舅舅张厚进先生是中国有名的水彩画家。他出生于1925年,1943年进入永安师范艺术科就读,1951年考入福建师范大学艺术系,曾任厦门集美大学教授。
我喊张厚进先生为舅舅,是因为母亲是他的堂妹。当然,这门亲戚还是有点勉强,因为母亲是小时候被外公抱养的,与张家并无血缘关系。但舅舅为人忠厚、善良朴实,待我母亲如亲妹妹,特别是知道我考上厦门大学后,多次嘱咐母亲,让我去厦门家里找他。
我遵照母亲的嘱咐,在大二时,找了个周末去探望舅舅。
舅舅家住中山路边上的水仙路。印象中,水仙路两旁都是2~4层的楼房,均为骑楼建筑。据说这条路很有来历,曾经是厦门港口最具人气的地方,店铺鳞次栉比。
第一次到舅舅家印象很深。房子不大,虽然厨房、客厅、卧室一应俱全,但显得特别拥挤。三个表哥当时只有大表哥结了婚,也住家里。舅妈见到我很热情,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而舅舅只是憨厚地坐在一旁微笑。
此后三年在厦门大学读书期间,我时不时利用周末时间去看望舅舅。舅舅平时住在集美,也只有周末才回来。每次见到舅舅,他都亲热地告诉我:“你只要周末没‘代志’(事情),就到家里来。”
每逢端午、中秋等重大节日,舅舅会提前一个月跟我再三交代,让我到时候一定要到他家吃饭。记得大二那年中秋节,我是在舅舅家过的,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过上的一个最像样的中秋节,第一次知道并参与中秋“博饼”。第二年端午节,也是在舅舅家过,第一次吃到添加了“虎蹄”(一种海产品)的春卷。舅舅的照顾,让我在厦门求学期间倍感温暖。
在舅舅家,第一次接触到水彩水粉画这一独特的艺术形式……后来,舅舅送给我一幅是以水仙花为题材的静物水彩画,至今仍挂在我家的墙上。
舅舅作为全国知名的水彩画家,曾应邀到台湾办过画展,出版过画册。
大学毕业后,我成为一名记者。每逢去厦门采访,怀着对舅舅的感激之情,都会抽空给舅舅家里打个电话。舅舅若是在家,我一定会去探望他老人家。有一次,得知退休后的舅舅在中山公园写生,我特地跑去中山公园看望。
舅舅有三个儿子,他们是我的表哥,当时他们好像都在国营的厦门罐头厂当工人。遗憾的是,表哥里没人继承舅舅的艺术衣钵。
舅舅虽于2002年4月逝世,但他一直活在我的心中!
(六)
我有三种厦门。
在从事新闻工作期间,厦门是出新闻的地方,它是我采访的主要地区之一。记得有一年夏天赴厦门采访,在采访鼓浪屿管委会之后,遇到暴雨,被困在鼓浪屿,直到很晚才脱困回到位于厦门科技宾馆的驻地。除了面上的采访,我还采访过住在鼓浪屿的书法家陈秀卿、画家林英仪,等等。那时,我是一个新闻记者。
1996年至今,我从事对外经贸合作工作,厦门是中国对外经贸合作的窗口。我参加过许多年“9.8”投洽会活动,在会展中心、厦门宾馆之间穿梭忙碌。此时,厦门是我开展工作的地方,而我是一个政府工作人员。
我最喜欢的是诗人的厦门。抛开我在厦门大学以及“采贝诗社”期间结识的朋友甚至忘年交不说,这些年来,结识了威格、高盖、子梵梅、颜非等厦门《陆》诗刊的至情至性的诗友,以及如杨桃院子主人吴谨女士等聚在《陆》诗刊周围的真诚朋友,使我有更多机会重新回归诗意的厦门,这是我的幸运。无论在鼓浪屿杨桃院子、复兴古堡还是厦门的其他地方,我感受到的是诗人的厦门,如夏天凤凰花的热烈与美好。
这个时候,我在厦门的身份,也是一个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