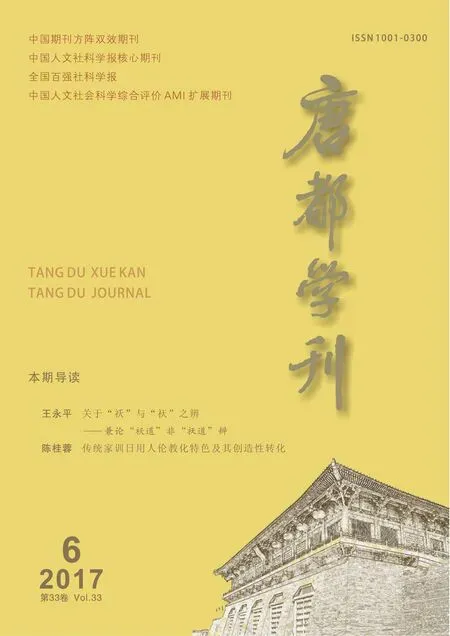明代被逮下诏狱之关陇士人考
2017-11-27高璐
高 璐
(兰州大学 文学院,兰州 730020)
【关学研究】
明代被逮下诏狱之关陇士人考
高 璐
(兰州大学 文学院,兰州 730020)
明代被逮系诏狱的知识分子在数量上非常可观,而关陇士人在这一群体中较为突出。受关中地区古直朴素的民风遗存、关学躬行致用思想的影响,关陇士人往往身兼学者与文官的双重身份,居家砥砺气节、居官敢于谏诤是他们一贯的行为模式。整体而言,明代被逮系诏狱的关陇士人主要有两大特征:一是以学问见长,甚至本身就是关学学派中的重要人物。二是主要集中在明代中期。这种情况与明代中期的经济状况、社会思潮等因素密切相关。对这一批人物的梳理与关注,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明代关学士人群体的政治态度与持身品格。
明代;诏狱;关陇士人
《礼记·曲礼上》曰:“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1]然而明代以其政治体制的特殊性,在建立之初就不吝以严刑峻法对臣属加以钳制。这种钳制的外化手段则体现为明代特有的厂卫制度,通过侦讯的方式监视臣僚,刺探舆论。锦衣卫北镇抚司下设的诏狱,则在审讯、用刑、羁押方面担负着重要的职能作用。自洪武朝以来,诏狱的运转几乎与整个明王朝的历程相始终,而有明一代被逮系诏狱的知识分子在数量上也非常可观。其中,关陇士人在这一群体当中较为醒目。他们往往兼具学者与文官的两重身份:作为文官,他们身上带有浓厚的关学学养,甚至本人就是明代关学学派中的重要人物。作为学者,在关学通经致用思想的影响下,他们在朝堂上往往敢于谏诤,以气节相尚。由于这一群体形象鲜明,难以忽视,因此有必要予以细致梳理和关注,进而整理谱录。在考察其生平行实、思想动向的同时,亦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明代关学士人的政治态度与持身品格。
一、诏狱释义
中国古代的诏狱自设立以来,即由皇帝直接掌管以羁押、惩戒臣属。“诏”作为有特定含义的字眼为皇帝所专用,意为该监狱当中的罪犯均由皇帝亲自下诏书定罪,“具有表明皇权尊严的神圣性和象征性的意义。”[2]可以说,诏狱制度的存在并非建立在当时实际律条的基础上,它的运转完全依靠权力掌握者与行使者的意愿,具有浓厚的人治属性,并且干扰了司法的独立性。延及明代,由锦衣卫北镇抚司署理诏狱,亦称“锦衣卫狱”或“镇抚司狱”,可以直接拷掠刑讯官僚,取旨行事,而作为“三法司”的刑部、大理寺、都察院均无权过问。据《明史》记载:
刑法有创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东西厂、锦衣卫、镇抚司狱是已。是数者,杀人至惨,而不丽于法。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极。举朝野命一听之武夫宦竖之手,良可叹也[3]2329。
由此可见,明代诏狱其实是君主专门针对文官群体而设立的一种私刑场所。它的运转在当时的国家政治事件中起着较为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是明代君主与文官集团权力冲突外化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在明代有众多文官因为直言切谏而被逮下狱,被杖受辱,但文人士大夫所主导的社会舆论往往会对这种冲突外化予以较大反响与干预。因此就文官个人声望而言,如果是因为上疏言事,而非某种确切的罪行被逮入诏狱,那么他的名望不仅不会因为下狱受辱而玷污,反而能够得到社会舆论的普遍支持与肯定。冯从吾在其《关学编》中对吕柟因上疏而下狱之事有如下记载:
甲申,(吕柟)奉修省诏,复以十三事上,言颇过切直。时东廓亦上封事,同下诏狱,一时直声震天下,人人有“真铁汉”之称[4]43-44。
事实上,这类事例在明代朝堂上并不鲜见。当事人因敢于言事而“直声震天下”,获得“真铁汉”的赞誉,也并非君主弹压臣属的初衷。如果君主企图通过直接折辱个别文官的方式来震慑文官群体,而又难以对社会舆论加以有效地管理和疏导,就会出现这种与其愿望相违的结果。这也是明代特有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尽管身份是诏狱中的阶下之囚,这类文官的声望反而较之前更为崇高。在这批直言切谏的文官当中,就不乏众多关陇士人的身影。
二、关学与关陇士人的气质
关学作为一个学派的名称,与其发源的关中地域密切相关。我国古代将函谷关以西、大散关以东称为“关中”,大致位于今渭河流域一带。由于历史传统与生活环境的影响,这一带的人民历来以稼穑为生,具有古直朴素的民风遗存。据《史记·货殖列传》载:
(关中)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邠,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5]。
实际上,关中学养的形成和发展也与这种淳朴的地域文化氛围密切相关,而生长、浸染于这种古朴民风当中的士人则往往具有一种较为尚质求实的气质。王守仁在《答南元善》信中写道:
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沉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四方之士,吾见亦多矣,未有如关中之盛者也[6]。
作为理学一脉,关学自张载创立以来,得到了众多关中子弟的追随。张载在关中讲学时,吕大钧、吕大忠、吕大临都相继拜其为师。蓝田吕氏兄弟是关中地区的望族,他们的加入为关学发展奠定了政治和经济基础,使关学与二程的“洛学”、王安石的“新学”形成鼎立之势[7]。元代以降,杨恭懿与其父杨天德、其子杨寅三代均以讲学为生,极力倡导关学。元代文学家姚燧称颂杨恭懿为“学者宗之,西士山斗”[4]21。杨氏三代的努力,为明代关学的复兴打下了基础。
明代立国之初,上层统治者注重敦伦教化,倡导儒学,为关学在明代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条件。随着国家承平日久,教化日深,关学的影响力也进一步扩大到了今陕西北部、甘肃东部一带。值得注意的是,与一般理学的学派不同,关学尤其强调学以致用和躬行实践。作为关学弟子,大多数的明代关陇文士受到了先师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8]论调的感染。对于他们而言,对圣贤之教的学习是为了在实际社会当中应用、力行,进而达到为匡扶社稷、澄清天下目的。经由这种学理所培养的明代关陇士人,期望通过直言切谏的实际行动,来实现内心长久形成的经世理想。这也使他们倾向于认为,由谏诤所导致的下狱并非什么难以启齿的耻辱,反而是一个臣子面对大是大非时的气节所在。即使因此而受刑长系,他们也往往在愤懑悲伤过后,努力借助平素对孔孟之道的长期熏修,将内心从犹疑惊惧逐渐过渡到安之若素,进而产生了一种求仁得仁的洒脱感和自我完满的充足感。许多人在此后数十年的系狱生涯中读书写作,吟咏不辍,表现出了传统知识分子面对忧患的一种从容不迫的修养和气度。
三、明代被逮下诏狱的关陇士人特征
整体而言,明代被逮系诏狱的关陇士人主要有两大特征:一是以学问见长,甚至本身就是关学学派中的重要人物,如被称为“朝邑二韩”的韩邦奇和韩邦靖兄弟、“韩门二杨”之一的杨爵、关中状元吕柟等,均是关学传人。其中韩邦奇、吕柟在下野之后曾授徒讲学,而杨爵则在诏狱里著述不辍。他们身兼官员与学者两重身份:在朝时则是敢于犯颜直谏的文臣,在野时又成为传播关学主张的宿儒。
二是明代被逮系诏狱的关陇士人在各个时期均有,但主要集中在明代中期。这是由于明代中期的关中地区处在稳定的社会结构下,已经推行儒家教化百余年。在这一阶段成长起来的关陇士人不像明初士人那样对高压政治表现出极端的惶恐,也不像晚明士人那样,或被卷入党争难以自拔,或厌弃现实而出入佛道。由于社会经济状况趋于稳定,这一时期的关陇士人更多地思考个人对天下国家的责任感和使命意识。如果君主做出了相反的举措,那么他们往往选择抗言直谏来予以反对。在他们眼中,君臣更像是一对合作者,而不仅仅是后者趋奉前者的关系。这也部分地解释了张原、吕柟等关陇士人,为何能以个人生命与政治前途为代价,参与到“大礼议”事件当中。这种知识分子责任感和使命意识的兴起,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中明时期的文官群体力量的抬头。就全国范围来看,虽然这种意识不仅仅在关陇地区出现,但将其付诸实践的急先锋当中无疑有着关陇士人的身影。
四、明代被逮下诏狱之关陇士人简谱
(一)明代初期
马京(?—1410),字子高,陕西武功人。洪武十八年(1385)进士,授翰林编修。因敦实有容,履洁持正,升通政司使,改任大理寺卿,临事务持大体。永乐元年(1403),改任刑部左侍郎,时皇太子守北京,命马京兼辅导。马京尽诚翼护,甚赞皇太子,因此为汉王高煦所忌。汉王高煦数毁之于成祖,谪戍马京于广西。永乐七年(1409),朱棣巡北京,命百司举戍籍中有文学者,马京在其中。抵京后,犹以前事下锦衣卫狱。永乐八年四月,瘐死狱中[9]。仁宗改元,追赠礼部尚书,谥文简[10]。
马京作为追随太子朱高炽的一员,与当时许多中央文官一道,被卷入了永乐朝后期的立储之争当中。先被谪戍广西,后虽以文名被荐举回京,又以前故被逮系诏狱。数月后死于狱中,未有文集传世。
(二)明代中期
李梦阳(1473—1530),字献吉,号空同,甘肃庆阳府人。弘治六年(1493)举陕西乡试第一,弘治七年登进士第,授户部主事。迁郎中,以格势要,被构陷下狱,得释。弘治十八年,应诏上书,陈五千余言,极论得失,语及寿宁侯张鹤龄。鹤龄奏辨,摘疏中“陛下厚张氏”语,诬其讪谤母后。以此被逮系诏狱,寻宥出。途遇寿宁侯,詈骂之,且以马箠击堕寿宁侯二齿。孝宗崩,武宗立,刘瑾等八虎用事,李梦阳起草劾疏。会语泄,为刘瑾所恨,矫旨谪山西布政司经历,勒致仕。既而以他事下梦阳诏狱,将杀之,以康海救之乃免。刘瑾伏诛,李梦阳起故官,迁江西提学副使。在任所与诸同僚龃龉,被吴廷举等人劾奏。诏遣大理卿燕忠往鞫,羁李梦阳于江西广信狱,遂以冠带闲住去职。李梦阳家居,益跅弛负气,招邀宾客。宁王朱宸濠谋反事败,御史周宣劾其为宁王党羽,复被逮。大学士杨廷和、尚书林俊力救之。终以其曾为宁王作《阳春书院记》,被削籍为民,未几卒[3]7346-7347。
李梦阳《空同集》卷9中有《述愤一十七首》组诗,题下有小字注曰:“弘治乙丑年四月作,是时坐劾寿宁侯逮诏狱。”[11]又同卷收有《离愤五首》组诗,题下有小字注曰:“正德戊辰年五月作,是时阉瑾知劾章出我手,矫旨收诣诏狱。”[11]可见,他本人一生的确曾因屡次得罪显贵而被逮入诏狱。据这些狱中诗作记载,李梦阳在狱中时常与狱友聊天、散步,同时非常思念家人,期盼早日出狱,甚至产生了归隐山林的念头。在《述愤一十七首》其五诗中,称“律律南山岑,拂衣会当还”[11]。可以说,李梦阳在诏狱中所写的这些诗比较详细地叙写了他的狱中日常生活和心境变化。尤为可贵的是,他曾以《炭篓盆架》《砂锅盆》《船板床》《砖枕》《芦席几》《坏墩》《麻绳椸》《葛衫帐》为题,写了《狱中八物》组诗,在表达自己随遇而安的心态的同时,详细描摹了诏狱中的各种物事。由于李梦阳的文名盛极一时,以至于后来下狱者反复摩挲、追和其狱中诗作。像如晚明被逮入狱的方震孺、高出等人,他们在狱中对李梦阳的《狱中八物》组诗均有追和仿作。这类诗歌不仅描摹了明代士人的狱中生活,同时也为明代日常生活器具的研究提供了可资考证的文献材料。
韩邦奇(1479—1556),字汝节,号苑洛,陕西朝邑人。正德三年(1508)登进士第。授吏部考功司主事,进吏部员外郎。正德六年(1511)冬,会京师地震,以疏陈时政阙失,忤旨不报。寻谪平阳通判。正德九年(1514),迁浙江按察佥事。寻被中官王堂诬奏,称其作《富阳民谣》诗怨谤朝廷,被逮下诏狱,出狱后罢官为民。嘉靖初,起山东参议,乞休去。嘉靖三年(1524),起山西左参政,平定兵变,再乞休去。嘉靖七年(1528)起四川提学副使。后入为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修撰。主应天乡试,坐试录谬误,谪南京太仆丞,复乞归。起山东副使,迁大理丞,进左少卿,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宣府。入佐院事,进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转抚山西。历四年,引疾归。后以故官起督河道。迁刑部右侍郎,改吏部。拜南京右都御史,进兵部尚书,参赞机务。致仕归。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十二日(即1556年1月23日)陕西大地震,不幸罹难。赠太子少保,谥恭简[3]5317-5319。
据《明史》记载,正德九年(1514)韩邦奇在浙江按察佥事任所,因作《富阳民谣》诗遭到宦官王堂的弹劾,随后被逮系诏狱。就其《苑洛集》中所收录的相关诗文作品来看,韩邦奇在诏狱中的活动主要是读书、作诗,偶尔也会下棋。他曾在《北司狱中联句序》一文中述及自己下狱后与狱友相处融洽,因此往往联句遣怀尽兴,打发时间:“余既为守臣状论,征诣京师,下锦衣北司狱。越二十余日,东岩以言礼并系,又二十余日,于是各出所怀,相得甚欢。或物感必为诗,诗必联,联止尽意,不求工也,故虽拷掠禁锢,不觉有愁苦状。”[12]显示出了一种“求仁得仁”的安然心态。就其下诏狱后的思想动向而言,韩邦奇曾以集李白诗的方式袒露心迹,在《狱中集古》诗中称:“松柏本孤直,虬龙盘古根。瑶草寒不死,犹怀明主恩。”[12]并与狱友徐文华联句作诗,互相砥砺气节,在《狱中》其二诗中称:“平生点检知无愧,尘世何劳较是非。”[12]至于因写《富阳民谣》诗而被逮入狱一事,韩邦奇虽然在《狱中》其六诗中自谦此举乃是“瞽言无补圣明时”[12],但始终认为自己是为当地百姓的福祉做出了努力,并不以此为憾。
韩邦靖(1479—1556),字汝度,号五泉,陕西朝邑人。弘治十四年(1501),年十四即举于乡。正德三年(1508)与兄邦奇同举进士,时称“关中二韩”。登第后授工部主事。于浙江征收木材,因数额不足而被弹劾,以廉得免。进员外郎。正德九年(1514)京师地震,乾清宫被大火烧毁,韩邦靖上疏指斥时政甚切,触怒武宗,被逮下诏狱。给事中李铎等为其进言论救,乃削职为民,家居八年余。嘉靖初,起任山西左参议,分守大同。数次力请朝廷赈饥,不得报。以病上疏乞归,不待命辄行。抵家两月即卒,年仅三十六[3]5319。
据韩邦奇所作《韩邦靖传》载,正德九年(1514)乾清宫毁,武宗以灾异下诏求直言者,韩邦靖即上疏曰:“……臣窃见陛下自即位以来,朝政不修,经筵罔御,盘游无节,狭近群恮。摧折骨鲠之臣,闭塞谏诤之路,百度乖违,庶事丛脞,府库空竭,闾阎流散,寇贼灾异荐至。迭兴危乱之形,已成社稷之忧,将大倾者。……不意陛下徒事虚文,不修实政。凡诸过举,仍遵往辙。臣工章疏罔有施行,而部官黄体行乃又以言罢去,天下人心莫不嚣然沮丧。”[12]因此触怒武宗,被逮入诏狱。韩邦奇下狱后曾作《狱中丝帐》《狱中寄友二首》等诗。其《狱中寄友二首》其二诗曰:“虚室通云气,幽门借日光。微臣抱愚悃,万一动君王。”[13]就诗中所流露的意思来看,韩邦靖始终怀有一种直臣的情结,并不为自己的逆鳞触颜的行为感到后悔。
吕柟(1479—1542),字仲木,号泾野,陕西高陵人。弘治十四年(1501),举于乡。正德三年(1508),登进士第一,赐状元及第,授翰林院编修。刘瑾以其为同乡,欲招引接纳,吕柟谢不往。居官二年,以宁夏边患,上疏请帝入宫亲政、潜消祸本。刘瑾恶其直,欲杀之,遂引疾返乡。正德九年(1514)刘瑾伏诛,吕柟起故官。乾清宫灾,应诏疏陈六事,劝武宗举直措诸枉,皆不得采纳,遂再次引疾告归。嘉靖元年(1522),起复故官,纂修《武宗实录》。次年任会试考官,采择士人。嘉靖三年(1524)四月,以十三事自劾,中有“大礼未定,谄言日进”句。世宗震怒,逮下诏狱,寻谪为解州判官。讲学于解梁书院,四方从学者众。嘉靖六年(1527)任南京吏部考功郎中,升尚宝司卿,讲学于鹫峰寺。嘉靖十一年(1532)升南京太常寺少卿,嘉靖十四年(1535)任国子监祭酒,整顿监规,上疏申明五事,得以允行。寻升南京礼部右侍郎,仍在任所讲学。嘉靖十八年(1539),致仕返乡,讲学于北泉精舍。生平所至皆以讲学为事,门生众多,几与王学中分其盛[14]。
嘉靖三年(1524)四月,吕柟上疏自劾,因言辞关涉大礼,被逮入诏狱。不久出狱,谪为解州判官。吕柟入狱时间较短,在狱中写有《狱中次东郭杖后憩桑林韵》《杖回同东郭观桑椹》《谢诸公馈食狱中》《狱中酬谿田诸君六绝句》《气楼》等诗歌。从其中部分诗题可知,吕柟在狱中曾经受杖刑,但他受杖之后并未失志,虽然在《狱中次东郭杖后憩桑林韵》诗中表达了“浮云蔽白日,屏翳不能开”[15]的担忧,但是终究在《风雨》诗中写道:“风雨无心天自定,荣枯有数物皆然”[15]。被逮系诏狱后,吕柟除了作诗,有时候也与狱友一道,对一些文学作品进行品评。比如他曾在诏狱中写过《与东郭评杜少陵诗作》诗,这说明他在下狱期间曾就杜诗与狱友进行讨论、切磋。此外,根据其《廖鸣吾寄骞林茶至狱》诗、《隔山消》诗中所透露的信息来看,吕柟下狱期间不乏有人寄送物品。《廖鸣吾寄骞林茶至狱》诗中的“骞林茶”,是湖北武当山出产的一种名贵茶叶。据汪灏《广群芳谱》载:“太和山(按,今武当山)骞林茶,初泡极苦涩,至三四泡,清香特异,人以为茶宝。”[16]而“隔山消”则是白首乌的一种,又称作“牛皮消”,具有清热凉血、解毒疗疮的作用,属于药品。这类物品均从狱外带入,在当时并非易事。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21《禁卫》“镇抚司刑具”条记载:“每市一物入内,必经数处验查,饮食之属,十不能得一。又不得自举火,虽严寒不过啖冷炙、披冷衲而已。家人辈不但不得随入,亦不许相面。”[17]吕柟诗中的这类信息不仅为了解吕柟的狱中日常生活提供了可资考证的材料,同时也为明代地方物产等相关情况提供了一些佐证。

杨爵先后系入诏狱七年,常与狱友周怡、刘魁讲论、探讨儒家经籍要义,在狱中写有《周易辨说》《中庸解》等著作,同时留下了一些诗文作品。由于杨爵系狱前后七年,时间较长,在狱中的各类作品也较为丰富,使我们能够较为详细地考察其狱中生活。杨爵在《苏宣传》中记载,自从系狱之后便被“昼夜锁”,以至于“右胫前为木转磕成疮”[19]。同时他一度曾遭到狱卒的刁难和欺凌,在《漫录》中记述道:“予系此四十一月矣,逻者日在侧,觇予动作。有甚厚予携壶酌以伸问者,后一人来,甚横逆。予卧于旧门板上,阻之以席,其人皆扯毁之,谓予罪人,不宜如此。”[19]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杨爵仍能尽量保持一种安之若素的达观思想,他曾在《杂咏五首》其五诗中称:“要信乐天为乐土,须知忧世是忧身。有诗吟咏忘颠沛,仿佛羲皇境上人。”[19]由于这种精神上的达观,以至于他的一些狱中诗作竟然能够显露出一种闲适的情趣。例如其《初夏二首次韵》其二诗曰:“日上圜墙景寂然,老囚于此尚安眠。好怀还有四时兴,世故全无一念牵。糯米煮从沙釜里,诗书堆在枕衾边。何翁若解吾真乐,日食何须破万钱。”[19]杨爵表现出的这种“素患难行乎患难”[20]的笃定,较为典型地代表了明代中期下狱的文人士大夫的良好心理素质。作为圣贤孔孟的信徒,这批人既然敢于主动上疏言事,那么也就做好了为言事而牺牲的心理准备。诏狱中的困苦艰难在杨爵看来,正是客观环境对自己多年所学的一种考验,而儒家经典中所提倡的君子安于忧患、知足守分等品行也因此在其身上得以充分地体现。
赵时春(1509—1568),字景仁,号浚谷,甘肃平凉府人。嘉靖元年(1522),举于乡。嘉靖五年(1526),会试第一,选庶吉士。嘉靖六年(1527),授刑部河南司主事。嘉靖九年(1530)七月,以上疏言事得罪,被逮入诏狱掠治,黜为民。嘉靖十八年(1539)五月,召为翰林院编修,兼司经局校书。嘉靖十九年(1540),世宗有疾,时春与罗洪先、唐顺之疏请太子来岁御殿,受百官正旦朝贺。触怒世宗,复黜为民。嘉靖二十九年(1550),京师被寇,以徐阶荐,起兵部职方司主事。嘉靖三十年(1551),任山东按察兵备佥事,统练民兵。次年转山东按察司副使。嘉靖三十二年(1553)二月,擢佥都御史,巡抚山西。九月,蒙古骑兵入侵山西神池、利民诸堡,时春率马步兵往御之,败绩而还,免山西巡抚,回籍听调。居家而终[21]。
据刘景荣《赵时春年谱》记载,嘉靖九年(1530)六月二十五日、七月二日赵时春先后两次上书,七月三日被逮系诏狱拷掠,七月十五日被黜为庶民[21],则其在狱时间仅十余日。尽管《明史》载其以上疏言事触怒世宗系狱,但就赵时春本人狱中诗作看来,他似乎认为自己更多的是遭到了政敌的打击和陷害。他在受逮时所作的《受械时赋》诗中写道:“岂甘摇尾辞罗网?犹意盛囊赐属镂。寄语悠悠行路客,腰金衣紫欲何湏。”[22]在明志的同时,明白无误地对那些“腰金衣紫”的“行路客”施以嘲讽。不仅如此,他还在《七月三日下锦衣狱》诗中直言“不辞落陷阱,搔首谩吟哦”[22],可见他认为自己的下狱是落入了政敌布设的陷阱。尽管如此,赵时春在诏狱中仍能自我勉励。他在《狱中对雨》诗中写道:“好雨来何处,悲风欲暮栖。带云同下上,落地自东西。景象窥天小,光华映日迷。吾心适有契,如晦更闻鸡。”[22]其中末句语出《诗经·郑风·风雨》:“风雨如晦,鸡鸣不已。”[23]常用以比喻恶劣环境中仍能保持不屈不挠的意志。赵时春以此来鼓励自己,不要因为下狱而改变君子的气节和操守。
(三)明代晚期

据刘宗周《闻诏狱惠君世扬之耗记事》载:“惠元孺先生,西(按,当为清)涧人。傥亮负奇气。……及大洪之及于难也,公亦坐赃削夺,与十五人同祸,而小人怒未洩,会六人称爰书,刑书李养正等突入公,为六人发纵,于是奉旨复逮诏狱,拷讯诬伏,至是自镇抚司发刑部,从重拟罪,尚缓须臾之死乎?未可知也。”[26]又文震孟《孝思无穷疏》载,惠世扬下狱之后,“身被五毒,体无完肤”[27]。然惠世扬未有文集传世,其狱中情形亦难稽考。唯在其转刑部狱之后,狱友方震孺在其《方孩未先生集》中曾言及二人相濡以沫的情形。据方震孺《卖床叹》诗序称,二人在刑部狱中经常“薪水断绝”,幸好囚室中有废床一张,便一道“借卖度日,遂得十日饱。”[28]不仅如此,惠世扬在狱中曾经两次一氧化碳中毒,方震孺有《惠元孺先生为煤熏者再既绝复苏志感》组诗八首,以戏谑语记其凄凉事。两人在狱中相互扶持,聊以度日。方震孺写有《足冷不眠者久矣元孺以汤婆见借感赋三首》组诗,可知狱中苦寒之时,惠世扬曾将“汤婆”借给方震孺暖足。“汤婆”是一种盛热水放在被中取暖用的扁圆形壶,用铜锡或陶瓷等制成,作用类似于我们现在所用的热水袋。《东南纪闻》卷3载:“锡夫人者,俚谓之汤婆,鞲锡为器,贮汤其间,霜天雪夜,置之衾席,用以暖足,因目为汤婆。”[29]而惠世扬在狱中逢遇生辰时,方震孺则为其作《惠元孺先生狱中初度三首》组诗以庆祝生日,可谓患难之交。
[1] 陈澔.礼记集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13.
[2] 张忠炜.“诏狱”辩名[J].史学月刊,2006(5):117.
[3] 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4] 冯从吾.关学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7.
[5] 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3261.
[6] 王守仁.王阳明全集:第2册[M].北京:红旗出版社,1997:445.
[7] 宣朝庆.张载[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11:47.
[8] 张载.张子全书:卷14[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9] 明太宗实录:卷130[M].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2604.
[10] (正德)武功县志:卷3[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 李梦阳.空同集:卷9[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 韩邦奇.苑洛集[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3] 韩邦靖.韩五泉诗:卷3[M]∥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62册.明嘉靖十六年赵伯一刻本.
[14] 马理.南京礼部右侍郎泾野吕先生墓志铭[M]∥谿田文集.明万历十七年刻清乾隆十七年补修本.
[15] 吕柟.泾野先生别集[M].清道光二十三年三原李锡龄刻本.
[16] 汪灏.广群芳谱:卷18[M].清康熙刻本.
[17]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8:538.
[18] 黄宗羲.忠介杨斛山先生爵[M]∥明儒学案.北京:中华书局,1985:168.
[19] 杨爵.杨忠介集[M].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0]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31.
[21] 刘景荣.赵时春年谱[D].兰州:兰州大学,2010.
[22] 赵时春.赵浚谷诗集:卷1[M].明万历八年周刻本.
[23] 方玉润.诗经原始[M].北京:中华书局,1986:220.
[24] 清涧县志编纂委员会.清涧县志[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1:760.
[25] 谈迁.北游录[M].北京:中华书局,1960:337.
[26] 吴光.刘宗周全集第四册[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144.
[27] 文震孟.孝思无穷疏[M]∥明经世文编:卷500.明崇祯平露堂刻本.
[28] 方震孺.方孩未先生集:卷8[M].清同治七年树德堂刻本.
[29] 佚名.东南纪闻:卷3[M].清守山阁丛书本.
[责任编辑朱伟东]
StudyofLiteratisfromGuanlongintheImperialEdictPrisonintheMingDynasty
GAO Lu
(CollegeofChineseLiterature,LanzhouUniversity,Lanzhou730020,China)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intellectuals were caught and sent into the imperial edict prisons in Ming Dynasty, among whom intellectuals from Guanlong made up the largest number. Influenced by modesty and plainness, as well as the personal practice of Guan School, they often had dual identity: scholars and officials, they respected integrity as scholars and were brave enough for expostulation and dissuasion. Generally, the imprisoned literatis from Guanlong had two features: firstly, they were knowledgeable and resourceful, even some were important and influential people in Guan School; secondly, this situation was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middle of the Ming Dynasty, which wa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economic situation and social thoughts at that time. Study of this group of people is helpful for 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al attitud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intellectuals from Guanlong in Ming Dynasty.
Ming Dynasty; imperial edict prison; literatis from Guanlong
K248
A
1001-0300(2017)06-0056-07
2017-03-21
兰州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自由探索项目(15LZUJBWZY002)
高璐,女,陕西榆林人,兰州大学文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明代文学、文献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