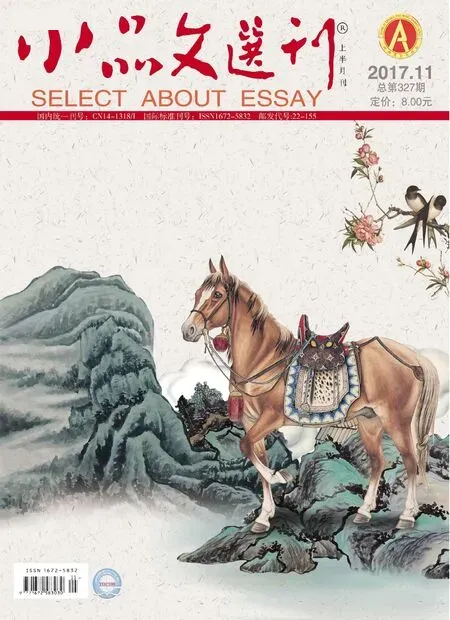人在草木间
2017-11-25刘梅花
□刘梅花
人在草木间
□刘梅花
人在草木间,说的是“茶”,可是不单单指茶,也是禅。
陆羽说,茶者,“南方之嘉木也。”令我这个北方人羡慕不已。而且,我还没有去过南方呢,不曾见过南方的嘉木。总是想,茶树,是怎样一种禅意的树呢?嘉木在野,诗经里一样风雅了。那百年的古茶树,老得禅意,老得孤独,动不动还要开花吧?
茶树一直长在我的梦里,从童年一直开花到现在。我的梦都是茶树的枝枝叶叶里长出来的。你以为我喝了多少好茶,对茶叶如此痴迷?其实也没有。穷人家的孩子,最先想的是要吃饱饭才好。至于茶,当然也是喝的。穷到连茶都不能喝到,人生就没有意思了,还不如当初就不要来尘世呢。
我喝茶,一直喝那种黑茶,也叫砖茶。很大的一块,坚硬,可以拿来打狗,砌墙。从小,喝黑茶。茶块在炉火上烤一烤,变得酥软了,很轻松地撬成碎块儿,盛在匣子里。煮茶的时候,取一块。那茶叶,粗糙,黝黑,却有一脉暗暗的清香,像我的日子。清早,生了火,先熬一壶茶。要熬得酽一点,不要太淡。茶熬得有了苦味儿,好了。伸长脖子灌下去一杯,上学去了。这样的一天,神清气爽。若是哪天缺了这一杯,总是蔫,打盹,头疼。
冬夜里,写完作业,爹熬着的茶已经清香扑鼻了。若是有钱的话,还能买了红枣,在清茶里下几枚,喝枣茶。没钱就丢几片姜,抗寒,暖胃。一家人围着火炉喝茶,任凭我说一些废话,狼筋扯到狗腿,没来由地乱说一气。我说,茶树应该很高,都长到半天里去了,仰头看,那茶花儿就开在蓝天里,和我一样大的花儿呢。爹听着,黄瘦的脸上还是笑容,吸一口烟,慢慢喝下去枣红颜色的老茶。有时候,弟弟谴责我说:爹啊,梅娃子最能胡诌,你信她做什么?爹一笑,不说话。漫长的冬夜,煮沸在一壶茶水里。炉火红红的,照在我脸上。爹笑着说,你看,我的黄毛丫头,红脸蛋。又说,梅娃子刚生下来,猫儿一样大。我隔着门看了一眼,脸上皱皱巴巴的,很难看,谁知道长大了这么让人心疼的。那样的日子,像茶,慢慢熬着,吸溜吸溜喝着。慢慢长大了。
天祝藏区的人唱酒曲,最有名的真兰歌是这样唱的:
对有恩的犏乳牛要知道报答。你如果没有喝过淡茶,你就不知道犏乳牛的恩情,你喝过淡茶才知道了犏乳牛,犏乳牛却在哪儿呢?
对有恩的父母要知道报答。你如果还没有接近暮年,你就不知道父母的恩情,你如果到了暮年才想起父母,父母亲却在哪儿呢?
我的朋友是一位藏族诗人,他最喜欢唱这首歌,他先用藏语唱,再用汉语唱,一遍一遍,歌声清亮真挚。唱到最后,我常常泪流满面。我的父亲,一直喝清茶。等我煮好满满一碗奶茶的时候,我的父亲又在哪里?他去世那么早,还未来得及给我筹备两麻袋砖茶的嫁妆。
草木是有气脉的,所以茶才有灵魂。有些草木,成了草药。有些草木,却成了茶,真是世事玄机啊。水煮草木,你知道哪个是药,哪个是茶?草木不会泄露天机。草木也不说话,却把味道交给你,心交给你。人在草木间,天地自有玄理。至于做茶做草药,都行,在于自己喜欢哪个。
选自《散文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