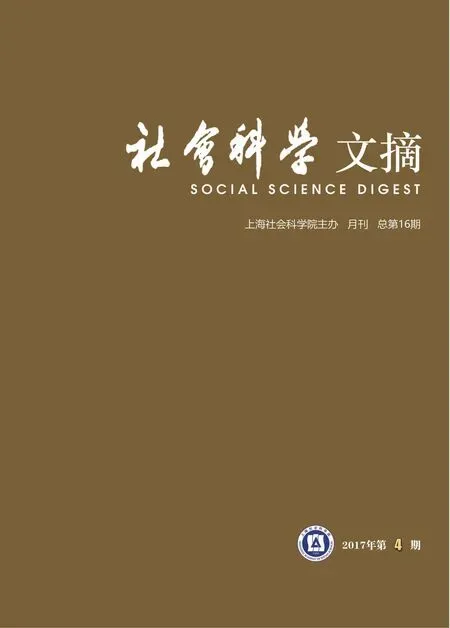西方世界中国哲学研究者的“三重约束”
2017-11-21黄勇崔雅琴
文/黄勇 译/崔雅琴
西方世界中国哲学研究者的“三重约束”
文/黄勇 译/崔雅琴
中国哲学在西方特别是在美国的状况不尽如人意,一个直接原因在于,西方主流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缺乏兴趣,而这种缺乏本身既导致又成因于他们对中国哲学价值的无知。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有责任激发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兴趣,尤其是通过展现中国哲学恰好可以对西方主流哲学家所关注的(至少某些)问题提出一些有意思的观点。我们的做法是:“虽然我们让西方哲学决定讨论什么问题,但我们让中国哲学对全部问题有最终发言权。”在西方哲学语境中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专家,除了要接受奥伯丁所谓的“双重约束”——即应该能够向西方主流哲学家表明,中国哲学传统中有一些既为西方哲学家所不熟悉,而又不是他们完全不熟悉的东西,还需要接受第三重约束,即他们向西方哲学家所呈现的中国哲学,应该是建立在对中国哲学家的认真的文本和历史研究基础上的。
英语世界中国哲学研究的困境
毫无疑问,中国哲学在西方特别是美国哲学界的状况不尽如人意。虽然美国哲学协会年会东部、中部和西部各分会上中国哲学专场的数量有了显著增加(尽管仍然主要出现在小组议程而非主要议程),同时研究中国哲学的英文出版物数量也有较大提高,但至少依旧存在两大问题。
其一,在研究型大学,尤其一流研究型大学里,缺乏具有中国哲学专长的学者。布鲁雅(Brian Bruya)最近便对此作了一番研究,结果发现:“在具有博士项目的美国大学哲学系从事专职中国(或亚洲)哲学研究的所有九位学者中,只有四位一开始是作为中国(或亚洲)哲学学者而被招聘的(其余的都是以西方哲学的某专长,如伦理学和古希腊哲学,而进入具有博士项目的哲学系,他们或者一开始对中国哲学也有一些兴趣,或者只是在进入这些研究型哲学系以后才开始从事中国哲学研究)。而全美哲学博士项目中总共仅有九位专职中国哲学学者能够指导博士学位论文。”
其二,与研究中国哲学或亚洲哲学的专门刊物相比,综合哲学期刊发表的中国哲学论文少之又少。奥伯丁(Amy Olberding)发表在近期美国哲学协会通讯上的研究专门探讨了这一问题。她发现综合哲学期刊自1940年以来每10年只刊发了3-4篇中国哲学方面的论文,且无增长之迹象。
当然,上述两项研究不过是证实了中国哲学研究者很久就已经有的,尽管有些含糊的共同感觉。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扭转这种不尽如人意的局面?本文将突出在笔者看来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在英语世界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应该而且可以受到奥伯丁所谓的“双重约束”。由于这样的研究有可能被指责为对中国哲学断章取义,我在本文的结语部分将说明从事这种研究的学者还需满足第三重约束。
英语世界中国哲学研究者的“双重约束”
要扭转中国哲学在英语世界的这种边缘状况,必须先弄清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万白安(Bryanvan Norden)所说的“沙文民族主义”或布鲁雅所说的“对多元文化主义的隐性排斥”,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合乎事实,尽管主流西方哲学家可能不会予以承认。然而,笔者认为更为直接的原因在于,西方主流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缺乏兴趣,这种缺乏本身既导致又成因于对中国哲学(之价值)的无知。布鲁雅所讲的一则逸闻清楚地反映了这一点。布鲁雅了解到美国某大学的哲学系想建立一个全美排名前十的哲学博士项目,于是就问该系的系主任,他聘用了哪位中国哲学专家来帮助他达到这个目标。这位系主任的回答让布鲁雅感到很吃惊:“中国哲学有助于解决那些当今哲学家致力研究的问题吗?”言外之意是说,第一,倘若中国哲学有助于解决当今哲学家致力研究的问题,那么哲学系自然会聘用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第二,中国哲学无益于此。
我们完全可以质疑上述第一点:即使(或者正因为)中国哲学不能帮助解决当前哲学家所关注的问题,哲学系仍应该聘请研究中国哲学的专家,这样他们可以引进西方哲学家目前没有关注但应该关注的问题,从而开阔他们的视野。不过,本文旨在质疑第二点:中国哲学不能帮助解决西方主流哲学家目前所关注的问题。当然,要使他们信服,我们这些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不能只是抱怨现状,而是应该比西方主流哲学家承担更多的责任来扭转这一不尽如人意的局面。事实上,他们既然不了解中国哲学,我们就不能指望他们某天突然来兴致阅读中国哲学,因为他们确实忙于处理一些令他们同时也令我们或应当令我们感兴趣的哲学问题。相反,我们有责任激发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兴趣,尤其是可以通过展现中国哲学恰好可以对西方主流哲学家所关注的(至少某些)问题提出一些有意思的观点。
正是在这一点上,笔者极为赞同奥伯丁的观点。她认为,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在提高西方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兴趣方面存在双重约束。一方面,他们不仅需要“紧扣主流话语中已有的问题、兴趣点或范式”,而且必须解释中国哲学能就这些问题、兴趣点或范式提供一些主流话语没有讲到的东西。这一点很重要。如果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不把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联系起来,或者即使把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联系起来了,但仅仅说明了两者有类似的思想,或者还进一步发现了中西哲学之间的某些差异,但不能说明中国哲学也是有意思的、合理的或有说服力的(如果不能证明中国哲学比西方哲学更有意思、更合理或更有说服力的话),那么就几乎不可能让那些对中国哲学还不感兴趣的西方哲学家开始对中国哲学产生兴趣。另一方面,如果研究中国哲学的学者使中国哲学观点看起来“极为怪异,偏离受西式教育的哲学家所熟悉的思想,那就会引发另一种类型的抗拒”,因为对于西方主流学者而言,这些观点可能看起来是非哲学的,属于他们眼中的东方神秘主义。奥伯丁如此概括西方主流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研究者提出的、在她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因而也是不合理的双重约束:请你们告诉我们一些我们在西方哲学中没有见过的东西,但同时要保证这些东西看起来确实是我们所熟悉的、我们称之为哲学的东西。
笔者曾在《如何在西方哲学语境下研究中国哲学:为中国哲学引入一种独特方法》一文中表达过类似的,但乐观得多的观点(该文的一些主要思想后来成为拙著《为什么应该是道德的:师法二程》绪论的主要部分),尽管那时笔者的关注点并不是想扭转中国哲学在西方不尽如人意的状况这件事。笔者当初主要关注的是如何在西方哲学语境中研究中国哲学,但关键点也在于如何激发西方主流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的兴趣。要回答如何在西方哲学语境中研究中国哲学的问题,就必须回答我们为什么要在这样一种语境中研究中国哲学;而要回答这一问题,就必须弄清楚我们自己的中国哲学论著是写给谁看的。当然,我们的论著也要写给研究中国哲学的同行看的。然而,如果我们想要把广大的西方哲学家当作受众——我认为这一点很重要——那么,我们就必须追问,为什么这些对中国哲学知之甚少,甚至一无所知的西方哲学家应该对它感兴趣。我认为一个重要的答案在于,中国哲学即使在今天西方哲学家所感兴趣的问题上,也能作出一些重要的贡献。
若想做好这项工作,我们首先应该熟悉西方哲学家关注的问题,西方哲学传统就这些问题所发展出来的不同观点,以及这些观点面临的问题;其次,我们要看看中国哲学家关于这些问题是否有不同的、更好的观点。这在本质上就是奥伯丁所说的双重约束,只是在表述顺序上颠倒而已。为了更清晰地呈现这种双重约束,笔者曾作如下陈述:“虽然我们让西方哲学决定讨论什么问题,但我们让中国哲学对这些问题有最终发言权。”由于我们并不认为中国哲学整体上优于西方哲学,这种比较研究所选择讨论的问题不可能是系统性的。一方面,在这样的比较研究中,至少在初始阶段,我们将不讨论某些在中国传统中可能非常重要,但对西方哲学家而言太过陌生或很难与他们目前所关注的问题相关联的问题。另一方面,还有一些重要的哲学问题,要么西方哲学家已经提出令人满意(或至少比任何可以在中国哲学传统中发现的观点更令人满意)的看法,要么西方哲学所发展的观点虽令人不甚满意,但中国哲学也无法提供更好的看法。我们的比较研究不涉及这两方面的问题。
关于这种研究哲学的方式,应说明以下几点:
第一,虽然旨在从中国哲学中寻找更好的办法解决西方哲学传统提出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采用这种办法的学者必须先确定一个西方问题,然后才开始从中国哲学中寻找其解决方案。某些情况下可能确实会这样做,但研究者也可能先是觉得某个中国哲学的观点特别有意思且意义重大,然后去看西方哲学家如何应对类似的问题。然而,这两种方式都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有时候,研究者可能看到西方哲学传统关于某一具体议题的代表立场很成问题,但在中国哲学中找不到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另一些时候,研究者可能发现某个中国哲学观点特别有意思,但它对于解决西方哲学中的问题并无助益,因为它所涉问题不是西方哲学所要处理的,或是因为西方哲学自身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发展出了同样有意思或更有意思的见地。在大多数情况下,从事比较研究的学者或多或少都熟悉中西传统,可以判断中国哲学中的哪些问题最有可能帮助解决西方哲学传统中的问题,然后仔细研究这两个传统在这些问题上的一些具体看法。
第二,尽管这种研究中国哲学的方式旨在解决西方哲学传统提出的问题,但它并不会像初看起来那样存在歪曲中国哲学的危险。一方面,它不同于试图利用当代西方哲学流行的理论来解释中国传统哲学的做法,那样的话可能确实会歪曲中国哲学。例如,针对当下美德伦理的问题提出儒家的解决方案,我们不必主张或论证儒家伦理也是一种美德伦理,至少不必说它是一种西方意义上的美德伦理。另一方面,诚然,这种研究方式所呈现的中国哲学图景是不完整的,但它本就无意呈现一幅完整的中国哲学图景。这是说,它只是研究中国哲学的一种方式,需要其他很多方式加以补充和支持。
第三,显然,这种研究中国哲学的方式不仅仅是文本研究,因为它旨在为目前西方哲学家所关注的问题提出新的、有意思且合理的解决方案,而不仅是提供一种“富有洞见的解释,以尽力复原文本写作的最初情景,进而有可能把握作者原意”。不过,更重要的是,它也不同于可能易于与之混淆的纯粹的哲学建构。纯粹的哲学建构存在以下危险:它“一开始就和激发了哲学建构努力的历史资源相疏离”,因为“一个人如此开展研究时,可能不会直接从所比较的两个传统中引经据典,虽然他可能用脚注来解释自己思想之根源”。为了证明中国哲学可以对解决当代西方哲学家所感兴趣的问题作出重大贡献,就需要证明这些贡献确实基于对中国哲学文本的扎实研究、仔细分析与合理解释,而这一坚实基础得经得起对同一文本其他解释的挑战。尽管我们在运用中国哲学文献去挑战西方哲学观点时必须进行筛选,但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在运用这些文献时不会歪曲它们在原始语境中的含义。就此而言,布鲁雅最近一项以中国哲学视域挑战西方哲学的重要研究与此处倡导的研究有所不同(至少从他的构想而非他或其项目参与者的实际开展情况来看),尽管笔者对他的研究深表赞赏,因为布鲁雅的研究“并不要求明确提及中国哲学资源,即使它的主要观点必须包含中国传统,至少把中国传统作为灵感的源泉”。
第四,奥伯丁正确地强调,“试图促使人们对非西方传统感兴趣的中国哲学学者所面临的这种双重约束对这些学者提出了一种迫切而不可能达到的要求”,因为要求我们深入了解两种传统。处理这个问题有一个方法:不管是就具体的研究项目而言,还是就一般的哲学兴趣而言,把研究的重点缩小到形而上学、认识论、伦理学、政治哲学等哲学的子域。比如,如果想看荀子将如何回应针对美德伦理学的情境主义批判,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充分掌握针对美德伦理学的情境主义批判和《荀子》文本,而这能办得到。同时,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也不应把熟悉西方哲学的当代著述视为一种额外的负担,因为那也是一种有意义的经验。中国哲学并没有在总体上优于西方哲学。就某些论题而言,西方哲学比中国哲学有更好的东西要说,我们可以从中学到很多;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即使在那些中国哲学有更好东西要说的问题上,我们研究西方哲学仍然可以获益良多。
在英语世界研究中国哲学的第三重约束
本文试图说明,至少是为了改变中国哲学在西方哲学界的边缘地位,在西方哲学语境中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专家可以且应该在其研究中接受奥伯丁所谓的二重约束。就是说,他们应该能够向西方主流哲学家表明,一方面,中国哲学传统中有一些为他们所不熟悉的东西,而另一方面,这些东西也不能是他们完全不熟悉的方面。这是奥伯丁对这个双重约束的表述。换句话说,一方面,中国传统哲学家也能参与讨论西方哲学家今天所感兴趣的问题,而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哲学家在这些问题上所持的一些看法不仅与西方哲学传统中的有代表性的看法不同,而且可能比后者更有道理。这是笔者对这个双重约束的表述。但不管是奥伯丁的还是笔者的表述,这种双重约束似乎都会使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所进行的工作有断章取义之嫌。
关于这样的批评,一方面,我们必须说,在从事学术研究中一定的抽象(这里所谓的抽象指的是将一位哲学家的某个思想从其上下文中抽离出来,而不是指与具体相对应的抽象,尽管这两种抽象也不是完全没有关系)是不可避免的。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必须注意到,当我们把某个哲学家的某个思想从其哲学体系中抽离出来时,也确实有断章取义和歪曲原意的可能。怎么避免这个问题呢?笔者认为,这里我们必须区分一位学者的研究过程和其写作过程。虽然我们不得不承认,在我们从事写作时,我们只能关注某个哲学家的某个方面,但这种写作是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的,而在从事研究时,我们就必须把我们所关注的这个哲学家思想的某个方面与别的方面联系起来,甚至把这个哲学家的思想与影响了他的以及被他影响的其他哲学家的思想联系起来。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我们对某个特定研究中所关心的这个哲学家思想的某个特定方面的理解是正确的,从而我们可以将这个因此而得到正确理解的方面从其所属的这个哲学家思想的其他方面合理地抽离出来,以回应当代西方哲学家所关心的问题。就笔者有限的经验而言,只有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才能在中国哲学中真正发掘出能对当代西方哲学家所关注的问题作出贡献的资源。因此,在西方哲学语境中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在其从事本文所推崇的那种研究时,除了上面提到的双重约束外,还需要接受另一约束,即第三重约束:他们向西方哲学家所呈现的中国哲学,应该能够得到在中国哲学语境中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的认可,也就是说,这是建立在对中国哲学家的认真的文本和历史研究基础上的。
(黄勇系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教授,崔雅琴系华东政法大学校报编辑;摘自《文史哲》2017年第2期;原题为《西方世界中国哲学研究者之“三重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