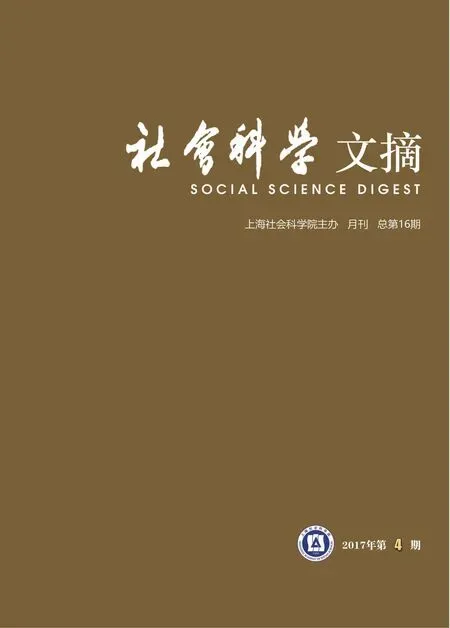学科特质、评价标准及研究范式
——高等教育学发展不能回避的几个问题
2017-11-21龚放
文/龚放
学科特质、评价标准及研究范式
——高等教育学发展不能回避的几个问题
文/龚放
把握学科特质:“像河一样无常流淌”,抑或“像树一样依次生长”?
事实上,人类认识客观世界所形成的知识系统是复杂多样的,是有各自的特性、特质的,不能用狭窄的口径、单一的尺度去观照、衡量,去约束、规范。英国学者托尼·比彻曾经专门论述不同的知识体系和学科文化,他把既有的学科分为两类,其一是“规则性结构领域(areas of contextual imperative)”,即“具有严格定型的解释顺序,每一项新的研究成果在整个知识的描述中有它适当的位置”,它们“像一棵树一样不断生长,每一新的树枝又依次生长出新的嫩枝”。此类学科最典型的例证就是,俄罗斯化学家门捷列夫发现元素的性质随着原子量的递增而呈周期性的变化。他编制了第一个化学元素周期表,不仅把已经发现的63种元素全部列入表里,初步完成了使元素系统化的任务,而且还在表中留下空位,预言了类似硼、铝、硅的未知元素的性质。第二类学科属于“联合性结构领域(areas of contextual association)”,它们“由许多观念群构成,没有明确具体的框架”,好像“河在流淌,流向无常”。例如,关于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认识,显然无法像元素周期表和太阳系行星运行规律等“规则性结构领域”的知识那样精确无误而且可以重复验证,它们往往充满着不确定性,而且不可重复,难以类比。例如,同样是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中国的红卫兵运动与法国的“五月风暴”,以及席卷美国的反越战学潮,就有着完全不同的动因,呈现的形态和产生的影响也截然不同。
此后,托尼持续不断地对学科分类、学科特质以及学科文化进行调查研究,并将自己的新见解发表在与保罗·特罗勒尔合著的《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一书中。其中最有价值的贡献是:将广义上的学科分为“纯硬科学”、“纯软科学”、“应用硬科学”与“应用软科学”等四类;依据学科研究对象的特点、知识发展的性质、研究人员和知识的关系、研究流程、研究成果的信度和研究标准及研究成果的表现形式等等,总结归纳了不同学科的“现实特征”,“即学科研究特点与现实世界的差异”。在托尼看来,存在不存在一个逻辑严谨、天衣无缝的学科整体框架,是区分硬科学还是软科学的重要标识。所谓硬科学,是指“逻辑严谨的一系列观点,就像我们做拼图一样,每一个新的学术发现都天衣无缝地镶嵌进这幅图画里”;而所谓软科学则“表示各种观点链接松散,没有很强的关联性,没有很强的整体发展框架”。
令人感概的是,迄今为止,我们在讨论学科建设时,很少考虑软科学与硬科学这一基本的差异。我们在检验和判定是否构成一个真正的学科,是否已经从“前学科”或“潜学科”发展、成长为独立的、成熟的学科时,最看重的判据就是:是否拥有严密、严整的学科理论体系,即“特有的概念、原理、命题、规律等所构成的严密的逻辑化的知识系统”。而我们学科建设的首要目标,也无一例外地将学科理论框架的确立,将特有的概念、范畴、命题、原理、规律等构成的严密的、逻辑化、体系化的理论框架,作为我们追求、向往的“金苹果”!根本没有考虑它是否是一个主观想象的、实际并不存在的东西!
《高等教育哲学》的作者约翰·S·布鲁贝克显然“不相信会有一种可以通过共同捍卫其纯洁性而永世可靠的、单一的、不变的、理想的大学教育‘观念’”,他也“不打算为所有的学术机构提出一种共同的哲学”。因为他深知,“正如高等教育的界限埋嵌在历史发展中一样,高等教育哲学的许多方面也是随着历史发展而逐渐显现的。”不同历史时期的大学面临着不同程度、不同层次以及不同类型的社会需求,不同国家、不同社会给高等院校发展的压力与推力也各不相同。所以,引领大学回应这些压力与挑战,满足相关社会需求并取得各自的合法性的观念与举措也各有千秋。先哲和前人在成功解决他们面临的矛盾与困难并成功推进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留下的哲学思考、行动方略与变革举措,无疑是弥足珍贵的,是后辈与来者解决自己的问题、回应当下的挑战时可以借鉴的参照系,但它们“像河一样流淌”,并不能像拼图那样一一镶嵌无缝。
根据托尼·比彻的研究发现,高等教育学与法学、行政管理学等应用社会科学一起,隶属于“应用软科学”,其特质是:“实用性、功利性;注重专业(或半专业)实践;在很大程度上使用个案研究和判断法;研究成果为规约或程序的形成。”我完全认同托尼·比彻的判断,即高等教育学是应用软科学之一;我们必须尊重此类学科的特质,即“实用性”“功利性”和“注重专业实践”,据此调整我们孜孜以求的目标及突破口和着力点。我们高等教育学科建设的方略必须改弦更张,必须放弃探寻、构建一个逻辑严密、范畴特殊、严谨规整、天衣无缝的高等教育学理论体系的目标,而将研究并解决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现实问题作为首要任务。
必须强调,这样提出问题并非贬低或者取消我们对高等教育学科理论的探讨,而是认为,高等教育学科的真正有价值的理论成果绝非在书斋案头冥思苦想、演绎、建构的产物,而是在高等教育实践中成功解决当时、当地突出的矛盾和棘手的难题后的必然结果。就像当年洪堡与费希特、施莱尔马赫等创建柏林大学的实践——旨在为德意志民族的重新崛起提供新的精神力量与智慧人才——其结果是不仅“用现代的方式重建了大学”(阿特巴赫语),而且“使旧瓶装入了新酒,旧瓶也因此破裂。古老的学府如此彻底地按照一种理念进行重塑,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语)这注入的“新酒”——崭新的大学理念——也就成为重塑现代大学的精神财富,成为高等教育学的理论精粹之一。
确定“验证真理”的标准:不同“厅堂”自有不同
对于学科特质及其“验证真理”方法的差异性,美国学者约翰·S·布鲁贝克有过相当精辟的论述:“实际上,在学问的圣殿里有许多厅堂。在有的厅堂里,学者是通过在隔音的实验室里拨控制盘来验证真理的。在另一些厅堂里,他们是通过在喧闹的城市、福利中心、诊所、法院等地方参与工作来积极验证真理的。还有一些厅堂里,一些孤军奋战的思想家是在静寂的图书馆里通过钻研故纸堆来验证他们的思想的。”这其实是在启发人们必须思考并有所抉择:我们是如何“验证真理”的,是在“隔音的实验室里拨控制键盘”?还是在图书馆“钻研故纸堆”?抑或深入现场“参与工作来积极验证真理”?这不仅因软、硬科学而有别,还因知识生产的模式不同而不同。
托尼·比彻等在长达7年的时间中通过两个国家、18个学术机构、跨越12个学科的1220名学者教授的调查访谈,用大量鲜活的资料深化了在“学问圣殿”的不同“厅堂”验证真理的不同特点、方式与结果。如他强调物理学等“纯硬科学”的发展特点是“累积的;原子论的(晶体状的/树形的);与普遍、数量、简化相联系;客观性,价值中立的”。而“纯软科学”如历史学、人类学等的发展却迥然有异,呈现“反复的;有机的(与河流相似);注重细节、质量与复杂性;主观性、受个人价值观的影响”等鲜明特点。“纯硬科学”如物理、化学、数学等等主要“为某种发现或对某种现象进行解释”,其研究成果常常以学术论文的形式呈现,其对真理的验证和知识的陈旧标准,都有明确的原则并容易达成共识,因而具有国际可比性,其学术前沿所在与学术影响力大小,也可以量化甚至排序。而“纯软科学”重在“对某种现象进行理解或鉴赏”,往往见仁见智,研究成果也难以一一证实或证伪,对新知识的确认和原有知识陈旧的确定标准常常“存在争议”,学科发展的标识与研究成果的评价也有所不同。
国务院文件强调,双一流建设必须“坚持以绩效为杠杆”。那么,什么是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的“绩效”?是发表SSCI或者CSSCI论文的数量?是高影响因子学术期刊的发文量?还是世界EIS学科排序前1%?或者,是完成国家级、省部级课题的数量与质量?
我曾经参加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点资助项目“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研究”,主持教育学子课题的研究,两次尝试运用科学计量学的理论与方法,借助《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即CSSCI的统计数据,分析我国教育研究的学术影响力。我发现,运用科学计量学来分析教育研究机构、期刊及学者个人的学术水平和学术影响力,确实有说服力!但同时我也发现,期刊论文或专著“被引”及“被引率”所反映的,仅仅是学者教授的研究所得,即他的思想、观点对“文本”的影响力,而教育研究的真正目的,却在于影响教育实践,包括影响教育决策、影响教育教学和教育管理改革,在于为一线的教师和学生、为各级各类学校管理者提供新视野、新思路和新见解!
什么是真正的影响力?什么是真正富有含金量的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绩效?是对教育宏观决策的影响,是对学校治理方略的影响,是对教师的教与研,对学生的发展与成长的真切而实在的影响!前者如匡亚明、刘丹、李曙森、屈伯川等四位老校长关于建设“重中之重”的“8.35建言”,后者如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如“慕课”的开发与创新……这些,才堪称对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教育变革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才堪称引领一个时代教育发展的里程碑式的成果!
在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建设中,如果仍只注重核心刊物、影响因子的评价,一味倚重SSCI发文量和引文评价,而忽略甚至无视对大学生的学习经历、学习投入、学习质量的研究,忽略甚至无视对课程、教法的研究,对第一线从事教学、教育管理者的研究和影响,那就将只能是一种典型的“异化”,只会催生一批擅长纸上谈兵、热衷自娱自乐的所谓“学者”,根本无助于中国高等教育的创新发展,也难以真正提升高等教育学的学科水平!
转换研究范式:数据罗列不能代替思想的凝练
研究方法的选择,历来是学科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20世纪90年代初讨论高等教育学的发展方略时,曾有不少同仁将能否找到高等教育学自己的、特有的研究方法,作为我们学科趋向成熟的一个依据。现在,越来越多的学者教授认识到,不必刻意追求为我独有的一种研究方法,也许,借助社会科学的多学科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就是高等教育学的方法论?
伯顿·克拉克是最先倡导并尝试“打开多盏聚光灯”,即借用社会科学多学科的研究方法的。他在《高等教育新论——多学科的研究》中文版序言中特别强调:“各门社会科学及其主要专业所展开的广泛观点,为我们了解高等教育提供了基本的工具……每一观点有它独特的优点,也各有其缺点,我们需要了解那些优点和缺点是什么。利用这些优点,我们可以发展一系列的研究方法。意识到这些缺点,我们可以避免每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的‘井蛙之见’和缺乏辨别力。”潘懋元先生组织他的弟子们,在借助多学科的方法研究高等教育方面进行了十分成功的初步的实验。应当承认的是,多学科研究方法的引进,为高等教育学科的深入发展与繁荣注入了新的活力。但是,毋庸讳言的是,我国高等教育学研究领域同样存在“邯郸学步”“东施效颦”式的弊端,近年来,高教研究界盛行的以量化、数据替代严肃的分析思考,就是一例。
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在《现代大学论》一书中讨论了“研究究竟由什么构成”的问题。他强调:“收集信息——即使是精确的信息——不是研究。收集大量的描述性材料——在家政学、社会科学和教育学领域这种做法相当普遍——不是研究。未经分析的和无法分析的资料,不管收集得多么巧妙,都不构成研究。……有没有图表、曲线和百分比,这些也都不是研究……” 弗氏的许多观点曾经一再被中国学人援引,但令人困惑的是,他的教育学研究范式和方法的独到见解,却很少引起国人关注。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科学研究?弗氏说:“科学的本质要求研究者要有一种思想,虽然他坚持这种思想的方式可以十分灵活。如果事实与他的看法相反,他必须随时准备修正或放弃自己的想法。无休无止的计算绝不会产生理论、原理或思想。”所谓“思想”,就是真知灼见,就是对于历史、现状,就是对于高等教育这一复杂系统的准确把握和深刻认识,对于其发展进程中存在的不确定性的相对靠谱的预测。高等教育现状和历史的研究必然涉及诸多信息、资料、数据、案例,真正的科学研究是对这些信息、数据的去伪存真的分析和鞭辟入里的解读,是对这些数据起伏变化原因的追溯和探讨!思想和观点来自这些分析、解读与探讨。我们不能用罗列一大堆数据,绘制一系列曲线图、直方图或者饼图,甚至列出一长串漂亮的“结构方程”公式,来代替我们的批判性思考和独到性阐释。遗憾的是,这样的研究阵势、研究范式却在期刊论文、学位论文及课题结题报告中风行一时、大行其道,似乎没有曲线,没有百分比和方差分析,没有计算公式,就不成其为“科学研究”!其实,如弗氏所云,许多所谓的问卷调查数据分析“最后得出的结论要么是凭调查开始时的常识就显而易见的,要么是最终得不到可靠证据支持的”。
今天我们已经进入了大数据时代,我们的高等教育研究,也需要实证调查、数据分析,来把握趋势、诊断现状、研究问题,来替代想当然、拍脑袋的决策管理模式。但是,这些问卷调查的设计,应当科学、自洽;调查数据的收集,应当全面、客观、可持续。
最后强调一下案例分析法。“孔子何为而作《春秋》哉?”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引述了夫子自道的一段话:“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我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解析孔子这段话,还是很有见地的。与其泛泛而论、“载之空言”,不如抓住具体“行事”,在描述与评析中将所思所得“深切著明”地阐发出来。英国学者托尼·比彻的研究也发现,作为“应用软科学”的高等教育研究,应当采纳的研究方法是:“在很大程度上使用个案研究和判例法;研究成果为规约或程序的形成。” 与法学、经济学科的案例法有所不同,高等教育学科的案例研究除了具体院校的案例之外,还可以将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国家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的成功与失败、高等院校的崛起、转型或衰落、分合……将当时当地当政者的判断、决策、执行,以及研究者的思考、批判、争论和建议等等,汇集成一个个专题研究案例,作为高等教育思想素材,以供后来的研究者与实践者们思考、借鉴和资政。
5年前我曾经建议在高等教育学研究方面做好三项工作:第一,选择、确定研究的真命题。第二,厘定高等教育的基本概念和范畴,逐步凝聚共识,规范高等教育研究群体多采用的“符号概括”,界定相关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并尽可能与国际学术界接轨,避免出现“鸡同鸭讲”的局面。第三,积累、汇集高等教育研究共同体的“范例”,可以分专题遴选优秀的研究成果并加以评述,逐步形成共同体的“话语体系”。时至今日,高教研究界对于“选择、确定研究的真命题”和“厘定基本概念与范畴”正在形成共识,而对于“范例”的选择、汇集与研判,对于高等教育研究思想库、范例库的建设等,尚需继续呼吁,并大胆尝试。
(作者系常州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特聘专家、南京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摘自《中国高教研究》2016年第9期;原题为《把握学科特性 选准研究方法——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必须解决的两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