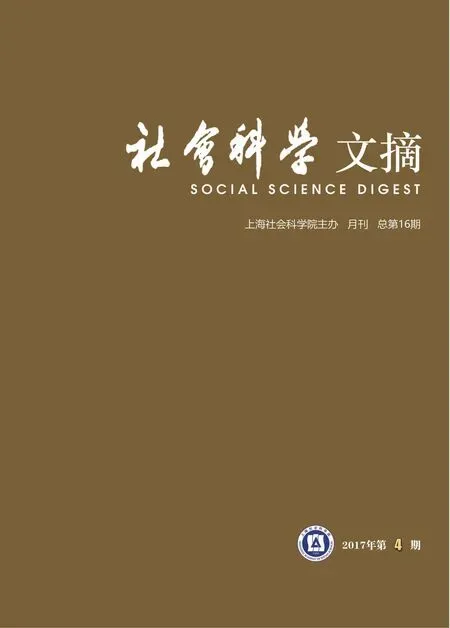对民粹主义的再思考:政治、媒介化和政治风格
2017-11-21本杰明莫菲特西蒙托米宋阳旨
文/本杰明·莫菲特 西蒙·托米 译/宋阳旨
对民粹主义的再思考:政治、媒介化和政治风格
文/本杰明·莫菲特 西蒙·托米 译/宋阳旨
民粹主义似乎是当代政治图景的一个主要特征。然而,在如何恰当地对民粹主义进行概念化这一问题上,几乎仍未达成任何一致。民粹主义的主要定义常常不得其所,未能体现这一现象的特性。在当代文献中,研究民粹主义至少有四种主要的路径,即意识形态、逻辑、话语和策略/组织,每种路径都展现了各自的问题。虽然大部分路径都在某种程度上认同民粹主义在其定义中的特征,但我们认为它们使用了有问题的术语来对这一现象进行分类。下文中,在提出我们自己对于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风格的叙述以及思考它在当代媒介化政治图景中的地位之前,我们将明确这些路径的主要缺陷。
作为意识形态的民粹主义
过去几年间,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概念化已经成为相关文献的主要观点,尤其是在欧洲政治学家中间。这大部分要归功于卡斯·穆德(Cas Mudde)的贡献,他关于民粹主义的作品为该领域的比较学者设定了议题。穆德提出了一个最低限度的民粹主义定义:一种内核空洞的意识形态,认为社会最终将分裂为两个同类的且对抗的群体——“纯粹的人民”和“腐败的精英”,并且政治应当是人民公意的一种表达。对穆德来说,对民粹主义的这种最低限度的意识形态界定,其优点在于它可以用于比较实证研究,尤其是它能够超越地域差异,此外,它还可以抛弃民粹主义概念之前经常宣扬的规范性偏见。他进一步指出,通过将民粹主义概念化为一种内核空洞的意识形态,我们会认识到,民粹主义并非以任何纯粹的形式存在,而是常常呈现在与其他意识形态的混合循环中。
有大量议题把民粹主义归类为一种内核空洞的意识形态。其主要关切在于:民粹主义的相关文献对“意识形态”这一术语的使用相对来说毫无问题,意识形态常常充当一种全方位的术语,它暗中埋没了其他路径——最明显的就是那种话语路径,最终失去了最初显著的透明性。此外,我们需要质疑一种“空洞的意识形态”实际上是否会变得如此“空洞”,以至于失去了其概念的有效性和实用性。与生态主义和女性主义不同,几乎没有人自认为是“民粹主义者”,也没有那种更大范围的全球“民粹主义运动”或民粹国际,同样没有重要的民粹主义哲学家或理论家,抑或任何试图“充实”其“理念丰富性”的文本。此外,除1890年代的人民党(也许是1870年代俄国的“民粹派”)外,民粹主义缺乏一个清晰、共同的历史或谱系参考。因此,考虑到这种路径中意识形态概念的极度“空洞性”,将民粹主义概念化为一种意识形态毫无意义。这并非质疑民粹主义包含重要的理念因素,而是如同下文我们将要论述的那样,最好将这些理念因素概念化为民粹主义的政治风格的一部分。
作为一种政治逻辑的民粹主义
在政治和社会理论领域中,厄内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的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逻辑的概念化影响最大。拉克劳认为,之前界定民粹主义的尝试已然失败,因为它们关注的是确定民粹主义的本体内容,而非捕捉这一概念的本体论地位。拉克劳抛弃了“政治”(politics)具体的实质性内容——实证的政治现实,转向更加抽象层面的“政治”(thepolitical)——构建社会的方式,他提出了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生活的结构性逻辑的案例,很明显,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等同都会战胜差异。
然而,民粹主义不只是普通的政治逻辑,拉克劳认为它是“政治的逻辑”。在这一方程式中,“人民”成为了一切重建的且有效的政治规划的希望,事实上他们是政治的唯一主体。如果“人民”是政治的主体,那么民粹主义就是政治的逻辑。在这一意义上,拉克劳声称所有的政治都是民粹主义的:“如果民粹主义体现为在共同体主义的空间内设想一种激进的替代性抉择,而一种既定社会的未来取决于这种抉择,那么民粹主义不就成了政治的同义词吗?答案只能是肯定的。”
这里存在三个主要问题:概念的滑移、实证的反例和方法论的适用性。第一,虽然拉克劳和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曾经指出,政治领域发生的这种博弈可以命名为霸权,但拉克劳现在又认为:“要理解有关这种政治的本体论建构之事,民粹主义是首选。”这就导致了拉克劳将其不同的主要概念混为一谈。第二,在当代政治图景中存在着诸如萨帕塔斯运动、另类全球化运动以及占领运动等政治运动,它们有意识地寻求疏远民粹主义模式的话语和组织,进而通过拒绝由领导人表达诉求,或者根本不表达任何实质性诉求,来试图否认被拉克劳视为普遍性的“民粹主义逻辑”。第三,从方法论的角度看,拉克劳的概念化过于宽泛,从而使其理论缺乏任何有意义的适用性。
作为话语的民粹主义
本部分将述及研究民粹主义的两条主要路径。第一条路径与拉克劳早期的理论作品以及后来从“埃塞克斯话语分析学派”中涌现的大量文献有关。鉴于埃塞克斯学派的路径大部分与上文中所描述的拉克劳的许多基本假设是重合的,我们不对其进行深入探讨。实际上,拉克劳和墨菲是这一路径的代表人物。这一路径将民粹主义视为“通过象征性地将社会划分为(作为‘弱者’的)‘人民’和‘其他人’来简化政治空间的反现状话语”。与更广义的话语路径一样,这些有关民粹主义的大量文献的关键问题在于它们常常对于阐述或者真正地分析眼前的主题毫无帮助,只是有助于核实和“证明”它们所使用的拉克劳框架的正确性和普适性。
第二条路径涉及经典和定量的内容分析法。柯克·霍金斯(Kirk Hawkins)、简·杰格斯(Jan Jagers)和斯蒂芬·瓦尔格雷夫(Stefaan Walgrave)等人经典的内容分析法典型地致力于发展一种定性的编码方案,试图以某些话语文本衡量民粹主义的“水平”;而最近的阿里尔·阿莫尼(Ariel Armony)和维克多·阿莫尼(Victor Armony)、伊曼纽尔·瑞恩古特(Emmanuelle Reungoat)和特恩·鲍威尔斯(Teun Pauwels)则设法借助计算机来分析大量以某些关键术语的出现为基础的文本。两者都存在很大的问题。正如鲍威尔斯所说,经典的内容分析法的可信度存疑,样本无规律,而且编码可能存有偏见。此外,从演讲到党派声明以及党派广播,在应当衡量哪种来源的问题上基本没有达成共识。另一方面,定量的内容分析法有自身的问题:依据某些关键词出现在党派资料中的频率而绘制百分比图表,很难发现这是否真的比核实或补充业已存在的理论假设更为有效。它肯定无法提供一种可行的理论框架,而且完全依赖编码者选择的关键词。此外,这些作为一种话语的民粹主义实证路径都从根本上忽略了民粹主义诉求的重要因素——即无法记录在册的“风格化”因素。这些因素包括视觉因素、表演因素和美学因素,还有大量关注这一话题的重要的民粹主义研究者们强调的那些有助于民粹主义情感或激情维度的特征。最后,民粹主义的话语路径应当被视为一种可以补充我们对民粹主义的理解的方法论路径,而非探求这一现象的首要框架。
作为策略/组织的民粹主义
科特·威兰德(Kurt Weyland)将民粹主义定义为个人领袖通过其寻求或行使政府权力——这种政府权力以大量几乎无组织的拥护者直接的、未经协调的和非制度化的支持为基础——的政治策略作为实证分析的出发点,这一定义颇受欢迎,尤其是在有关拉美民粹主义的文献中。这个定义的首要困难在于,它以多种不同的表述定义了政治谱系中出现的组织或策略的方式,我们通常绝不会称这些为“民粹”;大量的社会运动(比如宗教运动或千禧年运动)或共同体政治的各种形式都可以被归入这一定义中。其次,没有理由认为民粹主义只有在低水平的制度主义或组织化的情况下才能兴旺起来;让-马里·勒庞(Jean-Marie LePen)的法国国民阵线或威尔德斯的荷兰自由党的命运证明,在一种严格的党纪和组织化环境中,民粹主义的确能够蓬勃发展。最后,作为克里斯玛型领导人领导下的多等级城市联盟的拉美民粹主义,其遗留的经典文献在此留下了一个疑问。这种定义还忽略了民粹主义的风格化和理念化因素,正如霍金斯所指出的,这种“民粹主义的概念化主要强调政治的实质性方面,即联盟、历史前提和政策。这种考虑是不全面的”。此外,该路径遗漏了探讨民粹主义的经典参照物:人民。这样做不仅抛弃了能将民粹主义与其他政治风格区分开来的唯一核心特征,也忽略了这一术语的词根,它主要以拉丁语中的“人民”(populi)为基础。
政治风格
为什么是一种政治“风格”?我们并非首先将民粹主义描述为一种风格的作者。奈特认为,民粹主义是一种“典型地包含与‘人民’公开的友好关系的松散的风格”,一种“他们与我们”的思想,一段危机和动员的时期。皮埃尔-安德烈 ·塔吉耶夫(Pierre-AndréTaguieff)、迈克尔 卡津(Michael Kazin)、玛格丽特·卡诺凡、卡洛斯·德拉托尔(Carlosdela Torre)和达尼·菲尔克(Dani Filc)同样将民粹主义视为一种风格,但却笼统地关注其修辞特征。事实上,杰格斯和瓦尔格雷夫甚至将其界定为“一种涉及人民的政治行为体的政治沟通风格”。然而,这些学者中没有一个人试图充实“政治风格”这一理念,以将其用于比较政治分析。在构建政治风格概念的过程中,我们努力超越这些作者所探讨的纯粹的沟通和修辞因素,强调政治风格的表演因素和关系因素。
为了承认在自反性现代性的条件下政治的形态发生了变化,我们进一步选择关注作为一种政治风格的当代民粹主义。“传统的”或“主流的”政治合法性——其特征是意识形态分歧的衰退、政治等级特征的转换和普通公民疏远传统的党派政治——的崩塌导致了政治的日益“风格化”,“风格”和“表演手法”借助于此而非借助于那些协调我们的政治参与的普通决策者引发了更多的共鸣。就此而论,我们将政治风格的概念定义为“用于构建政治关系的各种表演手法”。在当代政治图景中,存在着许多政治风格,包括民粹主义、技术决定论、威权以及后代议制风格,它们都有自身独特的能够创造并影响政治关系的表演手法和借喻。在我们的案例中,当设计民粹主义政治风格时,我们更感兴趣的是那些参与者的表演如何影响了民粹主义领导人与“人民”之间的关系,反之亦然。这种认识避免了对风格与内容的传统区分,而其他路径本质上都依赖这种区分:我们并非只关注所谓的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抑或只关注民粹主义可能使用的政治逻辑的组织形式,而是关注民粹主义领导人的表演手法及其拥护者是如何相互影响的,以及这又将如何影响他们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试图承认风格和内容在进行这些“精彩的表演”时会崩塌,我们认为这种情况在当代政治中普遍盛行。我们并不认为所有的政治都是纯粹“表面的”,我们也不认为当代政治的“表面性”揭示了一种更加重要的、混乱的“真实”,我们仅仅认可并强调当代政治图景急剧媒介化和“风格化”了,因而所谓的“美学”或“表演”特征就尤其(且日益)重要。所以,政治风格是一种探索当代政治领域的重要概念工具。
作为一种政治风格的民粹主义
我们将概述作为一种政治风格的民粹主义模型。该模型的要素要在一种归纳的基础上进行分辨,我们回顾了1990年代以来有关民粹主义的当代文献,确定了被视为民粹主义领导人的那些毫无争议的案例,他们包括全世界范围的政治家。我们通过分析这些案例来确定是什么风格特征将这些领导人联系在一起创造了我们的模型:这些领导人“为何”是民粹主义者?他们是如何成为“民粹主义者”的?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并且由于我们发现这些领导人在意识形态路径、话语以及政治和组织策略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所以我们重点探讨政治风格。那么什么是民粹主义风格的要素呢?
1.诉诸“人民”
召唤“人民”是区分民粹主义与其他政治风格最主要的因素。“人民”既是民粹主义者的主要受众,也是民粹主义者试图通过其表演“使之出现”的主体。此外,“人民”是领土的真正拥有者。与诉诸“人民”相关的是“人民”与其他人之间的二分法。与穆德在“纯粹的人民”与“腐败的精英”之间做出划分相反,我们并不认为民粹主义者必然视精英为腐败,或者他们总是反对精英。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人民”主要反抗的可能是社会中的其他群体,甚至机构。然而,民粹主义者声称他们有别于精英。无论如何,这种将政治性一分为二的观点源于诉诸“人民”的表演性方面。
在民粹主义话语中,“精英”、“当权派”、“国家”或“体系”(或其他相关指标)经常会被提及,并被视为危机、分裂、腐败或失效的来源,相反,“人民”则“大失所望”、“被欺骗”、“被敲诈”、无能为力或不得善治。民粹主义的这些努力往往是要建立其超越“日常政治”的外在性。它可以采用很多形式,从使用常用俚语到特定姿态、到时尚潮流。它也可以包括反对体系/精英“政治正确性”的声明,这被用于证明民粹主义者“真正了解”人民的所思所想。此外,它还可以采用否定专家学识以及对抗官僚、技术专家、代表或“我们利益的守护者”的方式来捍卫“常识”。
2.. 危机、分裂、威胁
民粹主义从对危机、分裂或威胁的感知中获取了推动力。这反过来导致了对果断而快速的行动的要求。危机常常与公民与其代表的彻底分裂有关,但也可以与移民、经济危机、不公正感、军事威胁、社会变革或其他议题有关。突发事件的这种召唤效应是要彻底简化政治辩论的术语和范围,朝简单、直接的表达方式发展的趋势也体现了这一点。
这与对现代治理的复杂机制和政策解决方案的混乱本质更加普遍的不信任有关,当代环境下的这些机制和解决方案常常要求磋商、评论、报告、冗长而重复的设计和执行。相反,民粹主义者提倡短期而迅速的行动,而非经过谈判磋商和深思熟虑的“缓慢政治”。因而,政治变得高度工具化和功利主义,应当忽略、取代或消除阻碍“议题”或“危机”解决的因素。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民粹主义政治一定是“简单的”或“单一议题的”,民粹主义政治也可以是错综复杂的。
3.“无礼的行为”
求助于作为“常识”仲裁者的“人民”,诉诸“未来的进一步走向”,以及民粹主义者所关注之事的紧迫性,都是为了粗化政治话语。民粹主义者的大部分诉求都源自他们对政治领域“正确的”行为方式的蔑视。卡诺凡称此为“小报风格”,而皮埃·尔·奥斯提盖伊(PierreOstiguy)将之定义为高低轴上较“低”的一极,它与传统的左右轴垂直交叉。较“低”一极的元素包括使用俚语、谩骂、政治失范以及过度的展现和“与众不同”,而非较“高”一极的严格、理性、冷静和使用技术语言的行为。
将民粹主义视为一种带有上述因素的政治风格对于政治分析有诸多影响。第一,它让我们摆脱了民粹主义能够出现在整个政治谱系中这一“谜题”。第二,它使我们可以思考挪用民粹主义“主流观念”所造成的影响。第三,它带来了一个问题,即代表制如何成为关于民粹主义的所有讨论的焦点。通过讨论作为一种政治风格的民粹主义,问题已经不仅是“人民”到底是谁,而且是“让人民出现”这一行为实际上是如何发生的,以及民粹主义是如何对制宪权与宪制权——即“人民”是否是一个塑造民主政治的活跃实体,或者“人民”是如何被外部力量(例如,宪法、历史、领导人等)塑造的——进行区分的。第四,它避免了民粹主义与民主之间关系的概念性滑移。考虑到民粹主义会如何试图穿越当代政治的复杂的“混乱状况”,以及这种政治风格会如何呈现一种对某些民主政治形式的固有批判,将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政治风格来讨论,让我们摆脱了关于民粹主义相较于民主的结构地位的讨论,相反,它让我们能以更为清晰的方式考察这种关系。第五,政治风格的概念有助于我们比较和区分民粹主义及其他政治风格——包括技术统治论、威权主义和后代议制的政治风格——并让我们质疑政治行为体为什么在不同时期会使用不同的政治风格。
随着政治的日益“风格化”以及政治的美学和表演因素的日益重要,作为一种政治风格的民粹主义概念对当代政治图景的轮廓十分敏感。在这种背景下,毫无疑问,民粹主义在过去大约15年间已经将其自身塑造成当代政治图景的一个永久性特征。政治风格的概念通过将民粹主义的表演维度置于前沿和中心,让我们重新思考民粹主义,并让我们有机会反思风格与内容之间的复杂关系。出于上述原因,思考作为一种政治风格的民粹主义将开辟一个探索这一现象的重要的新维度。
【本杰明·莫菲特(Bennjamin Moffitt)、西蒙·托米(Simon Tormey)单位: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社会与政治学院,宋阳旨单位:中央编译局世界发展战略研究部;摘自《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