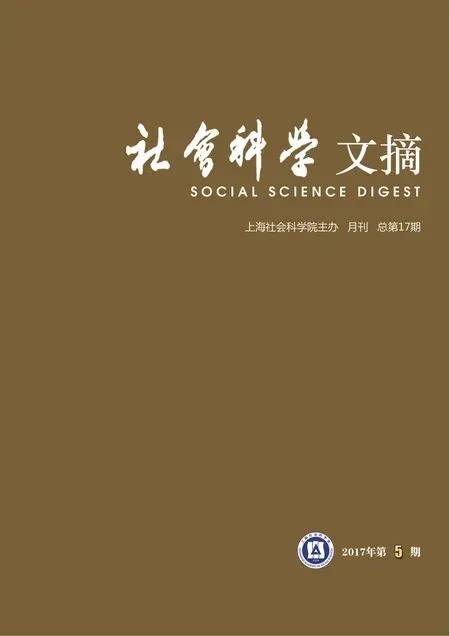从“四夷”到“外国”:正史周边叙事的模式演变
2017-11-21钱云
文/钱云
从“四夷”到“外国”:正史周边叙事的模式演变
文/钱云
不少当代学者,像杨联陞、王赓武、尹达等,都已经观察到,在传统中国有关域外的历史书写中,《宋史》等中出现的“外国(列)传”不单是列传名称的转变,也与惯常认为的“中国的世界秩序”有观念上的差异。然而,考察中国史学的发展历程,是否如晚近学者所称,“外国传”在宋代开始成为历史书写概念的选项之一?事实上,迄今尚未有全面探讨正史中“外国传”出现之历史、背景与意义的研究。但是,这一史学史上的微变映射出近世中国的许多关键问题,因为从“四夷”、“夷狄”转为“外国”的变化过程,不仅是传统中国正史书写体例的转变,也牵涉到由宋至元、明乃至清的域外认识,还关系到不同族群、文化、政治立场对于“中国”的不同观念。因此,本文期望对“外国传”在传统中国历史编纂中的出现、发展及其意涵加以考证,为进一步阐释相关问题做基础性的讨论。
汉唐正史中的“四夷模式”
司马迁在汉代盛期书写的《史记》,超越了前代的历史书写方式,形成笼罩天下、铸造古今的“历史”。同时,随着历史的进程,“新”创造会成为“旧”传统,《史记》的书写方式亦逐渐成为后世史书的“范式”而影响深远,其中,《匈奴列传》、《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和《大宛列传》就创立了古代中国史学记载周边民族与区域(为行文方便,本文将此称为“周边叙事”)的传统。
《史记》的周边叙事对后代正史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叙事策略和模式中。这些叙事结构在后世史书中被不断模仿、再现。但是,有关《史记》周边叙事部分的编次始终存在争论:是否将《匈奴列传》与《南越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诸传编排在一起。通过梳理相关争论就可以知道,中古时代,有关正史的编次方式已经形成了一套广泛接受的模式,即所谓“先诸传而次四夷”。如果将汉唐时期正史中的周边叙事放在一起,很容易看出这种观念的影响:大多正史叙述各族群时,将其大致以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排列在一起,并通常将这些列传放在类传之末。
或有观点认为,这种变化源自经学,又是从《汉书》开始的。伴随着从战国走向大一统的汉朝,基于地理空间而形成的世界观念,经由经学的确认与发展而更趋真理化、标准化,最终成为对庞大帝国想象的方式与结果。后世截然两分的经、史之学,此时共同构建了同一性的帝国想象:经典中的清晰区分为历史纂述的分类、重组提供了概念工具;历史纂述中的基本史实,则为论证、阐释经典中含混模糊的周边叙事提供了具体案例。正史书写常常就在观念与实际之间寻求平衡,一面是“秉笔直书”下的史实记述,一面则是“帝国想象”下的历史书写。“先诸传而次四夷”的史书结构正史对应了“内诸夏而外夷狄”的世界观念。
在“内”与“外”的区分日渐清晰时,“外”也开始了秩序化和标准化的演进历程。“四方夷狄”逐渐被赋予明确的内涵,东南西北与夷蛮戎狄一一对应,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搭配日渐固定,也就成为对于周边世界的一般观念。在正史中,“四夷”也从对“中国”周边的泛指,转变为内涵具体的四方分类。到唐代时,经典所载的清楚、整齐的“世界秩序”就成为新帝国推向现实的国家意志,按照东南西北四个方位来区分各族群与政权的“四夷传”也开始在官修正史中固定下来。
可以说,从《史记》开始创设的周边叙事传统,在几个世纪的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一套清晰而整齐的“四夷”叙事结构,本文将之称为“四夷模式”。史书作为观念与“历史”的载体,从结构、修辞中展现出观念中的“世界秩序”:无论是域内还是境外的蛮夷都被划入“四夷传”的大框架中;无论是否来自同一族属、政治上是否有其渊源,都被整齐地按照方位区别,使得整体上的史书呈现出“内诸夏外夷狄”的格局。当然,真实的历史不可能按照思想与观念的逻辑发展,无论在何时,周边对“中国”总产生着利害不一的影响,不同的族群也在历史中扮演着不同轻重的角色,可供史家记述的史料丰富程度也就不同,因而成为正史书写不断面对的挑战。
汉唐时期的“外国传”
虽然直到宋元之际,“外国传”才逐渐成为纪传体史书的列传名,但是用“外国传”作为记录域外历史、事迹书籍的名称,可以追溯到更早。
在《隋书·经籍志》史部地理类中,著录有萧齐释昙景的《外国传》和刘宋释智猛的《游行外国传》两书,都是西行僧人的行记。与之类似的书还有不少,可见当时西行僧人的行记多以“外国”为题。这类书还有一个比较共同的特点,“皆盛论释氏诡异奇迹”,即在书中表现出佛教的宗教性,实现其宗教意义,宋代的程大昌也有持相同观点。所以,用“外国传”作为行记名,也可以视作是出于宗教的考量。
生活于5世纪的佛教徒使用“外国传”作为西行行记的名称,应当是受佛教世界观的影响。这个世界观中有关空间的概念不同于传统中国的观点,是一个比中国想象世界更为广大的整体世界,世界也不再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同心圆式的结构。相较于深受“华夷之辩”影响的传统中国所使用的夷狄、蕃国等具有道德、秩序、文明高下之分的名词而言,“外国”一词显然更容易为佛教徒接受,也更接近佛教经典中的世界观。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同时期所出现的非佛教徒有关西域的著述多用“诸蕃”为题,如《诸蕃风俗记》、《诸蕃国记》等。
“外国传”,无论是否是佛教徒所作,都代表着一种不同于中国立场的观点,这种观点以更为广阔的世界为立足点来看待世界秩序,其背后所代表的意涵可能并不是简单的“中国以外的国家/区域”,而带有与中国并立的意味,在佛教徒所记录下的《外国传》中,这种意味更为突出。此处“外国传”之意涵,与日后正史中《外国传》亦有相通之处。但是,有关“外国”的表述与世界想象,似乎始终是有关世界秩序讨论中的低音,这种世界观随着佛教的逐渐“中国化”和经学的发展,其本身意欲与传统中国思想分庭抗礼之势也日渐式微,来自远古南亚的世界观念及其延伸出的“外国”概念,始终无从影响政治、儒家思想主导下的官修正史。
元修三史中的“外国传”与“蛮夷传”
元修《辽史》、《金史》、《宋史》三史,全然颠覆了正史中的“四夷传”的命名与叙事传统,意味着以汉族王朝为中心的唯一正统性(“中国”)被打破了,取而代之的是多个政治中心的并立,还意味着以汉族王朝为中心的唯一文明性被消解了,取而代之的是多个文明群体的并立。
事实上,我们并不能轻言元代史官抛弃了正史书写的传统。元代初年即开始了有关宋辽金三朝孰为正统的旷日争论,实际上就是在正史编纂思维逻辑下展开的。但是,即便元代史官深受汉唐以来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却又不得不面对10至13世纪曾经真实发生过的历史。在长达三个世纪的时间里,“中国”始终未出现统一的局面,也未曾出现相对集中的单一政治中心,而是长期处于“复数王朝”的政治格局中。虽然“帝国想象”始终影响着传统中国士人的世界观念,但是,现实政治才是历史书写的真实来源,因此在观念与想象的对弈中,迸发出正史体例的新可能。
元代史官纂修前代历史时,意识到简单地将三史分立并不能够完整地展现之前一个多国、多文明体并立的时代,因此不能沿袭、效仿汉唐正史的体例,将其悉数纳入以方位为区分标准的“四夷传”中。即便是三史中最接近前代“四夷传”结构的《宋史·外国传》,也是先立西夏、高丽、交趾、大理四传,再以南、西、东的次序分类叙述诸国。这样的编排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宋代的宾礼制度相似。
由此可以看出,元代史官不仅改变了前代常用的“四夷传”等具有华夷区分、政治等级的列传类目名,也有意识地开始抛弃前朝“四方蛮夷”的叙事次序,于是正史中所展现的内与外之关系,由以往同质化的“四夷”转变为层级不同的政治团体,这是现实对正史书写的影响,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史官通过正史叙述的转变实现对现实的再度秩序化。
因此,从元代史官分修三史,又依据《辽史》、《金史》的叙事结构分析来看,相对汉唐时期以“中国”为中心,强调由“内”向“外”的政治层级、体现经典中“帝国想象”的叙事结构来说,元修三史更多地通过不同分类来说明10-13世纪复杂的政治格局,以及在此格局中的不同层次的族群关系。于是汉唐以来,“内诸夏外夷狄”的政治理想和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周边印象,也在元修三史的“外国传”中隐退,取而代之的是多重政治群体的角力和“外国”意识的凸显。
“四夷传”,“外国传”?
本节将补充讨论三个问题:其一,在现存二十四史中,《旧五代史》中即以“外国列传”为周边叙事的类传名,是否应以此为正史中出现“外国传”的源头?其二,元修《宋史》是在宋国史基础上修纂而成,如果说元代史官基于10-13世纪历史发展而创设了“外国传”,那么直接面对政治新格局的宋代史官又是如何书写宋朝国史的呢?其三,自汉至宋的正史书写中,是否出现过“外国”?其意涵又是什么?
诚然,只需要翻阅现存二十四史之目录,就不难看出,现存《旧五代史》中就已开始以“外国列传”作为对域外传记的总称。然而,薛居正所修《五代史》早已亡佚,现存的各个版本《旧史》都要追溯至清代乾隆年间邵晋涵的辑佚本。因此,“外国传”的名目为邵晋涵所拟的可能性非常大,“薛史”原本并未以“外国传”为类传名,应该是最接近历史真相的推测,而邵晋涵之所以以“外国传”名之,则应当是出于清代政治的特殊境况,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测说,邵晋涵可能是受了从《宋史》到《明史》的暗示,才采用了“外国传”这一名目。
宋代官方修纂的《两朝国史》、《三朝国史》以及未修成的《五朝国史》中,都没有使用“外国”作为类传名,这说明宋代国史可能从体例上一直沿用了“四夷”、“夷狄”等作为列传类目名,到元代官修《宋史》的时候,这些明显代表华夷观念的列传类目名称终于被“外国”取而代之。
汉唐正史中,不乏言及“外国”,然而其含义模糊,又多与“蕃国”相近,仍带有传统世界秩序中区分华夷的色彩。而在宋代文本中频繁出现的“外国”,则渐有与“中国”相对之意,但是这些文本多由清代四库馆臣经手,不少应是由“夷狄”等字改定而成。与其说代表着宋代中国人的观念,倒不如说更代表清代官方的意志,也恰说明在宋以后的历史时期,对于世界观念与“中外分际”的不断往复、强化与再塑,促成了对“外国”一词及其意涵的接纳。
小结
历史书写是近年来一再引发争论的话题。其中原因无非是史家不得不身处在对过去的“想象”、对未来的期待和可掌握的有限史料之间,对已过去的时代进行描述。因此,历史书写中究竟展现的是真实的历史,还是史家的一己之见,或是代表史家生存时代的政治意志和社会思潮,在史学理论不断翻新的时代,这给后代历史学家重新理解过去提供了新的可能。“外国传”问题亦是如此。
汉唐时期的正史中,从未曾使用过“外国传”作为周边叙事的列传类目名,而常常使用类似“四夷”、“四裔”、“夷狄”等词汇。就像王明珂曾经提到过的,正史作为一种模式化的文类,实际上是受到前代正史书写(“文本规范”)、正史编纂制度与流程(“制度规范”)和各朝代对“帝国”的模仿(“政治社会规范”)综合影响的。因此,透过对正史中一再出现的叙事模式,也同样可以看出正史背后所透露出的历史传统与王朝结构。因为无论是“四夷传”还是“外国传”,既是对某历史时期“中国”周边族群、政权的历史记录,是史家所观察和书写的外部世界,也是我们对“中国”内与外关系观察的管道。
从秦汉开始出现的统一王朝,和与之相应出现的儒家政治秩序观,将传统中国的历史书写扩展到前所未有的范围,开始书写“中国”周边的异民族与异文化,并将周边塑造为以“中国”为核心的文明世界的边缘。此时的核心与边缘区分,虽然表明了政治观念中的统治层级,但无远弗届的政治影响也透露出区分本身的暧昧与模糊。这种观念先行的正史书写,在唐代初年达到高潮,背后恰是官方意志强势介入历史编纂的政治现实。然而政治局势的发展,并不受王朝意志的控制,宋辽、宋金的对峙格局,以及异民族统一王朝元朝的建立,为正史周边叙事结构的改变提供了契机,也因此开始了从“四夷传”向“外国传”的转变。
毫无疑问,“外国传”一词的使用和“蛮夷传”的分立,表示元代史官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区分“中国”(核心)与周边(边缘),标识出两者在疆域、政治结构、文化发展的多重差异。虽然,到了明代,从民族、文化、政治立场出发的明代士人,不少都反对正史的这一改变。但是,流传至今的不少明人重修的宋史中,如柯维骐的《宋史新编》、王惟俭的《宋史记》中都采用“外国传”为列传类目名,似乎也在表明一种关于王朝、国家结构的历史书写模式,正在被汉民族的中国人所接纳。
本文的讨论集中于正史中周边叙事列传的叙事传统与结构,试图通过对书写模式的历史考察分析历史变化中不同时代对于王朝结构的记忆、观念与想象,但这只是文本考察的第一步。史书体例的变化固然代表着史学思想的转变,实际上,还与政治发展、社会思潮密不可分,牵涉到不同政治文化的历代王朝的域外认识,还关系到不同族群、文化、政治立场对于“中国”、“外国”的不同观念,这将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考察。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摘自《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