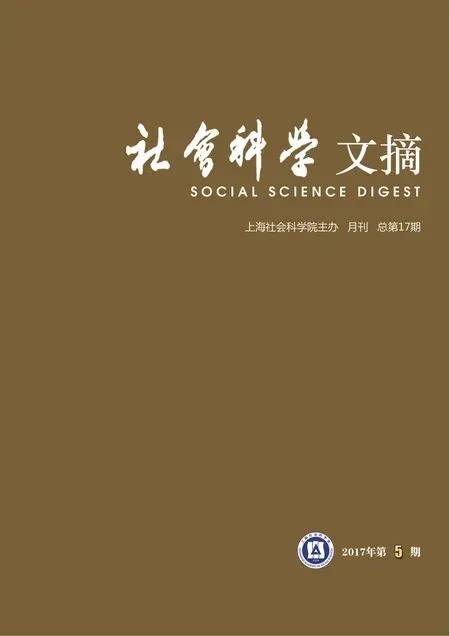法律如何保卫良知?
2017-11-21郭忠
文/郭忠
法律如何保卫良知?
文/郭忠
2016年11月1日,《上海市急救医疗服务条例》正式实施。同年12月19日上午,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召开,《民法总则(草案)》进入三审阶段。这两部法律法规的草拟或出台有望解决过去常出现的救助反被讹的道德困境问题,使好人的救助行为得到法律的保护。
“好人法”顾名思义就是促使人成为好人的法。要促使人成为好人,就需要消除善良行为的心理顾虑和外在压力,让良知得到充分的释放,对此法律大有可为。在“好人法”相继拟定出台之际,我们有必要从更高的理论高度去探讨法律为何能保卫良知以及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保卫良知,以促使法律在更广阔的范围内促进良知。
良知成本与良知的实现
(一)良知的呈现或沉沦:人性的两个方面
人性有着分裂的特征,一方面是道德人,一方面是经济人。人性的两个方面并非毫不相干,各自起自己的作用,而是往往引起人的意识中的激烈交锋。由于利益更显露,良知更潜沉,因此更容易发生的是良知被利欲遮蔽、良知沉沦的现象。这种情况特别容易出现在逐利之心被大大激发,比如市场经济你死我活的竞争环境中。
由于人对利益的追逐,而利益是可计算的,因此产生了计算理性。在逐利之心和计算理性的驱动下,良知也被纳入了成本和收益的考量之中。良知本来是不计成本的,良知行为并非是为了得到自己的收益,但是当良知导致极大的损失的时候,良知就可能被纳入成本的计算中来。比如,当老人倒地,基于良知是要予以救助的,但计算理性又会对良知行为进行成本计算。如果考虑救助行为存在被讹诈的可能性,自己要为良知行为支付巨大代价时,是否要扶起地上的老人,便成为一个艰难的抉择。
在社会生活的竞争中,良知往往并不能让人获得利益的增长,相反增加了获取利益的成本,使人受到损失。在良知行为和利己行为的交互活动中,良知行为在竞争中处于劣势,于是容易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现象。
但毕竟良知作为人性的本真和深层的需求,是不容被驱逐的。正因为良知的真实呈现,我们才认识到这个世界上还存在着罪恶,我们才有可能为自己犯下的罪行而忏悔。从这种意义上讲,良知是人类道德行为的原初动力。此外,一个良知被驱逐的社会,也不可能让人获得真正的安全和幸福,人类文明也缺失了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在良知和利欲的对抗中,一个健全的社会,不是“灭人欲”,而是要考虑如何通过制度减少良知的成本,实现利他和利己的平衡,使良知得以呈现而非沉沦。
(二)社会环境:良知的摇篮
使良知背负上成本的,不仅有利益,还有社会环境。由于人是社会的动物,人们彼此以他人为镜子,形成对自我的判断,而这种判断也在潜移默化地塑造着自己,而使自己成为一个社会化的个体。人们通过模仿他人而形成自己。而一个人一旦成为异类,和大家不一样,则可能承担被社会孤立的后果。因此个体背离群体的成本相当巨大。
良知的生长需要适当的环境。在这个方面,中西思想家有很多重要的论述。良知受外界影响而难以呈现,也被一些心理学实验所证明,比如“米格拉姆实验”和“斯坦福监狱实验”。这些实验展现了残酷的人性现实:通常意义下的好人也极易在某种特定的群体环境下,变得良知麻木和残忍。
人类生存的外部环境对良知的不利影响可分两种。一种是由于受到制度环境可感知的威逼,良知被压迫,如良知面临严酷环境(巨大的成本、被权力压迫以及不公平的制度等)时,良知被放弃,而让人只能释放出人性丑陋和反社会的一面。另一种是人们未有对环境威逼的感知,而是基于社会权威和外部环境的潜在影响,盲目服从了权威,从而放弃了良知的判断。
因此,人的良知状态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社会的烙印。如果社会一旦出现病态也会进一步演化为良知的病态。只有健康的社会才会造就健康的良知,促成个体良知的顺利生长。然而,如同个体会生病一样,社会肌体也极有可能染上疾病。如同人的疾病可能自然痊愈或服药痊愈一样,社会的疾病当然也可通过自发的或人为的手段得以好转。法律就是一剂人为的良药,把握好剂量,服用得当,即可消除社会的疾患。
通过法律减轻良知的成本负担
良知是一种道德上知善恶的直觉。这种直觉——按王阳明的观点——是祛除“良知之蔽”的产物,“良知之蔽”则是指对七情的执着和欲望。
法律减少良知的成本支出,并不能直接实现良知的“去蔽”。良知的“去蔽”和良知的呈现必须是通过主体自身对良知的追求才能实现。但是法律可以减轻良知遭受的内在的和外在的压力,减轻七情之蔽的影响,使良知更容易呈现出来。良知的内在压力在于自我利益的计较,外在压力在于社会环境对良知的逼迫。在计算理性之下,二者都可能构成良知实现的成本。只要法律减少良知行为的成本负担,良知就会减少自身压力,从而更利于人们做出良知的行为。
由于良知是非理性的、活泼的、直觉化的,医治社会的“良知缺失症”,切不可简单地通过道德的法律化,强制人们实施道德行为来实现。实际上强制实施道德,可能使人们的良知背负更大的成本。
虽然从秩序出发考虑,道德也需要法律化,但法律所能强制的道德只是最低限度的道德,而且始终只能涉及行为领域,而无法涉及意识领域。良知的领域并非法律所能强制的领域,相反,它需要呼吸自由的空气才能顺利成长。良知需要实现自由,而良知需要的自由,必须靠法律来保卫。
法律对良知的保卫主要在于为良知减负,以实现良知的自由。法律对良知的保卫要求法律充当良知抵御压力的屏障,使良知免受各种压迫;同时又需要法律不断地释放正义之善,滋润良知生长,营造适应良知生长的环境。
法律保卫良知的方式
(一)法律防范压善行为保卫良知
压善行为出现于纵向型社会关系之中,即出现在权力与服从关系中,它的表现是权力或法律迫使人服从而罔顾良知的存在。
1.法律防范权力对良知的压制
国家权力和服从者的良知之间并不存在天然的和谐关系,相反,在盲目的服从中容易泯灭良知。虽然服从是权力成立的必要条件,但是对权力的服从永远都不应背离个体的道德判断。完全没有良知过滤的服从,可能成为国家权力作恶的参与者。
在纳粹德国时期,一些参与屠杀犹太人的德国官员,并未被发现有任何的邪恶动机,却犯下了滔天的罪行,以至于最终站上了审判台。纳粹军官埃希曼(Adolf Eichmann)被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认为属于这样的典型。在埃希曼身上,阿伦特发现了一种有别于“根本恶”的“平庸之恶”的存在,即缺乏思维和判断能力,盲目服从国家权力。个体对权力的盲从,现代官僚制度要承担责任。因为对大多数平庸之人而言,在制度的逼迫下,良知难以呈现也许是普遍现象。对个体来说,要以良知来抗拒这种官僚化、理性化的制度,实际上有着巨大的成本负担——被排斥、被否定以及其他经济利益的丧失。
在良知面临现代性危机时,法律无法改变现代性的方向,但法律可以提醒人们:对权力的服从并不能免去自己良知的责任,要善于倾听良知的声音,要勇于运用自己的良知。二战后,对“平庸之恶”进行的审判即是一例,它彰显的是法律对良知积极运用的鼓励,对盲目服从权力的拒绝。1999年重庆对綦江虹桥垮塌案进行的审判,也表明盲目服从上级领导,并不能推卸自己良知和法律的责任。法律对“平庸之恶”的审判,提高了放弃良知判断的行为成本,从而使良知的行为成本相对减少,因此对大胆运用自己的良知有激励作用,有利于对社会集体良知的维护。
2.法律防范自身对良知的压制
权力对人的逼迫也可能以暴力的形式体现出来,法律就是最为典型的形式。由于法律制度总是存在着不完善性,这种不完善的进一步发展也可能导致不正义,那么对以良知名义违背法律者,法律又当如何处置?
以良知的名义拒绝服从法律,显然和基于私利的违法有显著不同,但毕竟损害了法律的尊严。善良违法要处理的问题是良知和法律孰轻孰重的问题。前者涉及对人性的尊重,后者涉及对秩序的维持,这样一个两难问题答案决不是非此即彼的。我们要实现的秩序不仅仅是一种秩序,还应当是一种尊重良知的秩序。保护良知不仅要求严厉制裁恶性的违法,以彰显法律的威严,而且要求对善意的违法予以适当的宽宥,以显示法律对良知的敬重。通过对善良违法的适当宽宥,法律不仅释放了它的善意,而且减轻了良知的外在压力,减少了良知的成本。
法律防范自身对良知的压制,还要求不得滥用利益激励,以至于强化了利欲对良知的挤压。一个社会往往有自己所追求的目标,但当这种目标的追求仅仅依靠对人的利益刺激,而忽视人的道德情感时,人也成为了达成目标的手段。在这种法律制度下,良知将会受到压制,甚至被驱逐。
但法律毕竟调整的是利益关系领域,如果不依赖利益激励显然无法调整这类社会关系,那么法律制度就必须考虑利益的激励尽量不要过度地去激发人们的逐利之心,以免形成对良知的挤压。同时良知又并非完全不依赖利益,大多数人的良知行为并非不计成本,因此法律也要致力于减少良知行为的成本支出,使人们的良知行为没有后顾之忧。一句话:法律作为调整利益关系的手段,既不要迫使人们为了利益出卖良知,也不要让人为了良知不得不丧失利益。
(二)法律严惩欺善行为保卫良知
欺善行为即欺负他人的善良,并利用它获取利益的行为。欺善行为发生在平向型关系之中,在这种关系中,没有权力与服从的特征,需要实现公平和平等,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对等对待。
就普通人来讲,如果善良待人,却招致恶的对待,善良将难以存续。比如,当我们好意扶起跌倒的老人,却被讹诈医药费;当我们无私施舍路边的乞丐,却发现他们把乞讨当成致富之路;当我们节衣缩食支援灾区,却发现救灾款物被贪污挪用……此时,我们可能不再扶起老人,不再施舍乞丐,不再支援灾区。
在平向型社会关系中,欺善行为比普通不正义行为更恶劣,因为欺善行为是通过欺负他人的善良而获得的更大的好处,同时也让善良行为者感受到良知行为可能遭到的巨大损失,于是引发善良行为者心中针对欺善行为的义愤。义愤从根本上看源于自我利益丧失或恐惧其丧失,因此,义愤的心理动因和自利的心理动因是基本一致的,无法平息的义愤有可能进一步转化为自利自保行为,乃至利欲冲破良知的束缚,向不义效仿,去获取更大的利益。
欺善行为让良知背负了巨大成本,污染了社会的善良习俗,导致恶的蔓延,给良知的生长带来了恶劣的环境。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欺善行为针对善良行为者实施,更容易被良善者相信,因而具有较小的成本。所以,它可以用最小的成本获得最大的收益。而法律惩罚就必须以更严厉的惩罚,来加大实施者的成本,才能禁止这样的行为。
从中国刑法的规定来看,法律对欺善行为的惩罚更重。比如:《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条“挪用公款罪”中,挪用用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人使用的,比普通挪用公款处罚更重。刑法第二百六十三条“抢劫罪”中,“抢劫军用物资或者抢险、救灾、救济物资的”也有着比普通抢劫罪更重的刑罚。
于是,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的原则:当欺善行为出现时,在有关惩罚性法律规定中,应有更重的处罚。同时,鉴于欺善行为对社会良知的严重危害,法律应重点针对这类行为进行惩罚,而不能任其蔓延。比如,虚假乞讨骗取善心,敲诈讹诈见义勇为者,利用慈善或宗教名义骗取捐款,等等。就目前中国的“好人法”的内容来说,仅仅免去良知行为带来损害的民事责任是不够的,还应当从刑法角度加大对欺善行为惩治力度。
(三)法律通过扬善行为保卫良知
良知生存的外部环境不仅包括良知所处的外部社会关系,也包括良知所处的外部制度环境。而良好的制度环境主要通过法律制度来实现。
法律制度促进良知的生存,不仅靠防范压善、欺善行为来保卫良知,而且还要通过扬善行为来保卫良知。法律所弘扬的善不是偏私之善,而是公平之善,是站在全社会的立场上公平地对待所有人之善。
一个社会的人在社会中得到公平对待时,他就会有一种对社会的归属感,他因自己被尊重、被同等地对待而产生愉悦感。他也因此更容易产生爱与被爱的感受,也更能够同等地、公平地对待他人。反之,当一个人遭受不公平的待遇时,他会感受到自己没有得到社会的尊重,有一种被排斥、被压迫的感觉,最终产生怨恨的负面情感。而不公平带来的怨恨情感容易驱逐爱和善良,更有引发暴力的可能。此外,不公平还进一步助长人性中逐利的倾向,引发计较和贪婪,从而掩盖良知。
从根本上看,社会公平之所以有利于良知,是因为公平减轻了良知的负担,而不公平则容易激发人性中对金钱、地位以及被爱、被尊重的强烈欲求,最终使良知在人心中被挤压。
因此,法律以公平来扬善,首先应当通过公平立法来维护良知。法律应当从社会共同感知的公平出发,制定符合本社会需要的公平之法。其次,法律通过善意适用来保卫良知。法官适用法律时的自由裁量如果不是出于公平之善,而是有偏私的裁量,那么仍然会损害当事人的良知意识。法官对任何一方当事人有意无意的偏向,都会导致对另一方当事人的欺凌,使当事人产生怨恨、被压迫的感受,因此法官的良知直接影响社会的良知。
敬重良知才能保卫良知
在人们的印象中,似乎法律实现正义,道德促进良知,而法律无法对良知产生什么作用。但实际上,法律对利益关系的调整,对正义的实现同样关乎良知。法律能否保护良知,还在于法律是否敬重良知。
失去了良知,我们不仅失去了道德上善与恶的判断能力,不能主动地去追求善,而且失去了和邪恶相抗衡的能力。在人类发展史上,正是因为有了善与恶的判断能力,我们才有了关于法律好坏的价值判断。可以说,人类良知的缺失也将导致法律的正义缺失。正因为如此,法律必须敬重良知,保护良知。
然而,当我们这个社会上,人们对利益的过度追逐、对某个社会目标的急迫期待、对社会公平的极度漠视,都有可能忽视良知,使良知背负过大的成本和负担,使良知遭受损害。一个法治的社会虽然不能造就良知,但法律可以保护良知,减轻个体在良知实现上的各种社会压力。
【作者单位:西南政法大学行政法学院;摘自《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2期;原题为《法律如何保卫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