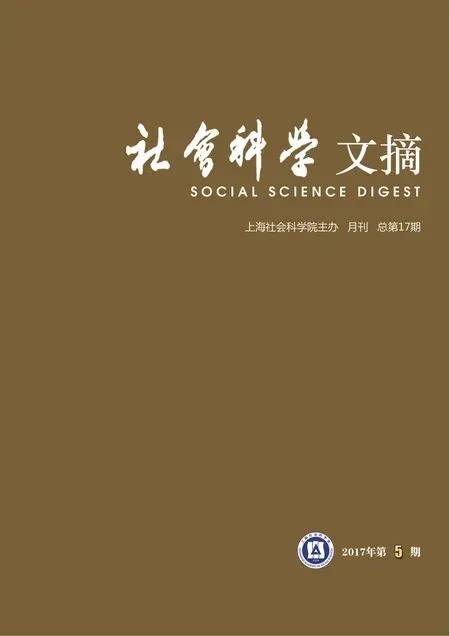作为一个公共管理问题的心灵治理
——兼与刘太刚教授商榷
2017-11-21张乾友
文/张乾友
作为一个公共管理问题的心灵治理
——兼与刘太刚教授商榷
文/张乾友
自人际关系运动以来,“人的因素”成为组织管理中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也成为公共管理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议题。尤其近几十年来,由于片面强调客观激励手段的新公共管理改革造成了公共管理人员公共精神的失落,包括新公共服务理论、公共服务动机理论、服务型政府理论等在内的诸多理论都向公共管理实践提出了心灵治理的问题,要求对公共服务人员的心灵予以重视,甚至基于公共服务人员的心灵特征来改造和重建公共管理体系。《心灵治理:公共管理学的新边疆——基于需求溢出理论和传统中国心灵治理范式的分析》(以下简称《心灵》)中,将这样一种关注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作者刘太刚教授不仅直接提出了“心灵治理”的概念,而且试图通过这一概念来彻底刷新我们对公共管理实践的认识,改写公共管理学科的知识版图。另一方面,该文无论是在对心灵治理是否一个公共管理问题的论证还是在如何治理心灵问题的阐述上都存在可商榷的地方,而对这些问题的争论将有助于我们加深对于公共管理性质的认识。
心灵治理是否一个公共管理问题
在现代观念中,从私人性的失败中寻找公共性的起源是一种常见的认识路径,且这种路径往往具有还原论的特征,总是试图将复杂的社会生活还原为某个单一的社会要素,再通过这一要素来理解私人性与公共性间的关系。比如,政治学习惯于把个体视为利益主体,而作为利益主体,每一个人都需要通过占用社会资源来促进自己的利益,当这种占用与其他人的占用行为产生冲突时,就可能使冲突各方都无法实现自己的利益,于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就需要通过某种方式确定社会的公共利益,并通过政府对公共利益的供给来保障每一个人的私人利益。又如,伦理学倾向于把个体视为责任主体,而作为责任主体,每一个人都对自己的生活负有责任,但当无论何种原因导致某些人没有办法对自己的生活承担责任,其他人则还有余力去承担额外的责任时,如果社会要成为一个道德共同体,前者的生活就成了后者的剩余责任,而这种剩余责任就是公共责任,社会则需要通过政府来更有效地分配和承担这一责任。需要指出的是,伦理学对于责任的探讨往往是与需求尤其基本需求联系在一起的,即每一个人都对自己的需求负责,同时也对其他人的基本需求负责,因而,只有当某些人的基本需求发生了溢出时才会产生公共责任,才需要通过政府来分配和承担这一责任。
比较而言,利益具有行动意味,当我们说某个人在某件事中存在利益时,通常意味着他会采取某些行动来影响这件事的进行,来保护和促进自己的利益。而要这么做,他必须具备基本的行动能力。所以,从利益视角出发,政治学向我们描绘的是一个行动者的世界,这些行动者都有着自己的利益诉求,也都有能力采取行动来维护和实现自己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利益具有排他性,当我们说某个人在某件事中存在利益时,也意味着,要实现自己的利益,他就必须排他性地占用与这件事相关的某种或某些资源,而当某两个人在同一件事中都存在利益时,他们就在对某种或某些资源的占用上产生了冲突。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就必须通过行动来解决冲突。所以,在政治学的视野中,行动者的世界也是一个冲突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公共利益是解决冲突的一种方案。就此而言,利益视角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关于私人性与公共性关系的解释,在这种解释中,衔接私人性与公共性的是冲突,政治就是寻找冲突解决方案的行为与过程,政府的工作则是通过执行方案来实际地解决冲突。
另一方面,需求意味着依赖性,而责任正是产生于依赖关系。在现代观念中,我们认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自主的道德主体,而他具有自主性的标志就是他对自己的需求负有完全责任,并会通过实践中的努力来履行满足自身需求的责任。而且,如果每个人都拥有实践其自主性的完全能力,那每一个人就都是且仅仅是自我依赖的,结果,每一个人就都只需要对自己负责,而不会产生公共责任。但在现实中,这种情况是不可能的,原子化的现代人之所以仍然要结成社会,就是因为我们虽然都是自主的道德主体,但我们自主状态的获得又都依赖于其他人的行为,依赖于其他人对满足我们需求的责任的分担。并且,无论一个人有着多强的自主能力,最终,他都会发现在某些需求的满足上自己仍然依赖于其他人。
然而,我们不可能对其他人的所有需求承担责任,也不能要求其他人满足我们的所有需求,否则就可能纵容人们的依赖性,甚至使他们失去自主的能力。要维护现代个体作为依赖性的自主主体的地位,我们需要为对他人的责任确立某个限度,根据基本需求理论的观点,这个限度就是基本需求,即满足每个人的基本需求——那些无法得到满足就将使个体陷入脆弱状态的需求——是所有人的无条件责任,而政府则是确保这一责任得到履行的一种机制。可见,需求视角关注的是人的脆弱性,而这种脆弱性就构成了私人性与公共性间的转化机制,其转化的结果则是,政府需要通过保障所有人基本需求的满足来将每个人的脆弱性降到一个合理的水平,并不断提高基本需求的标准,直至消除每个人的脆弱性。这是对政府角色的一种伦理解释,其所指向的则是福利国家的实践安排。
在某种意义上,政治学是把公共性理解为一种冲突解决机制,伦理学则是把公共性理解为一种困难互助机制,这两种理解都是与公共管理的学科传统不符的。今天,在批评政治—行政二分误导了人们对于治理过程的认识时,人们往往忽视了这一原则的历史贡献,即它让人们得以摆脱政治学对于治理问题的冲突式理解,而把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治理问题中合作性的方面上来。从公共管理的学科视角来看,社会是一个合作体系,公共管理则是对这一合作体系的维护。由此出发,我们可以提出关于公共性的合作式理解,这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同时,所有人都不拥有实现自身目标的全部手段,于是,所有人就都处在了一种相互依赖之中,都依赖于其他人扮演起作为实现其目标之手段的角色来实现这些目标。由此,目标与手段的不对称分布就构成了社会合作的必要性,而公共性在形式上就表现为社会的合作体系,这种公共性要得到实现,就需要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管理主体通过公共管理活动来维护社会的合作体系。
这种理解之所以是合作式的,一方面是因为它建立在不同社会成员间的分工而不是每个人的脆弱性的基础上,从而确认了每个人作为合作贡献者的地位;另一方面是因为它包含了所有社会成员不断寻求更高目标的进步意涵,而不像在互助式的福利国家中那样,人们只是在通过对已有资源的再分配来解决某些短缺性的问题。在这里,心灵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合作体系的有机运行需要每个人都具有某种服务意识,即主动扮演实现他人之目标的手段的意识,而如果服务意识不彰,就意味着政府需要诉诸一些强制性的手段,动用许多物质资源来确保每个人都在必要的时候扮演作为手段的角色。由此,心灵治理就作为培育服务意识、让人们主动扮演作为实现他人目标之手段的角色进而促进社会合作的一种非物质化的机制,而被证明为了一个公共管理问题。
心灵治理的范围与方式
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心灵问题很重要,这不仅是因为公共组织成员的心灵特征与心灵状态会影响到狭义上的组织绩效,更因为公共组织成员的心灵特征与心灵状态会影响到政府存在的合法性。如果说市场的功能在于促进市场主体的道德自主性的话,政府的功能则在于促进社会作为一个共同体的道德自主性。如果说市场主体的道德自主性表现为他们能够形成自己的需求,并通过市场行为来满足自己的需求的话,社会作为一个共同体的道德自主性则表现为它能够形成各种公共目标,并通过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管理主体的公共管理活动来建立和维护社会的合作体系,进而让社会成员在这一体系中开展合作的行动以实现这些目标。在这里,之所以根据公共目标而不是公共需求来理解社会作为一个共同体的道德自主性,是因为需求这一概念所蕴含的生物性特征过于强烈。从社会层面看,虽然人类社会化的过程本身包含了以“抱团取暖”的方式来满足某些共同需求的阶段,但在各个社会能作为一个个共同体尤其是政治共同体而存在之后,可以认为,所有共同行动尤其政治行动都是以实现目标而非满足需求为导向。从以需求为导向到以目标为导向的转变反映了人走出自然状态的过程,也构成了广义上的政治文明的基本标志。
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管理主体的合法性在于促进各种公共目标,而这将包括几方面的内容。
首先是要帮助形成公共目标。作为社会主体,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而作为多元社会的标志,这些目标往往相互不一。从公共管理的学科视角出发,个体在目标上的差异构成了合作的前提,而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管理主体则需要促进人们形成公共目标,进而在这一目标之下开展合作。在这里,无论我们如何理解到底私人目标之间的何种结合状态才能被视为公共目标,这种结合或转化一定需要某些程序,这些程序将对所有私人目标做出筛选和组合,使最终得出的公共目标能在尽可能大的程度上包容尽可能多的私人目标。对这些程序的供给就是通常所说的制度供给,它是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管理主体最重要的常规职能,其结果则是以制度的形式为所有社会主体提供了一个合作行动的框架。进一步,在通过制度供给帮助社会形成了公共目标和达成这一目标的行动框架的基础上,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管理主体还需要为合作行动找到必要的资源,并有效地运用这些资源来促进社会公共目标的实现。
在这一过程中,公共管理人员的心灵特征与心灵状态是有作用的。这种作用一方面表现在公共目标的形成阶段,即由于程序可能存在缺陷,某些本应被包容进公共目标的私人目标事实上被排除在了公共目标之外,在这种时候,我们往往希望公共管理人员具有额外的关怀意识,虽然他们并不能也不应改变已经形成的公共目标,却可以在被允许的裁量范围内对这些私人目标予以必要的照顾。这种照顾可能是偏狭的,但只要没有超出合理的限度,就不被视为对公共性的背离。公共管理人员心灵特征与心灵状态的作用也表现在合作行动的开展阶段,在这里,公共管理人员是作为公共组织的一员而存在的,其心灵特征与心灵状态对组织行为和组织绩效的影响也是组织理论尤其组织行为学的经典研究议题。但无论如何,似乎并没有哪一种公共管理理论主张对非公共管理人员的社会主体开展心灵治理。其原因在于,社会作为一个共同体的道德自主性依赖于个体的道德自主性,即只有当每个人都能自主地决定其所欲实现的目标时,通过公共管理过程所形成的公共目标才可能的确具有公共性。
如前所述,公共管理的一大职能是通过制度供给来帮助形成公共目标。在这里,根据早期民主理论的解释,个体有决定其私人目标的自由。但根据当代民主理论的解释,个体决定其私人目标的自由并不是绝对的,这种自由也需要受到合法性原则的约束,即个体并无自由决定追求任何私人目标,而只有自由决定追求合法的私人目标,否则,如果任何私人目标都可进入公共管理过程,结果将是公共管理的超荷。在实践中,如果公共管理所面对的所有私人目标都是任意的,如果所有人都仅仅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来确定目标,那么,无论制度供给多么完善,所得出的公共目标都不可能具有充分的包容性,结果,公共管理所欲维护的社会合作体系也将重新变成政治冲突的场域。为了避免这一后果,当代民主理论提出了讲理(reasonable)公民的概念,要求每一个人在确定自己的目标时不仅仅考虑自己的立场,也考虑其他人的立场。只有当一个人是从讲理公民的立场出发确定自己的目标时,他的私人目标才具有进入公共领域的合法性。显然,这是对普通社会成员的一种心灵要求,在这种要求有助于形成公共目标的意义上,它是必要的,在多元社会中人们固执己见的倾向日益增加着公共目标形成困难的现实下,它还是十分紧迫的。而要把这种要求付诸实践,就需要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管理主体承担某种心灵治理的职能,以讲理公民而非仅仅考虑自身立场的理性公民为标准来培育社会成员。
普通社会成员需要得到心灵治理的第二方面理由,源于所有社会成员互为手段的特殊关系。当一个人充当了另一个人实现其目标的手段而后者拒绝作为实现前者目标的手段时,社会中就出现了搭便车的行为,这种行为普遍到一定程度就会导致合作体系的瓦解。为了维护社会的合作体系,以政府为代表的公共管理主体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避免搭便车的现象。但这些措施的成本非常高昂,如果措施不得当,反而可能阻碍社会合作。在这种条件下,公共管理主体也需要采取一些心灵治理的措施来培育社会成员的服务意识,即主动承担作为实现其他人目标之手段的角色的意识。服务意识是社会合作的润滑剂,如果公共管理主体能够有效地培育社会成员的服务意识,将对社会合作起到极大的促进作用。
可见,普通社会成员的心灵也需要得到治理,一方面是为了培育讲理公民从而促进公共目标的形成,另一方面是为了培育服务意识从而促进合作行动的开展。那么,公共管理主体应当如何开展心灵治理呢?
在本文看来,公共管理主体的心灵治理职能主要是一种信息职能。如果说理性公民的问题在于他们仅仅从自己的立场出发考虑问题的话,要培育讲理公民,公共管理主体就需要把所有人的立场都呈现在每一个人面前,并保证每一个人都无法无视其他人的立场。这一点在今天的公共生活中非常重要,因为今天的许多社会冲突与政治冲突都是由于许多社会群体有意无视社会中还存在其他群体,而且这些群体有着与自身不同的立场,只有在这种选择性失明的条件下,人们才能心安理得地做一个理性人。而当公共管理主体将他们试图无视的信息充分地呈现在他们面前时,我们将很难想象他们还能继续心安理得地做一个只考虑自身立场的理性人。
同样,培育服务意识也不是让公共管理主体直接告诉每个社会成员“其他人的目标比你的目标更重要”,而是要求公共管理主体提供充分的信息,使每一个人都充分认识到其他人依赖于自己、自己也同样地依赖于其他人的事实,进而,基于这些信息,每个人就都更可能产生服务的倾向。在本文看来,作为自主的道德主体,每一个人的心灵本身都是不受干预的,但由于每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心灵所做出的判断会影响到其他人的道德自主性和社会作为一个共同体的道德自主性,因而每一个人运用自己心灵的判断过程都需要受到干预。又由于这种判断的基础是信息,因而公共管理主体就可以通过提供充分的信息来帮助每个社会成员做出更符合公共目标的判断。这才是心灵治理作为一种公共管理职能的恰当履行方式。
(作者系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摘自《中国行政管理》2017年第2期;原题为《如何理解作为一个公共管理问题的心灵治理——兼与刘太刚教授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