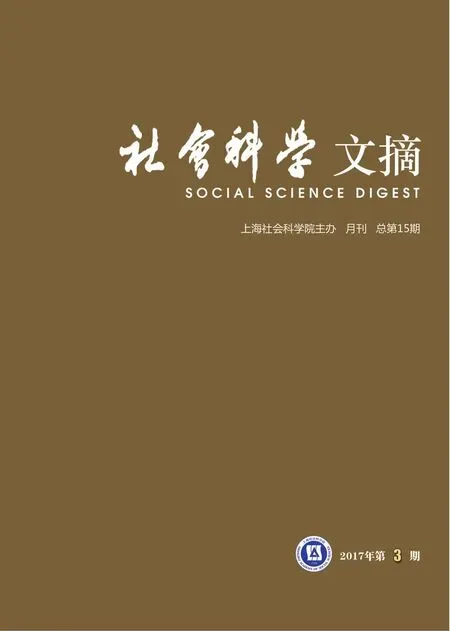现代民主的和平悖论及不平等
2017-11-21刘圣中
文/刘圣中
现代民主的和平悖论及不平等
文/刘圣中
民主观念和民主制度从古典时代的城邦理想转变为现代社会发达国家的标志性政治框架,随着全球化浪潮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人们似乎越来越清晰地发现民主的背后蕴藏着深深的秘密,民主制度之内还夹带着无法逃避的宿命般的悖论。
古典民主与现代民主的分野:政治与市场
古典民主源自古希腊的城邦和广场,城邦内的公民都享有基本的参与审判和投票权,有平等而自豪地参与决断权(亚里士多德),能够自由地表达自己对城邦事务的意见和看法,并投票决定是否选择某位公民担当执政官和其他职位。古代雅典民主的意义在于它能使自由成为可能,“它不只使雅典人在一个相当稳固的基础上成为自己的统治者,而且使他们按照他们个人或共同选择的方式生活,毫不吝惜地保护他们的私人机会免受任何强权的威胁——这些威胁或者来自雅典内部,或者来自别处”。(邓恩)古典民主是一种整体的民主,以统一性、一致性、参与型和非常严格的公民资格为标志。(赫尔德)而进入现代社会,民主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民主不再立足于政治共同体,而是立足于个人。通过代议制选举出来的政治官员从自己所代表的立场出发作出判断和选择,政治决断就在简单多数中妥协和产生。他们所决断的事情以及所代表的人民之间被隔离开来,这种代表制度让民主过程变成一个二次行为。政治已经无法还原为古典时代的政治中介性,而是成为众口难调的、讨价还价的、利益纠葛的政治角力场。它消散了古典政治的整体感。正如贡斯当所言:在一个现代商业社会,要重建一种同样专注的、不知疲倦的、全体公民共同分担城邦中心的政治机构的责任和义务的民主制已不可能,并且,这种徒劳的重建要求必定会侵害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使其为之付出可怕的代价。与古典民主相比,现代民主与市场经济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它是一种为现代市场经济提供保护的民主体制。商业带来自由,也赋予了民主权利。反过来,民主制度则强力保护市场机制,民主的决策也因此遵照市场原则,常常为市场辩护。那么,这种分野将民主带向了何处?其背后有着什么样的秘密法则呢?
现代民主的秘密:资源的占有制度
现代民主与古典民主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立足于个体的民主,它从市场和商品交换中获得力量,乃至价值。现代民主的价值和自由观念来自市场的斗争和切身的体验,成长于市场的第三等级和商人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权益,争夺与贵族阶级相等的政治经济地位,他们起而抗争,从而获得了宝贵的政治自由和民主权利。“新兴的乡绅和资产阶级找到了团结全国的力量参与最高政权,掌握一部分政权直至夺取政权的最好组织形式。”(郭方)在这场现代政治的抗争过程中,正是市场和经济为他们提供了动力和支持,所以市场就成为了民主的基础。而现代民主的秘密也恰恰藏在这里。维护市场是现代民主的天然本性,而维护市场的延伸就是维护资本。现代民主的秘密也恰在此处。
按照索托的研究,资本的秘密即资源的所有权。正是这种对自然物或者说资源的所有权,给资本主义体系提供了联结、合作、竞争与进步的原动力。资源和财产所有权让资本主义世界获得了长足的飞跃式发展,并成为发达世界“自由的基因”之一。(汉南)所以说,对所有权的维护和扩展是资本主义的命根子。洛克在他的《政府论》中也明确地指出著名的洛克式限制条件:“劳动在万物之母的自然所已完成的作业上面加上的东西,这样它们就成为他的私有的权利了。”当然,占有应该以物的恰当使用为限度,然而货币的发明却让人们可以扩增其无限占有的机会。这就是资本占有正当化的理论辩护。同时洛克也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的著名论点:“政府的主要目的就是保护财产”,这一点很清晰地指出了现代民主与资本之间的关系。
民主制度所保护的资本主义从一产生开始就不仅仅局限于一个主权国家之内,而是在全球范围内拼命地争夺和占有各类资源,以实现利润和资本的最大化。纵观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可以说,没有海外殖民地和第三世界的资源与市场,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发展和延续到今天的。从资本主义拓展世界市场的开端到大发展,乃至后资本主义时期,无不如此。当时间推移到21世纪,当今资本主义世界正日益遇到经济危机和债务危机的困境,这恰恰是当代资本主义掠夺式占有资源在全球主权国家遇到层层阻力之后而呈现出来的困境。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海外市场瓜分完毕,海外市场的竞争与利润链条的中断是这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逐渐衰弱的根本原因。这种衰败及其产生的冲突和危机最先在发达国家最薄弱的链条上产生,如南欧的小国希腊、西班牙等。
带给发达国家“紧箍咒”的并不仅仅是发展中国家。另外一个根本性的要素是资本主义危机的真正的诅咒。这就是地球有限资源与环境发出的资源诅咒。有人预计,地球上所有的矿产资源将在未来的30年耗尽,地球上主要的资源如石油将在未来的18年内耗尽。(斯蒂芬·李柏)如果这个预计成为现实,我们无法想象未来的资本主义将走向何处?资本主义的幽灵将在其带给世界瘟疫一般的资源耗尽式的疯癫之后,逐渐烟消云散。
在资本主义世界里,民主与市场是相伴相生的。民主为市场保驾护航,市场为民主提供物质基础。然而市场却有着固有的缺陷,这种缺陷将给民主机制带来挑战和压力。有学者总结了市场的三大缺陷:(1)限制了人们在福利事业进步中明确的推动力的信仰;(2)市场效率与分配公平之间缺乏联系,自由市场价格机制调节的失败及对环境保护的失败;(3)看不见的手无法确保个体在追逐财产、地位优势等个人利益时能同时导致社会福利事业总体的进步。(理查德·布隆克)市场机制不能解决的问题,终究要交给民主制度来落实,然而民主制度在落实这些问题的时候并不能确保一定按照更加符合人类理想的方向来开展,而是极容易被民主的政治竞争性裹挟,带入到无休止的争斗甚至暴力威胁当中。所谓民主和平的自由体制很可能转变为利益占有者和暴力掠夺者的专断体制。
现代民主的和平悖论:内外有别
索托认为,“所有权使资本更加友好”。然而,现实告诉我们,目前的资本主义世界正陷入一种所谓的和平悖论当中,即民主国家之间很少发生(或者说没有)战争与民主国家成为20世纪最主要的战争策源地之间的悖论。
“民主和平论”自康德开始就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假设。其后许多学者也都延续着这一观点,并提供了理论和实证方面的论证。但是,无论这一公理存在多大的可能性,但它却与另一个残酷的现实是相悖的,这一现实反过来也证明民主和平论的有限性。这一现实即二十世纪主要的民主国家是世界上主要局部战争的策源地(特别是美国以及其盟友国家北约成员国)。那这一悖论的形成究竟是什么根源呢?其背后原因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总的来说,这两者并不是一种互不相关的关系,不是偶然产生的,而是有着特殊的互为因果的关系。前者恰恰是后者的结果,没有后者就没有前者。民主国家之间不发生战争虽然从目前来看有一定现实性,但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他们失去了战争的激情和动力。那么,为何他们在没有失去战争动力的情况下却还可以避免国家间爆发战争呢?究其根源在于,这些国家之间暗存着一种自动化解战争的机制。在许多人看来,这是因为民主国家内含的民主决策机制,决策的民主化保证了暴力手段的谨慎控制。当他们遇到同样类型的民主国家时,通过民主程序来反映多数民意的制度,可以有效缓冲各种激进的暴力倾向,因为人民反对战争,人民的反对可以防患战争的发生。(斯蒂芬·平克)然而,同样是民主决策却也是民主国家与非民主国家战争的制造者,正是民主机构中的议员们通过法定的投票机制决定了每一场针对非民主国家的战争。从这一点看来,民主决策机制并非是民主和平的根源,那么其原因究竟何在呢?
实际上,结合民主国家与资本主义不可分割的关系,我们不难发现,市场和资本因素在这里发挥着重大的作用。市场和贸易有一种和平的绥靖功能,也可以称之为市场的绥靖机制。康德就提出一种和平三角理论,其中重要的一角即商业贸易。市场就是这样的一种东西,有了国际市场,有了可以瓜分的蛋糕,战争的可能性就被消减了。20世纪初期,帝国主义瓜分殖民地的时候大多数时间是相安无事的,甚至是结成了同盟。但也有擦枪走火的时候。英法在非洲的战争、日俄在中国的战争、美西在美洲的战争等都是例子,而这正好说明了民主国家之间曾经不是和平的,为了争抢殖民地也发生过真实的战争。
市场的绥靖在一定程度上基本上是有效的,但是其前提是市场有效。在市场有效时,市场发挥的绥靖功能让民主国家划分市场资源和产品中能够理性地保持了一定时期的和平。但是,一旦市场出现无效,民主国家间无法理性地分享各种市场成果,甚至会因为国内环境的倒逼,加大民主国家之间的竞争和恶斗,这时候这种绥靖就会自动瓦解。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消除民主国家深藏起来的战争的原始动因。曾经的盟友片刻之间就会变成敌人。这方面,波兰尼的论述非常深刻而且有力,他的著名论点“自由放任是有计划的,而计划却不是”,意指自由市场并不是完全自由的,而是在民族国家背后的强力推动下逐步发展的。他揭示了现代政治经济过程中的三次大转变,18世纪统一市场的建立,19世纪针对市场的社会保护主义普遍的建立,更重要的转变是20世纪30年代市场经济保护运动所衍生出来的巨大灾变:法西斯主义与苏联式社会主义。自由市场的发展演变成了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包括民主国家体系内部和外部的战争。
根据市场的现代性要求,民主国家遵循着这一铁的规则,努力维持和巩固着世界性的市场秩序,一旦哪里出现不和谐之处就会产生重大的压力,导致采取战争性暴力手段来达到目的。因此,我们所看到的发达国家同盟对付某个小国的不平衡战争经常出现。尽管我们也无法否定战争发动者所主张的国际正义理由对战争的作用,但是我们同样也不能否定作为政治之核心要素的国家利益在其间所发挥的重要功能。正如艾森斯塔德的分析:现代性有一种破坏性力量,是这种破坏性力量带来了世界战争和种族屠杀,这可以从两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后的种族屠杀得到验证。“所有这些事实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与现代性的乐观主义观点相反,现代性的发展与扩张事实上并不是进步的、和平的。”艾森斯塔德所言的现代性,恰恰是资本主义现代性,是一种市场无限扩张、利益无限追逐的现代伦理要素。
现代民主的不平等后果
立于资源无止境占有和消耗的全球资本主义陷入和平悖论而难以自拔,其根源不是某个或者某些民主国家具有好战的秉性,而是现代民主与生俱来的秘密所带来的自我紊乱。它也会带来严重的不平等后果。
(1)现代民主的第一个不平等后果就是国家体系之间的不平等
和平悖论的本质是围绕占有资源的斗争,这种争夺资源与反争夺的斗争必然导致双方的资源大损耗,会更加速资源枯竭的步伐。战争胜利者可以依靠资源剥夺而暂时领先,享有资源的好处,战争失败者则独自品尝其苦果。所谓的自由市场体系难以在战后重建,如果真的建立起来,那也是战胜方的市场体系。诚如布罗代尔所言:“资本主义仍然建立在剥削国际资源、利用国际机遇的基础之上的,换言之,它以世界为存活的范围,至少它是向世界伸展的。它当前的大目标是:重整全球主义的旗鼓。”全球主义是强者的全球化,而不是弱者的全球化。全球化必然带来难以弥合的不平等。日本学者也曾论述道:“全球化资本主义问题的根源在于,现在商品和货币都跨越国境自由翱翔了,而控制他们的主体却仍然是分散存在的国家。”(中谷岩)
(2)第二个不平等的后果是战争动员体系下公民政治和生存权利的剥夺
为了维持在全球体系中的优势地位,民主国家必须保持着强势的军事能力,这样才能实现经济市场全球化和维持和平、优雅、奢侈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在苏联垮台以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体系一下子找不到敌人,但是又不能削减其战争储备力量,于是陷入了所谓的“过剩的帝国主义的无限战争”的状态。这种帝国主义不仅不会削减去军备开支,反而要强化、保持永恒的军事强势地位,将所有可能的敌人都置于其监控之下。这种模式终究会一定程度地剥夺国内公民政治和生存的权利。高度战争动员状态的民主体制是一种不平衡的体制,也是一种相对缺乏弹性的体制。
(3)第三个不平等的后果是民主代议制过程的不平等
现代民主作为一种代议制民主,“作为一种旨在保护资本主义经济的政体形式,将难以避免消逝的命运。代议制民主也没有办法自己提高其对现在所面对的众多领域的——国内的和国际的——实际问题的处理能力”。(邓恩)关键的问题是在代议制民主的过程中容易出现两种结果:代议民主的寡头化替代和技术化肢解。所谓寡头化替代是指代议制过程中掌握经济资源的政客或者资本家能够利用手中的资源来掌控选举和决策过程。民主有时候必须付出沉重的代价,用一个国家公民们的个体生命去换取另一个国家的政治灾难以及延续前者命运的战略资源。而所谓的技术化肢解是指大空间范围的民主只能通过电视技术或者网络技术来推广其平面形象和模式化语言,而选民们也只能在这种有限的单调的虚拟的形象和认知中进行决断。这可以说是一种残缺的选举政治。
后自由主义民主是否可能?
美国学者提出过一种未来的民主模式:后自由主义民主。这种民主用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来替换自由主义民主模式,即:“追逐利润的资本市场为民主地负责的投资和资源配置的计划所取代,工作场所和其他共同体通过代表制和参与制而组织起来,实现经济不平等的弱化。”(塞缪尔·鲍尔斯)他们希望用一种新的计划模式来替换纯自由的放任的逐利的资本市场体系,并且希望通过民主参与的深入来解决工作过程中的控制、经济依赖和不平等问题。舒马赫也提出了一种小的经济模式,认为回归到原生的、中层技术的、当地化的经济状态更有可持续性。
总而言之,政治的回归是未来人类社会必须直面的重要问题,如何寻找更好的,能够超越现代民主的模式,来构建新的共同体和生活道路,是我们需要认真思索的问题。
(作者系江苏师范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摘自《国外理论动态》2016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