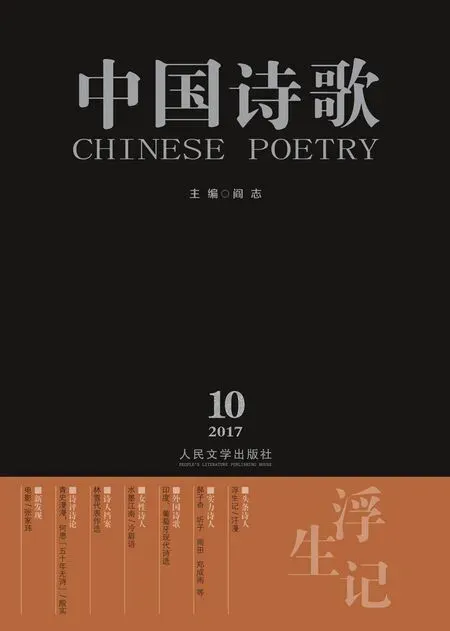时代、生活与自然
——梁上泉新诗导读
2017-11-15袁循
□袁循
时代、生活与自然——梁上泉新诗导读
□袁循
梁上泉,四川达县人,创作历程达六十余年,诗作数量达两千余首,诗集计有《喧腾的高原》(1956年)、《云南的云》(1957年)、《开花的国土》(1957年)、《从北京唱到边疆》(1958年)、《寄在巴山蜀水间》 (1958年)、《红云崖》 (1959年)、《小雪花》 (1961年)、《大巴山月》(1962年)、《山泉集》(1963年)、《长河日夜流》(1964年)、《歌飞大凉山》(1976年)、《春满长征路》(1978年)、《山海抒情》 (1979年)、《火云鸟》(1979年)、《在那遥远的地方》(1980年)、《飞吧!信鸽》(1982年)、《高原,花的海》 (1982年)、《多姿多彩多情》(1986年)、《爱情·人情·风情》 (1989年)等。从历史纵向来看,梁上泉诗歌创作大致分为两个时期,前期即十七年时期,主要特征是歌颂时代,尤以抒写边疆地区的建设与面貌为主,后期即文革后期至八十年代末,主要是寻觅与歌唱生活之美。整体而言,歌颂是梁上泉诗歌主题的基本特征,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到其艺术风格。
一、对生活与自然的歌颂
十七年时期,表现工农兵、服务政治是文艺界创作主导思想。可以说,梁上泉基本上是在此观念中成长与发展起来的(参看梁上泉:《梁上泉(自传)》,《中国现代作家传略2》,徐州师范学院《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编辑组编,1978年,第222-224页)。五十到六十年代,梁上泉以部队创作员的身份写下了大量歌颂新时代的诗歌,诗集《喧腾的高原》、《开花的国土》、《云南的云》、《从北京唱到边疆》、《寄在巴山蜀水间》、《我们追赶太阳》、《大巴山月》等都属此类。因军旅生涯,梁上泉对时代的歌颂主要以表现边疆生活为主。如《高原牧笛》:“在那以往的年代,/笛声冷如寒霜,/吹着古老的调子,/总是那么忧伤;//进军经过这里,/笛声渐渐高昂,/寒霜化成春水,/暖流淌向远方”(《喧腾的高原》,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第5页),以高原牧笛往日的忧伤与今日的悠扬作对比,隐喻解放军对高原的进军与建设,以及高原所发生的变化。《姑娘是藏族卫生员》以对话形式赞美了一位羞涩而热情、善良而勇敢的藏族卫生员,她从北京医生那里学会医疗技术,为藏地穷苦人家看病,还着力表现了藏族阿妈对姑娘的感激之情与浓浓祝福。《月亮里的声音》献给彝族姑娘沙玛乌兹,诗人因观看其业余演出(表现彝族人家摆脱奴隶命运,走向解放)而心潮澎湃,挥笔写就。诗人就演出展开想象:往日的苦难如银霜,娃子的热泪似火光,今日的现实如神话,未来的梦幻似星星,想象丰富而色彩鲜明,在对比中形成较为强烈的艺术效果。《阿妈的吻》写一位藏族阿妈眼睛噙满泪水,一边吻着怀里的孩子,一边脸庞亲贴着医院的玻璃窗。诗歌末尾以真切口吻低语道:“啊!你吻吧!吻吧!/你以吻孩子的母爱,/在吻着自己的医院,/在吻着自己的祖国呀!”(《山泉集》,作家出版社,1963年,第32页)据诗人回忆,藏族地区旧俗认为女性生产是脏污的事情,只能在牲口圈里进行,得了病痛,也只能念经求神。诗歌中的阿妈连续生养八九个孩子,却因缺医少药先后夭亡,一直独自一人生活在一顶又黑又小的帐篷里,过着风烛残年的日子。因其一次生病,诗人与医护人员送去药物,并亲自喂药,才有了诗歌当中这感人的一幕(参看梁上泉:《处女作的诞生——谈谈诗集〈喧腾的高原〉》,《作家谈创作·下》,《作家谈创作》编辑组编,花城出版社,1985年,第847页-849页),诗人见此一幕,诗思自然不择地而出。诗歌主要是表现藏族人民的新生活与藏族地区的新风貌,又以阿妈吻着医院的玻璃窗如同吻着祖国,将诗歌艺术空间扩展为表现整个中国的变化,主题扩展为对时代的礼赞。
文革以后,梁上泉的诗歌观念发生了一些变化,但是走的仍然是表现生活的现实主义的路子,只不过不再是单纯表现边疆生活,更注重从平凡生活中发现美的因素。诗集《多姿多彩多情》的“序诗”咏道:“我与生活做伴,/生活与美做伴,/美与爱作伴,/爱与诗做伴”(《多姿多彩多情》,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1页)。这可以看作诗人诗歌观念的自白,那就是要在诗中表现生活中的美与爱,赞美多情的大地与多姿的山川。“我愿做一颗小小的行星,/沿着长长的轨道飞旋,/虽然只能反射有限的光芒,/却要投入无限的空间。”(《多姿多彩多情》,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2页)表明诗人要以全部的热情投入生活洪流当中,绽放短暂的光芒。因此,对人情、爱情、风情等的礼赞,成为梁上泉这一时期创作的主要追求。诗集《多姿多彩多情》、《爱情·人情·风情》等便是这一追求的产物。《峨嵋酒家》写于石河子,这里有一峨嵋酒家,店不大生意倒十分兴隆,诗歌主要表现酒店的热闹场面,以及这热闹场面给荒漠带来的一片生气,充满生活情趣。“惊退了片片荒原,/挤走了片片黄沙”(《多姿多彩多情》,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7页),大有荒漠中此处一室皆春之感,与白居易《问刘十九》“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类似,天欲雪,自然是心心念念一片苍茫银白,而久久未雪,自然化为一片焦灼,这时忽然有友人奉上新醅绿酒,红泥火炉,真真是令人欣喜之至,那就一任那窗外风雪,畅叙幽情!《峨嵋酒家》表面看来寡淡无味,但是从平凡生活中发现一点欣喜,捕捉一点诗意却是诗人自觉追求,大漠荒凉,旅途困顿,发现一室春色,一身疲乏便随之而去。对于此诗我们不宜做过分阐释,与《问刘十九》相比,此诗缺了一点景中情,情中景之交融。《果林夜曲》写于凉山布托,表现青年男女的幽会。夜间火把燃尽,聚会也已散去,林间重又恢复平静,隐于心间的火焰却燃烧开来,阿妹口弦声声,阿哥月琴叮叮,互递情愫。对此诗人发出由衷的祝福与赞美,“——轻轻,轻轻……/不碰落枝头的夜露,/不惊动草丛的虫鸣,/在自己营造的果园,/倾诉甜蜜的爱情”(《高原,花的海》,四川民族出版社,1982年,第19页),营造出一种极为安恬静谧的氛围,夜露虫鸣,成为甜蜜爱情的衬托,又像是甜蜜爱情的见证。又如《桑椹熟了》写丰收的喜悦,儿童的顽皮,农家的好客;《车上对谈》写同乡人在异乡的相识;《欢乐的古尔邦》写穆斯林男女庆祝古尔邦节的盛大场面;诗集《爱情·人情·风情》第一辑“爱的礼赞”以29首诗歌礼赞爱情的或两心相悦、或浓烈深刻、或坚贞不渝。
作为军旅诗人,梁上泉足迹遍及全国各地,东至渤海苏杭,南至南沙群岛,西至草原戈壁,北至长白天池,时时都有诗作,以“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形容应当说并不为过。总体来说,梁诗歌颂时代与歌唱生活多以抒写自然风物作为载体,这构成其诗歌贯穿始终的特质。这些诗歌因为与时代和历史贴得太过紧密,思想境界与艺术品质并不十分高远。第一,歌咏时代:《三千岁少女》写哈密的一座古墓中沉睡三千年的少女,诗人首先赞其容貌之秀丽与身世之神秘,转而想象当少女醒来,望见当地的军垦农场、戈壁新村与新成立的人民自治州,将会格外高兴自豪;《山城的山》写重庆的山,先写山之苍翠浓郁、雄峻庄严,连绵多姿,转而大声歌唱另一些群山——一座座拔地而起的高层建筑,以自然的山衬托人工之山,赞美城市建设;《西海》赞美西海的开拓与建设者;《三峡回声》写三峡古猿的啼鸣,古人的长吟,号子的雷震与汽笛的歌音,这一切回声经历岁月变迁,而今汇成向未来前进的时代大合唱;《边城小景》写湘黔川三省交界的边城的热闹情景,诗歌集中笔墨写三省乡民饮水同源,几个民族的人们同船共渡的友好与欢快。第二,歌咏历史:《登大雁塔》写登塔的感受,却以“穿过那千多年的雨,/迎着新时代的风”作结;《圆明园》写八国联军焚烧圆明园的滔天罪行;《卢沟桥》写石狮子的怒吼,“一部抗战史,/从这儿开头”;《船行白洋淀》写华北油田的开掘与建设,又联想当年的游击队,歌颂英雄辈出;《我爱长白山》写长白山之壮阔奇丽,原本写景开阔大气,想象丰富,但转而联想到“东北抗联”,抒发追随英雄足迹的豪情;《妃子园》则像是杜牧“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白话翻译。
抒情诗强调对生活的独特感受,但梁上泉这些诗歌中的感受却并不见得十分“独特”“自我”,恰恰相反,这些感受与时代政策话语和历史常识概念有着相当直接的关联,有时甚至是一种直接的简化与图解。就感受的单薄与缺失的角度来说,这些诗歌有些类似于汪国真“要输就输给追求/要嫁就嫁给幸福”那样老生常谈的贺卡式诗歌。
二、“白水诗人”的艺术追求
梁诗在艺术形式上形成了一定的美学追求,吕进称梁上泉为“白水诗人”(参看吕进:《白水诗人梁上泉——序〈梁上泉的抒情诗(1953-2013)〉》,吕进、熊辉主编,《诗学》2014年第6辑,巴蜀书社,2014年,第348-355页),主要表现为:1.强烈的音乐性,2.明白晓畅的语言,3.平实自然的手法。
第一,强烈的音乐性。梁诗大部分具有很强的音乐性,其中有许多被谱成曲子广为传唱,因此他也成为中国当代有名的词作家。这得益于他对中国古典诗词与民间歌曲的有益因素的自觉吸收,对诗歌节奏、押韵、对仗的讲究。如《牧归》:“草原的黄昏,/从旱獭的鼻尖降临了,/草原的夜色,/从旱獭的洞穴展开了。//饱食的牛羊,/驮着夕阳回圈了,/巡场的牧犬,/摇着尾巴归来了。”(《梁上泉近作十首》,犁青主编《文学世界》第9-10期,文学世界社,1990年,第289页)节奏轻缓,将读者自然地带入一种平静安恬的氛围,段落之间与段落内部构成对仗与复沓,重章叠句,前后对应,节奏鲜明,大有《诗经》古风味道。又如《高原牧笛》:“高原的笛声悠扬,/是牧人倾诉衷肠;/高原的笛声响亮,/是牧人心底歌唱——//进军经过这里,/笛声渐渐高昂,/寒霜化成春水,/暖流淌向远方;//公路修过这里,/笛声与喇叭交响,/飞过无边的草原,/惊醒熟睡的群羊”(《喧腾的高原》,中国青年出版社,1956年,第5-6页),首段整体押韵,结构整齐,内部对仗复沓,节奏得以加强;后两段,段落之间形成复沓结构,段落内部则韵律发生变化,整齐划一又错落有致,另外,整诗以“ang”作为韵尾,整体上形成铿锵激昂之感。又如《大巴山月》:“月色白如雪,/月色明如霜,/人在清辉里,/似闻月桂香,/香绕苏区三千里,/曾随战歌远飞荡”(《大巴山月》,重庆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3页),无论是节奏,还是押韵,都有着浓浓古诗味道。
第二,语言明白晓畅。纵观梁上泉两千余首诗歌,除叙事长诗《红云崖》 (1958)以外都是抒情短章,这些抒情诗语言风格几乎一致:明白晓畅。如《峨嵋酒家》:“这个要盘回锅肉,/那个要碗菜豆花,/外乡客不知要啥,/想吃川味怕麻辣,/只好先饮五粮液,/再吃清汤抄手,/加几个叶儿粑”(《多姿多彩多情》,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6-7页),以菜名俗称入诗,以“要”“啥”“怕”等口语入诗,《姑娘是藏族卫生员》、《车上对谈》以日常对话入诗,《阿妈的吻》:“啊!你吻吧!吻吧!/你以吻孩子的母爱,/在吻着自己的医院,/在吻着自己的祖国呀!”是口语似的呼告,《果林夜曲》:“——轻轻,轻轻……/不碰落枝头的夜露,/不惊动草丛的虫鸣,/在自己营造的果园,/倾诉甜蜜的爱情。”是直率的低语,以及前文多提到的《大巴山月》、《果林夜曲》等,口语色彩都十分浓厚,并大量吸收民歌语言,真率自然,犹如对谈。即便是前文所提及的那些借用古诗整齐划一排列形式的诗句,如《大巴山月》:“月色白如雪,/月色明如霜,/人在清辉里,/似闻月桂香,/香绕苏区三千里,/曾随战歌远飞荡”,《高原牧笛》:“高原的笛声悠扬,/是牧人倾诉衷肠;/高原的笛声响亮,/是牧人心底歌唱——//进军经过这里,/笛声渐渐高昂,/寒霜化成春水,/暖流淌向远方;//公路修过这里,/笛声与喇叭交响,/飞过无边的草原,/惊醒熟睡的群羊”,读来也是明白晓畅。
第三,平实自然的抒情手法。从意象的选择与表现的方式来看,诗人的抒情手法相当自然平实。纵观梁上泉所有的抒情诗歌,极少出现奇特,夸张,梦幻,神秘,变形等艺术形象,也极少采用艾略特《荒原》那样的神话象征模式,李白《梦游天姥吟留别》那样的磅礴瑰丽的想象,或陶渊明《饮酒·其四》那样幽深婉转的暗示。梁上泉多采用直观常见,目之所及,耳之所闻的意象,采用比喻、对比、对偶、复沓、对话等传统手法作为抒情的主要手段。如《姑娘是藏族卫生员》、《车上对谈》、《阿妈的吻》采用对话与呼告,《月亮里的声音》、《高原牧笛》、《大巴山月》、《天鹅湖》、《明月出天山》、《酥油草》采用比喻或对比,《牧归》、《高原牧笛》、《果林夜曲》、《大巴山月》采用复沓。
梁上泉的诗歌创作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也留下许多争议。梁诗与时代和生活贴得太过紧密,主要是一种时代和生活的记录,而文学绝不应当如此,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一个作家应适度地与时代和生活保持距离。这当然是认识的进步,但也有不少人每每接触到这类诗人创作,就会连忙摆头,从先入为主的概念和印象给予直接或根本的否定。实际上,对待此类诗人,我们更应当回到他们自身,回到历史语境(包括诗歌的创作环境与接受环境),从而对其做出更为公正、公允的评价。总体而言,梁上泉的诗歌创作有着一定可取之处,一是形成了一定的创作风格,表明其创作的稳定性和自觉追求;二是一部分诗歌有着一定的艺术价值。
其一是那些纯粹描摹自然山水的诗歌。《牧归》便是一例,“草原的黄昏,/从旱獭的鼻尖降临了,/草原的夜色,/从旱獭的洞穴展开了”(《梁上泉近作十首》,犁青主编《文学世界》第9-10期,文学世界社,1990年,第289页)。旱獭是高山草原的代表动物,藏族地区见其踪影,性情极为机警,视觉、听觉都很敏锐,因此最先感觉到草原黄昏的降临的或许应当是它们,最先归巢或许也应当是它们。因此诗人笔下,黄昏的第一颗露水似乎是有意地,悄然落在旱獭的又尖又长的鼻尖上,夜幕也在旱獭的黑暗细窄的洞穴外神秘地渐次展开。黄昏的降临,夜幕的展开本是极自然的事情,在诗人笔下却饶富生趣,达到了与“春江水暖鸭先知”相似的美学效果,足见诗人观察之细腻。紧接着诗人又写道:“饱食的牛羊,/驮着夕阳回圈了,/巡场的牧犬,/摇着尾巴归来了”。诗人先写牛羊享受美餐后满足悠闲的姿态,这当然是近景,夕阳又与羊背自成一线,镜头拉长,又构成远景,牛羊驮着夕阳归巢,镜头又回到近处,构成近景,构成空间结构变化。又加之“驮”与“归”两个绵延性的动词,写羊群的往画面近处的前行与夕阳往画面远处的下落,两相对应,极富动态。此外,高原草场苍茫阔大,满目嫩黄抑或浅绿,羊群则是分布其上的团团洁白,远处又是夕阳的一片鲜红笼罩,这构成画面色彩的交融。同时,这里我们还大可以想象,画面中羊群的喧闹之声与夕阳的静谧无声所构成的对应,这又构成音响的交融。因此,诗歌从空间的变化、色彩的交融、动静的结合,涂抹出一幅极为生动有趣的草原牧归图景,达到了“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的艺术境地。又如《天鹅湖》,“溪河千回百转,/在草原任意流淌,/亦如天鹅的曲颈,/闪着银白的光。”(《多姿多彩多情》,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年,第9页),诗人从大处着笔,以俯视的角度,以天鹅曲项之弯曲柔美与色彩之银白闪光,比喻镶嵌于草原之上的天鹅湖的多姿多彩,将湖之形态与色彩抒写得淋漓尽致。又如《酥油草》写草原之辽阔,牛羊之肥壮;《青衣江》写江水之清冽,山色之青翠,山水一色犹如白练;《缙云山》写山形之雄奇,山境之悠远;《秦川鸣蝉》写秦川之宽广壮阔,蝉鸣之悠长高昂;《我向往长白山》写似宝石的天池,似青剑的白云峰,似长练的瀑布;《北极光》写北极光之辉煌瑰丽;《夜宿南山》写南山之高峻幽怨,“拥宿云而卧,/抱南山而眠”(《爱情·人情·风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第99页),意境开阔;《登鹞鹰岩》写鹞鹰岩之雄奇突兀,“哈!不是云雾在飘,/而是山岩在飞……”(《爱情·人情·风情》,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9年,第100页)想象奇特。
其二是后期一些诗歌,也有少量是对生活的暴露与反思,甚至批判,主要见于诗集《爱情·人情·风情》中第二辑《沉思的湖》中的19首诗歌。如《我的影子》写人情淡薄,惟独影子与“我”痴心相伴,永不背叛;《劫后的竹子》写被砍伐的竹子的无声哭泣与幼稚愤怒;《红枫》写枫叶如火焰热烈燃烧,却在深秋光景中黯然凋零;《驯蛇者》写蛇本应冬眠,驯蛇者却强行令其表演,直到瘫软;《野花》写山乡野花甘于自然,市人却将其引入庭园之中,供人观赏;《沉思的湖》抒写火山湖的蓄势与沉思;《剖析》剖析生活的苦涩;《月台》感慨人生过往匆匆;《知青的回忆》追忆噩梦;《枇杷树下》抚视伤疤。这些诗歌主要以自然之物隐喻诗人对生活的体悟与审视,具有比较高的思想与艺术价值,在梁诗中算得上精品。
梁诗的问题比较明显,具有那个时代许多诗歌的共性问题,主要表现为:一、歌颂有余,暴露不足,缺失自我;二、风格单一,思想简化,张力缺乏。
其一,歌颂有余,暴露不足,缺失自我。整体而言,梁诗以歌颂为主,从早期走遍边疆,歌颂那里的建设,勾连和深化对时代的歌颂,到后期歌唱生活,梁诗从主题到艺术形式一以贯之的就是其创作生涯开端便形成的“颂诗”风格。任何时候,一个作家都不应当同时代和生活保持太过紧密的关系,一个有着独立意识与独立追求的作家,对时代话语总是会发生一些抗拒,以“自我”之眼光,审视一切:生活、自然乃至宇宙。因此,好的诗歌首先应当是“自我”的,放眼历史上任何一位大诗人,中国的陶潜、李白、杜甫、苏东坡,西方的但丁、莎士比亚、华兹华斯、艾略特等莫不如此。又如易卜生早期就写了大量政治与时代主题的诗歌,后期就对此作了深刻的检讨与反思,提出“生活就是——同心中的/魔鬼做殊死斗。/写诗就是——对自己的/灵魂进行审判”,“银本身是如此高贵的矿石,/不像秋日的稻草一样易碎;/数千年来它静卧在土地上,/是那样光彩夺目,永不会销毁!/生的渴望恰像秋日的稻草,/悲哀属于银,银——高贵的矿石!”诗歌就是以对自我灵魂的审判作为基点,以诗意的想象展开,以象征的方式传达,那些真正具有诗人灵魂深度与精神内核的诗歌,才会像银一样不朽,才使他写出了像《在高原》、《泰尔耶·维根》这样杰出的长诗,成为一个真正的诗人(参看邹建军:《三种向度与易卜生的诗学观念——对易卜生诗歌的整体观察与辨证评价》,《外国文学研究》2009年第2期,第36-46页)。梁诗的主要问题,就是从观念到创作都同时代保持着太过密切的联系。十七年时期,时代话语成为梁上泉诗歌主题的基本来源,这主要归咎于:一、见识有限,诗人对古典诗歌有一定接触,但是对现代诗歌,尤其是强调知性的西方诗歌则比较陌生;二、阅历有限,诗人的军旅生活,使得他同十七年时期种种运动保持一定距离,人生轨迹相对平稳(关于一、二两点参看梁上泉:《梁上泉(自传)》,《中国现代作家传略2》,徐州师范学院《中国现代作家传略》编辑组编,1978年,第222-224页;梁上泉:《〈梁上泉诗选〉自序》,《梁上泉诗选》,四川文艺出版社,1993年,第1-4页);三、时代影响,梁上泉早期的那些诗歌恰巧迎合了当时普遍流行的激昂与歌颂的情绪,从接受的角度来说符合主流和民间的需要,梁上泉短短几年之内创作数部诗集也就不足为奇。十七年以后,梁上泉对其诗歌观念虽然有过一些反思,但文革末期依旧写下了歌唱领袖与时代,歌唱革命历史与工农兵,具有浓厚时代色彩的诗集《春满长征路》(1978年)、《山海抒情》 (1979年),令人难以卒读。八十年代梁上泉求新求变,发表了不少歌唱生活的诗,表明诗人的不懈追求与不尽思索。但是今天来看,颂诗的痕迹依然十分明显,与同时代的归来诗与朦胧诗相比,无论是思想境界还是艺术品质,高低立显分明。尽管求新求变,但是同样经历了文革,甚至挨整坐牢,为什么诗人眼中的生活依旧美不胜收?甚至1976年3月创作的《题革委会大楼》中,“革委会大楼”这样标志性的建筑,在诗人眼中也是“根基深厚……钢铁堡垒……金梁玉柱……”(《山海抒情》,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13-14页)更不用说像归来诗人那般,以人生挫折与悲惨经历写高贵生命的死亡与被毁灭的悲剧(《悼念一棵枫树》),以悬崖边的树,写受难者“似乎即将倾跌进深谷里/却又像是要展翅飞翔”(《悬崖边的树》)。飞翔以跌入谷底作为代价,跌入谷底却渴望飞翔的矛盾撕裂的姿态,以“向死而生”的姿态重新展开对社会理想、人生理想与艺术理想的追求。八十年代的梁上泉许多以自然山水关照社会历史的诗歌,同样延续着颂诗的模式,以时代与历史作为基本主题进行简化式、概念化的抒写。总而言之,梁上泉六十余年的创作,无论文革前,还是文革后,几乎并没有跳出那个特定时代的特定语境。
其二,思想简化,风格单一,张力缺乏。尽管梁上泉形成“白水”似的创作风格,但是今天来看,这一风格却对其诗歌创作造成一定的伤害,使得梁诗无论是思想内涵还是艺术形式都缺乏张力,很难让人留下深刻印象。众所周知,大凡在文学史上不朽的诗歌都有着强大的艺术张力,譬如李白的《将进酒》、《行路难》,杜甫的《秋兴八首》、“三吏”“三别”,“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之陶潜诗,现代诗人洛夫之《边界望乡》、《烟囱》,艾略特之《荒原》,里尔克之《豹——在巴黎植物园》,波德莱尔之《恶之花》等,莫不如此。梁诗艺术张力的缺乏主要表现在艺术形式上。应当说所有文体当中,诗歌最为讲究,最为精致,从语言到艺术形象,再到艺术手法,都有着不同于散文、小说、戏剧的独到之处。梁诗当然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但是今天来看,实际上存在着不少问题。一是语言过于平实,尤其是后期的许多诗歌,口语色彩、民歌色彩十分明显。二是想象比较缺乏,诗歌首先是情感的艺术,其次更是将情感加以物化的艺术,这种物化又必须寄托于想象,想象的思接千载与视通古今又将诗歌艺术空间与思想内涵加以扩大,所以,诗歌生命力的高低还在于想象力的高低。梁上泉的许多诗歌当然是想象的产物,但是总体而言,其想象并不十分开阔大气。三是意象比较单一,想象对于诗歌至关重要,想象的展示却是以物象作为载体,也就是所谓意象,但凡杰出的诗人,一定会在意象的选择与安排上煞费苦心,精雕细琢。梁诗对意象自然有所讲究,但是在选择与安排上比较生活化,比较简单,甚至比较随意,意象所蕴含的意蕴与味道也比较单一。所以,从艺术形式上来说,梁诗确实存在张力不足的问题。这种张力不足,实际上根源于诗歌思想内涵的贫乏。虽说想象与意象对于诗歌至关重要,但想象的根还在于情感,情感深厚博大与否直接决定了诗歌的质量,梁诗的想象并不十分开阔大气,意象比较单一的根本原因,是因其许多诗歌思想内涵的单一贫乏、概念化、常识化。梁诗并没有跳出时代的圈子,超越时代的语境,对生活、对人生、对社会、对宇宙,形成自我独立的,深刻的,博大的体悟与认识。
梁上泉六十余年的创作,两千余首诗歌,可以说为中国新诗的发展做出了不懈努力。但是总体而言,诗人的创作从一开始就局限于那个特殊的时代,并贯穿始终,不能不说令人惋惜。新诗走过百年,从萌芽到横遭腰斩,再到当前式微,真正留下的经典会有多少呢?或许并不会太多。梁上泉的诗歌创作,作为建国后新诗发展历程中具有普遍性的个案,或许应当为我们思考什么是诗,什么是真正有价值、能够留下来的诗,提供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