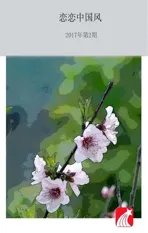渡桥归梦
2017-11-14六州笑
◎六州笑
渡桥归梦
◎六州笑
秋日的渡口,荻花飘零,黄昏里彤云密布,惨淡夕阳斜照着荒废的野渡,大风呼啦啦地裹挟尘埃,席卷苍穹。野渡旁简陋的酒棚下,有人在孤独饮酒。
少年的白袍破破烂烂,落满灰尘,身旁的布袋包裹着长剑,然而长剑沉睡已久,袋子的颜色也已泛灰。
“落魄的少年将军。”忽有人哈哈大笑着从外步入酒棚,一身赤衣,风风火火撩袍在陌满面前席地而坐,“屡去东渭国,次次不中,想必你此次又是无功而返。”
陌满抬头,冷冷望着这热络的路人—亦是一位少年,狭长含笑的眉目,反常地白了少年头,三千银丝如瀑倾泻,衬着红衣格外妖娆艳丽。
“你是谁?我不认识你。”陌满自顾自饮酒。
“可我知道你。”赤衣少年笑嘻嘻靠近,道出了他的窘境,“你是陌满,师出兵家,壮志难酬……”
“是宜纵兵家。”陌满皱眉打断。
“那巧了,我是归衡兵家。”他抢过他的酒壶,将头一仰,苍白的颈子和尖尖下颌勾勒出凌厉的曲线,酒水顺着曲线滑落,滴落在他的衣襟上,他浑然未觉,大叫一声“好酒”。
陌满怔怔望着他,总觉得这场景似曾相识。落魄英雄大约是惜英雄的,于是他放下戒备试问:“却不知你……”
“你会识得我的,他日在战场之上。届时相逢,须得争个高下来。”他仰天大笑振衣出门,步伐看似轻松缓慢,须臾间却消失在茫茫江渡上,再无踪迹。
荻花呼啦啦一下又被吹起,大风天,依稀如旧梦里一抹残阳。
梦里常会出现似曾相识的场景,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旧时的渡口春水未竭,粼粼江面飘散着上游吹落的花瓣。系岸的乌篷船中,孤独的老侠客弄着一管长箫。他武功已臻化境,天下再无对手。他捻须长叹,再叹,一管长箫声音幽冷,响彻天明。
东方渐白时,有一人衣衫渺渺,在渡桥边张开双手呐喊,林涛风声訇然响应,仿佛天与地在回应他的拥抱:“此生约定,来世再践,誓不负你。”
誓不负你……
陌满从梦中惊醒,窗外雨声淅沥,他已在西洛国的客舍中,客舍青青柳色新,又是一年春寒回暖时。去年秋天,他孤坐在东渭国和西洛国的荒废渡口边怅惘了很久,有红衣少年指点他,不如去西洛国一试。
也是,天下乱世,东渭不赏识他,不若去西洛一展拳脚。
陌满便背着长剑去了。西洛的树很顽强,在春雨贵如油的荒漠倔强生长,西洛的人民亦很顽强,在物资贫乏的土地上操戈苦练,誓要与世仇东渭争这天下江山。西洛君主有一双如鹰隼的眼,他知晓西洛的军队需要一位有勇有谋的将领带他们东出峡山、争霸于广袤的中原领地,当风尘仆仆的陌满背负长剑,踏上巍峨长殿时,西洛国君选择了他成为西洛大将。
在东渭接连碰壁的陌满终于在西洛找到了伯乐,得以施展他的才华与抱负。
他操练军队,严格规范战骑与士兵攻防配合的格局;他亦教人耕作,令守兵在军营旁开垦良田,避免空耗国库;他最擅长在战域规划布局,指尖指处,旌旗翻卷战马嘶鸣,西洛的军队如同出鞘的锋刃,骁勇的士兵誓死拼杀,一片片蚕食中原的土地。
终于,三年鏖战结束后,东渭溃败,数十座城池一夜尽失。真是意气风发少年时啊,东渭当初没有重用他,陌满要他们百倍尝受失去他的苦果。他要让他们的君主后悔,东渭没有陌满,是最大的败笔。
说到底还是不甘,他对当初的失败耿耿于怀。
陌满杀到东渭京城时,四方连营号角声起,那日的残阳让他想起了旧年渡口的斜阳,好像从前有个赤衣少年祝福过他。那晚他枕着刀戈入睡,天明时刻他便要攻破这最后的城防,了却这桩最介怀的心事。
梦里,又是那花瓣飘零的渡口,只是那个持箫的老侠客不见了身影,反倒是赤衣白发的少年踏浪而来。那少年立于江面,刹那间水流停滞,波涛凝固,千万花瓣随着他的两袖翻卷,他笑嘻嘻地说:“该是我登场的时候了。”
陌满以为自己在做梦。直到第二日兵临城下,东渭城头红袍翻卷,少年三千白发肆意张扬在风中。他大笑挥袖,东渭军队预先设好的机防到位,包围圈收拢,陌满带着兵马原地打转,避无可避。军队溃散,狼狈而逃,这是西洛败得最惨的一仗,从前的一路胜算势如破竹,到此戛然而止。战局仿佛被一只无形的大手扭转,胜负翻盘,陌满看着敌方笑意盈盈的少年,白发红衣一如当年。他在遥远的城头上向陌满张开双臂,风从肋下穿过,像一只临风的大鸟。他无声地向陌满传达讯息,微笑的唇形陌满读懂了,那少年笑说:“重逢的礼物,你可满意?”
最后,陌满带着折损惨重的残兵撕开缺口突围,狼狈逃回了西洛。
东渭新来的军师,一战天下闻。人们都说,那个风流妖冶的红衣军师,叫度秋。
度秋,陌满念着这个名字,好像有渡口的草香幽幽飘来,花瓣在琉璃般的春水上滑过,旧梦绵绵里,有少年认真而执着地说:“我还欠君一诺。”
陌满头疼了起来。
铩羽而归的陌满回到西洛,自是被君主责罚了。只是西洛君主到底还是要信他,东渭得了度秋军师如同猛虎添翼,西洛若是没有陌满,真不知还能拿什么来和对方抗衡。西洛国君通晓平衡权力之道,军心依然要安抚。君主给陌满加官晋爵,以宽宏的威严向陌满施压。陌满长跪殿前:“谢主隆恩。”
因祸得福,他自己却也不知,能否笑到最后……
陌满重新整饬军队,白日更加刻苦地练兵,夜晚更加痛苦地饮酒。他要回到梦中去质问那红衣白发的少年,为何有这般神通广大的智谋,似乎天生便是他的敌手。可梦里的渡口,白雪覆了苍苔,老侠客的箫声悠悠,度秋立在斑驳的渡桥上,遥望着薄冰覆盖的河流,寒天里不会有归舟。陌满僵在原地喊他,他却呆呆伫立着,仿佛永远也不会回头。
人们都言,东渭军师,智谋非常人,白发妖冶,眉目似狐,谋算近妖。
度秋,度秋,你一定是妖,夜夜入我梦来,未发一言,我已寤寐难安。
陌满在西洛又休养生息了三年,再度东出。
这场争夺战,是中原的一场巅峰对决。两位兵家以天为盖,以地为盘,走卒调遣,以之为棋局。昏天暗地的持久战从夏末杀到冬至,陌满铆足了劲,竟一点点把战线推进,压向中原。收回从前被东渭夺走的失地后,他带军驻扎在高原峡谷上,两军在相对的高地遥遥相抵,列阵厮杀,大片雪花覆盖了原野,鲜血喷溅在雪白的霜草地上。
度秋军师的阵法出神入化,唯有陌满的宜纵兵法能够破解。
陌满一骑绝尘,杀入东渭阵营里,高声大喝着度秋的名字。彼端少年大笑相应,赤衣白发,单骑策马迎来。
刀刃相割,四目相抵,持长刀的度秋眉眼狭长,陌满没来由地恼怒。
“归衡兵家早已失传,度秋,你究竟是谁!”
“你有宜纵,我便能自创归衡。”
“你是兵家,武功也不差,为何却不为将!”
“我无将心。”
刀刃割出了火花。双人双马在阵心游走,陌满让不了半步,度秋游刃有余,却也不愿全力相逼。
“有敌手,果真是快乐的。”度秋忽然说,“陌满,你欢喜吗?”
陌满横剑,没有说话。高岸下的峡谷,白雪皑皑,马蹄踏乱了飞雪。
“你的君主不信你,你是他东征的工具。东渭亦然,我是制衡你的工具。”度秋洒脱而淡然,“现今西洛的半壁河山已经收回,你觉得他会留无用之人吗?”
“休要挑拨离间!”陌满振剑杀去,长剑相抵,谁料陌满之剑刃口折断,脱手而飞。却在此时,漫天箭雨密密麻麻铺排了天地!
“今日飞雪,是你我同死的坟土啊。”度秋浑身是箭,跌下马来,东渭军队阵型大乱。高地上站满了西洛大军,他们早已不再听陌满的指挥,重甲铁骑,弯弓搭箭……陌满不可思议地捂着胸口,看着接二连三的长箭刺穿自己与敌军的身体,鲜血汩汩流出,落在雪地上开出妖娆的花。
陌满和度秋双双倒在飞箭和马蹄下。陌满猩红着眼,执拗地望着铅色的雪天:“君王当真狠心。”
度秋大笑着抹去唇边鲜血:“江山易主,向来如此。罢罢罢,你还记得从前的约定吗?”他挥袖,地上血迹飞升,大片绯红的光华冉冉升起,溯流成记忆的泡沫……
“你会识得我的,在他日战场之上。”他在渡口时说。
“我答应你,作为你的朋友,成为你的敌人。”前世的他说。
陌满脑中訇然有惊雷炸响,前世的记忆如书页,页页翻动,流淌到眼前。
那是梦里的渡口,春江水倒映着碧蓝的天空,老侠客在渡桥边的乌篷船里弄一管长箫,从月升吹到月落,从花开吹到花谢。陌满的前世便是那独步天下的侠客,静居渡口后,再没人能挑战他,也没人来找过他。渡桥静默地望着他,守在清冷箫声覆盖的岁月里,无比孤单。老侠客痼疾在身,纵武功盖世,到底敌不过生老病死。他在秋日的黎明前逝去,离世前他的遗愿是:来世能有一友,成为他的对手。
没有对手的日子,太孤独了。
渡桥与他相伴了悠悠岁月,早已修成人形,他化作赤衣白发的少年模样,踏着清秋的露水行来,替他阖上了双眼:“我答应你。”
雪域战场,两军阵前,陌满失去最后的意识前,看见度秋驾着绯色彤云,脱离了肉身骨骼,飞入雪天。
又是秋日的渡口,今夕却不知何年。日薄西山,荻花在渡口的晚风里飘摇。有少年唱着歌儿行来,抱一山猫,红衣白发肆意飞扬在风里。
“莫不是你怕这一世输给我,所以投胎成了山猫?”度秋低着头笑了笑,轻抚它的脊背,它侧着脑袋瞥他一眼,慵懒地趴在他的臂弯里。度秋又唱起歌来,抱着它,踏着江水走入暮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