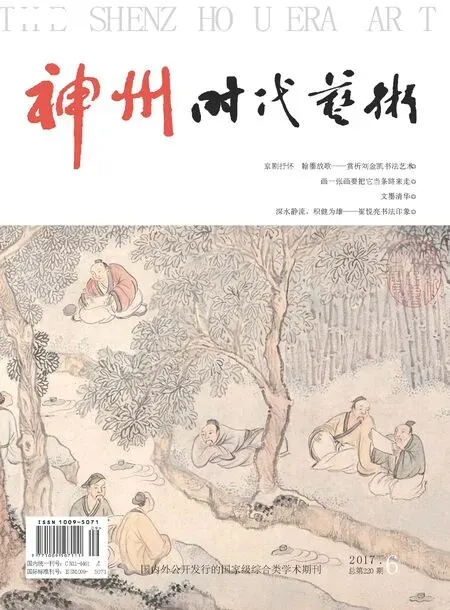困境与突破
——当代碑学发展的价值与意义
2017-11-14李晶
李 晶
当代,多元化带来的艺术领域的变革影响了独具中国气质的书法艺术。从艺术学科的建构来看,属于美术学类的书法艺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受到西方美学思想的影响,书画同论且加入很多新潮思想的各种观点被当代书法家接受,于是流行书风、展厅书法愈演愈烈,追求形式的夸张,追求艺术语言的特立独行,逐渐偏离了书法艺术发展的根本。而在“回归经典”的影响下,“尚文”的帖学书法被更广泛的接受,掀起新一场的热潮,新文人书法、新古典主义、学院派、现代派都在用实践理论奠定帖学在当代的地位,碑学陷入了发展的困境。
一、当代书法的碑帖之争
遗憾的是,当下,碑学在当代仍然缺乏独立、完善的理论体系。更多的学术观点倾向于肯定帖学的正统地位。有学者认为:碑学书法在清代兴盛过后,开创者们并没有把碑学理论体系建构完备,而在如今“全媒体”时代,从者明显流于表面形式,导致碑学泛化,而对帖学的传承、创新则成为一种主流。所以沙孟海先生在碑帖比较的时候也说:比起造诣的成就来,总要请帖学家坐第一把交椅。80、90年代书法表现为强烈的对抗古典的阶段,这一阶段,书画同论、流行书风、意象创新一度甚嚣尘上影响了书法的发展,碑学的创新、突破也受到质疑。很多崇尚帖学的人士其实忽略了碑学所固有的文人传统,将其简单理解为恋碑情结,并认为残缺不全的各种碑文会导致碑学资源的枯竭。
所以,碑学迫切需要建立起自己的理论体系,碑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一方面是碑学自身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当代碑学未来走向的逻辑起点。碑学的理论确认和实践充实,正是为了在当代的艺术构建中寻找自己的园地,不至于沦入“失语”的境地。曹顺庆指出:“‘失语症’的实质并非指现当代艺术理论没有一套话语规则,而是指没有一套自己而非别人的话语规则。何谓话语规则?话语规则是沟通得以实现的基础,是指在一定的文化传统、历史背景、社会语境中约定俗成的语言和意义建构的法则。而如今的失语症,是指我们失去了固有的具有民族性的意义生成和话语言说的话语规则,失去了我们自己的基本理论范畴和运思方式。” 碑学新境的建构与拓展在当代的确立,是一个积极而有效的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有大家、名家的倡导,更有致力于书法艺术的众多书法家的参与和实践。在过程中寻找书法艺术的“大美”之势,试图挣脱书法理论、实践的“失语”境地,强调“技”的同时更强调“人格魅力”,其文化语境包含了中国文化几千年的积淀。所以碑帖的相互碰撞才能产生当代书法的新格局,碑帖融合的趋势才能让当代书法发展更多元化。
二、本土与异质的之争
中国的思想资源为儒释道三家,从政治到生活,从伦理纲常到艺术建构,儒释道都是我们至高无上的经典。这种延续了千年的思想方式,在近百年来却因为西方的入侵而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传统美学思想和文化自信,更是让学界重新审视中华传统美学精神的价值,以中国文论为基础建构的理论体系是对西方中心主义的一种回应,也是重塑中国声音和寻找中西方平等对话的一次努力。在这种背景之下,书法作为中国独有的艺术形式更需要建立自己的艺术学体系。这个体系中,书法甲骨文、汉魏简牍、石刻等都是碑体书法的本源,碑学在源头之处便占尽优势。西方比较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整体植入,确实在中国艺术学研究的现代转型过程中起到了关键作用,但是这种整体植入的结果与中国本土艺术以及中国人的情感经验之间的距离,始终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症结。碑学在当代发展的也逃不过这一困境。
其一,书法从书斋走向展厅,为了追求视觉冲击力,形制被放大,书法的章法结构图形式张扬,笔墨夸张。所以中正、木讷、笨拙的碑体往往不如其他书体表现得张扬,而受到冷落。殊不知,中国传统美学精神中对形象的憨态、木愚是较为推崇的,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老子说:大辨若讷。实际上都是对讷的品格的赞美。中国崇尚的大智若愚,就是希望通过讷的形象来获得睿智。所以,碑学大师邓石如的创作造型憨拙,有木讷之像。其二,受媒体发展的影响。媒体在社会中承担的功能远比我们想象的大,它的肯定与否定,往往代表了主流社会的肯定与否定,甚至影响了大众的艺术判断,放大了它们强加的“流行”与“权威”。媒体的“误读”也让碑派书家看起来没那么“抢眼”。其三,审美的日常生活化。大众文化使人们的日常生活价值追求平面化,个人生活开始失去特殊性。对于一般的书法从业者来说,眼下的精神生活空间没有得到真正的发展,这种缺乏充分发展的个体大多急功近利,不愿意从最根本的临摹、苦读中挖掘、创新书法之美,碑学最具特色的创新、突破精神,没有得到真正的继承。
西方文论的影响还体现在艺术学的学科建设方面。中国是书法的故乡,但是与美术、音乐、戏剧等艺术专业相比,我国高等书法专业教育的起步却很晚。1963年,中国美术学院才开始在国画系增设书法专业,1979年中国美院才开始招收书法方向的硕士研究生,1993年首都师范大学才设立了书法方向的博士点。进入21世纪后,高等学校开办书法专业的数量和规模开始急剧增长,但是由于基础不稳,招生数量的发展过快和书法学科教育的实践不足,亟待需要建立一个完整的书法体系。这其中,碑学的理论构架的梳理自然必不可少。
三、碑学发展的当代价值
清代碑学大潮改变了书法惯有的方向,碑学从对千年帖学的反动与创新中获得发展,这时出现了一大批杰出的碑派书法家,如邓石如、伊秉绶、何绍基、赵之谦等。在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的大力鼓吹下,碑学大兴。碑学如“铁马秋风冀北”,追求阳刚、雄健、气势,点画峻利,疏密自然,拓展了帖学如“杏花春雨江南”,追求阴柔、妍美、意韵的美学意境。康有为称碑学:“六朝人书无露筋者,雍容和厚,礼乐之美,人道之文也。”“笔气深厚,恢恢乎有太平之象。”清代碑学理论对当代书法的学术影响和创作影响是深远的,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清代碑学对当代书法创作的话语方式与精神气质的影响在于亲近自然,回归本源。书法从商周甲骨文、金文至秦篆汉隶,当属于碑派一系。由此看来,碑学当属书法最初的原始状态,但同时也是艺术的不自觉时代。清代碑学的诞生、发展、壮大,完成了艺术自觉的反思,阮元著《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包世臣又以老师邓石如的杰出成就在《艺舟双楫》中大力推崇碑学,稍后康有为在政治变法失败后的极度苦闷中写成《广艺舟双楫》,进一步发展了阮元、包世臣的碑学理论。碑学主张从理性到感性,想象、独创、自由、自然等主观性范畴,让书法艺术又回归到与自然相近的艺术范畴。碑学对书法艺术自觉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碑学以书法发展中进步思潮的姿态,对尊帖这种单一的书法发展之路提出否定,挽救了当时帖学的靡弱书风。从某种意义上讲,碑学转型的核心价值就在于消除了艺术历史积累下来的,已经从根本上制约乃至误导艺术创造思维的方式,最终启示了时代的新精神。碑学作品强调创作时的自由、自然,反对清规戒律,标举“回归自然”的主张。艺术一旦进入原始状态便是无功利的、便是亲近自然的、便是艺术思维的最佳萌动。其二,清代碑学对当代书法创作的影响还在于延续了传统文化与当代创新相融合之道。清代碑学以金石考据为源,重实证、尚古雅,扩展了书法之路。书法强调“从心所欲而不逾矩”的准则,法度固然重要,但当法度日趋完善时,需呈现出无法之法。“心忘于手,手忘于书,心手达情,书不忘想,是谓求之不得,考之即彰”(王僧虔语),正是心手两忘造就了不定法,渲染出“吾观之本,其往无穷;吾观之末,其来无止”(《庄子·则阳》)的气象,达到书法最高气象。其三,碑学的出现和发展,应和了书法艺术法度“变”的思维,是当代书法创新的姿态的本源。清代是中国书法史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书坛渐成“帖学”和“碑学”二水分流的局面,导致了书法流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大分化。在阮元、包世臣提出碑学后,康有为进一步发展、完善了他们的理论主张。康有为提出“变者,天也、书学与治法,势变略同。”在《广艺舟双楫》中,始终贯穿“变”的创新之美,并揭示书法艺术同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一样,都要经历不断的发展进化过程。正是这种对书法的“变法”主张促成清乾嘉以后书法碑派创作的巨大成就。宋代以后,书法艺术进入个性化时代。而清代碑学的出现,更是让个性化的书法艺术进入了自觉化时代,也就是说一切的“突变”和“创新”都是有理可循、有据可依的,不是盲目而无章法地改变。在消费主义时代,艺术走向视觉化冲击不可避免。如何让艺术在传统人文诉求中融入现代艺术的审美追求,如何在原有基础上融入自己的风格、发挥个性。创造出新的富有时代特征的艺术作品也需要谨守“变”的思维。清代碑学给予我们的正是从传统中不断创新的启示。因此在当代将碑学的精神加以继承,将碑学的风格加以完善,是书法学科建设、理论建构的必然。
对碑学在当代的意义和价值的研究,是整个书法理论学科建设的突破点,碑学在书法历史上虽然并不见得有如帖学一样熠熠生辉,但却是不可缺失的。所以,对碑学在当代的建构和拓展,是我们建构书法理论学科的一个个突破点,从个体入手以获得整体发展。中国书法不仅面临着自身的发展困境,还遭遇了西方艺术霸权的冲击。吴冠中曾说:现在是离传统越来越远了。现代中国人与现代的外国人之间有距离,但现代的中国人与古代的中国人的距离更遥远,而且现代的中国人与西方的距离越来越近,这是必然的。书法理论学科的建立,就是要强调人类艺术的非趋同性,我们需要从中寻找中国文化的生命力所在,以此来回应全球化进程中何谓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这样的研究需得从书法发展最本源的碑学入手,从中寻找时代所需要的艺术精神和文化气象,从中发掘中华文化的包容性、生命意识、实证态度、创造特征和风雅精神,而这正与碑学的精神相契合。
四、当代碑学的建构需要继承中华传统美学精神
我们说的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书法的传统包含两方面,一是艺术美,二是精神美。卫恒《四体书势》,索靖的《草书势》,欧阳询的《八诀》《用笔论》等都是对书法形式探究的典范。中国书法美学对形态美学的研究是很系统的。还特别注重“虚实”“浓淡”“雅俗”“巧拙”“奇正”“繁简”等辩证关系的研究,既是对形式技巧的阐释,又是对风格形成的概括。书法创作与中国艺术观念趋同,强调疏处走马、蹈虚蹑影、无色之色、疾涩之道等。对空白的关注,是中国美学空间意识的核心组成部分,并不是书法的专有,但却在书法中获得了最透彻的反应。碑学代表邓石如认为书法的技巧在于“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邓石如把虚实对比的艺术理论阐释得明白如话。其妙处、神处,不在实处,全在虚处。邓石如讲“计白以当黑”则论述了笔不到而意到的艺术本质。艺术者,天地之精英也。艺术自有高山大川、白日皎月的气象。中国美学传统更强调无笔墨处的妙境,与西方透视、结构等庞大体系支撑的视觉艺术有极大差别。老子谈空,空乃大用,空乃根本。书法的笔墨纸之间,实乃具像,空才是万象。
中国美学还强调精神美,是“言志”和“载道”的传统,经世致用是为人生为艺术的标准。从先秦到当代,这一观点也未改变过。苏轼《论书》中认为神、气、骨、血、肉五者缺一,则不为书也。孙过庭《书谱》中认为美的心灵才能造就美的艺术,作为创作主体的书法家应该自我约束,美的心灵表达需要更精密的技巧。《二十四诗品》有《形容》一品,书法要通过笔墨将实用汉字的精气神表现出来,所谓以形显神,书法艺术的绝妙处,如空谷幽兰,似有似无、似淡似浓,神秘而空灵。这与中国古代的学术思想相关。中国传统的学术中,“经世致用”是为人生、为艺术的标准,从先秦以来,就形成了思想内容上的“尚质尚用”和艺术形式上的“尚朴尚简”,儒家文艺思想的诗言志说,诗教说,诗无邪说,辞达而已等,虚拟和写意等;道家说的朴素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等;墨家的非乐等。从诗言志开始,就强调文艺的社会政治功能。所以碑学的建构理应具备“文质兼美”的精神。“文”与“质”是中国古典美学的特殊审美范畴,常指审美对象的“形式”与“内容”。《论语·雍野》云:“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强调文质并举,既以品人,亦以论世,奠定了中国美学史上人品、文品相统一的诗学基础。《论语·八佾》云:“君子以义为质。”“先质而后文”,没有“质”倡导于前,便不能有“文”扬名于后。《庄子·缮性》云:“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质灭,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淮南子·缪称训》云:“锦绣登堂,贵文也;圭璋在前,尚质也。文不胜质,之谓君子。”王充的《论衡·齐世篇》云:“文质之法,古今所共。”魏晋以降,尚文轻质,诗风华靡,颇受后世诟病。历代朝代交替之初,因世混乱,都不免出现重文轻质之风,但发展在后面都被文质兼具的艺术观所替代。中国固有的“观乎人文以化天下”的文化意识,阐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涵和人文气象。所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中,文与质兼美的审美意识始终占据主要地位。
碑学是一个开放的、多元的系统,他的取材对象远比帖学丰富而芜杂。陈振濂先生提出了“新碑学”说法,其具体特征是一不取以人(书家)为权威的模式,而取非权威的方式,关注现象多于关人物。二、不遵循原有的书法优劣价值观,比如用笔笔法,比如经典风格,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多关注新发现新解读的阐释能力与“再生”能力,善于从平凡中发现不平凡,从不关注到重点关注,从一般存在到创新点的确立。反对盲目崇古与片面复古,强调创作与时代审美风尚相和谐的“新碑学”一定能在不断的实践中突破困境,取得全新的发展。
[1] 曹顺庆 付飞亮:《再谈传统文论现代转换之失语症》,载《中国艺术报》2013.3.20。
[2]陈振濂:《“新碑学”-魏碑艺术化运动》,《艺术百家》2009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