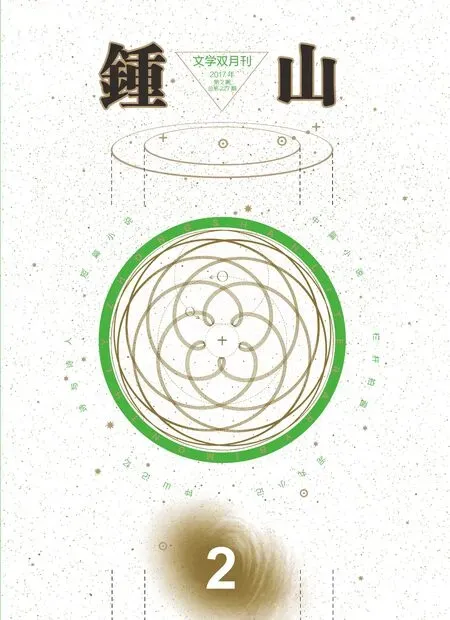胡适面折陈济棠
2017-11-14王彬彬
王彬彬
一 胡适曾经在广州当面批评、指责、教育陈济棠。
胡适是谁,用不着多说。至于陈济棠,在被胡适当面批评、指责、教育时,是广东省实际上的最高领导,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都是核心性人物,在整个西南地区也大有势力,以至于被称作“南天王”。
胡适面折陈济棠发生在1935年初胡适南游期间。
胡适于1935年元旦在上海乘“哈里生总统号”(今译“哈里逊总统号”)轮船赴香港。到香港的主要目的,是去接受香港大学授予的法学博士名誉学位。胡适一生接受过35 个名誉博士学位,这是第一个。胡适于1月4日到达香港,1月8日离开,这期间,除了接受平生第一个名誉博士学位,还发表了五次演讲,三次用的是英文,两次用的是国语。1月8日晚,胡适登上“泰山号”轮船,睡了一觉,翌日晨便到了广州。这趟到广州,是胡适人生中的一次“滑铁卢”。这一点下面再说。
本来预计在广州停留四天,结果只待了两天半。1月11日下午,胡适从广州到了广西梧州。在广西,胡适周游了近两个星期。梧州而南宁(邕宁)而桂林而阳朔,探访了广西诸多名胜,饱餐了广西的山水美景。这次在广西游览,胡适的主要交通工具是飞机,而且是专机。南游回来后,胡适陆续写了四篇“报告”(一、香港;二、广州;三、广西山水;四、广西的印象),以《南游杂忆》为总题,发表于《独立评论》上。据曹伯言、季维龙编著之《胡适年谱》和胡颂平编著之《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南游杂忆》之一的《香港》,写于1935年2月,发表于1935年3月10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141号;《南游杂忆》之二《广州》脱稿于三月初旬,发表于1935年3月17日出版的《独立评论》 第142号;《南游杂忆》之三的《广西山水》(《南游杂忆》结集为单行本时,《广西山水》改为《广西》)写成于1935年4月初,发表于4月7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145 号;《南游杂忆》之四的《广西的印象》完稿于1935年8月12日,发表于1935年8月18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164 号。
在《南游杂忆·广西山水》中,胡适写道:“我们1月11日下午飞到梧州”;“12日讲演完后,吃了饭就上飞机飞南宁了”;“我在邕宁住了六天,中间和罗努生到武鸣游了一天。钧任飞去龙州玩了一天……19日飞往柳州……20日上午飞往桂林”;“24日早晨从桂林起飞,本想直飞梧州,在梧州吃午饭,毅夫夫妇约了在广州北面的从化温泉吃晚饭。但那天雾太低了,我们飞过了良丰,还没到阳朔,看前面云雾低压,漓水的河身不宽而两傍山高,所以飞机师赵先生决定折回向西,飞到柳州吃午饭,饭后顺着柳江浔江飞往梧州,在梧州吃夜饭……在梧州住了一夜,25日从梧州飞回广州,赶上火车,晚上赶到香港。”26日,胡适登上“胡佛号”轮船北返。
胡适从北平出发之初,是并没有广西之游的打算的,本来计划广州活动结束即返回。1月8日,在香港的胡适接到了广西军政巨头白崇禧、黄旭初联名发来的急电:“急,广州转胡适之博士鉴:久慕鸿名,未亲雅范,关山迢递,仰跂为劳。顷闻文远游,已抵羊石,粤桂相距非遥,尚希不吝赐教,惠然来游,俾得畅聆伟论,指示周行。专电欢迎,佇候赐复。白崇禧、黄旭初叩。”白崇禧时任广西民团总司令,是仅次于李宗仁的广西第二号人物。李宗仁其时大多数时候住在广州,代表广西方面与广东交涉各种事宜,广西军政事务委诸白崇禧,所以,白崇禧实际上是广西的最高领导人。黄旭初其时则是广西省政府主席。白、黄二人急电胡适,意思是:我们对您仰慕已久,一直没有机会零距离接触您;广西与北京隔得太远,我们踮足引颈仰望您,仰望得都累了;现在闻知您南游到了香港广州,桂粤离得不远,切盼顺便到广西一游,让我们聆听您的宏论和对我们工作的指示。这样的电报自然让胡适感动,加之在广州受到广东军政当局的冷遇、拒斥,胡适便接受了广西方面的邀请。但一开始也没有打算在广西逗留那么多天,是白崇禧等人的盛情而“强行”的挽留,胡适才改签了船票,在广西飞来飞去地飞了十多天。
值得说说的是胡适在广西专机旅游一事。飞机是西南航空公司派出的。胡适也当然无需掏一分钱。以公帑乘专机而游广西山水,自然是惬意的。胡适在桂林——阳朔上空曾以《飞行小赞》为题赋诗一首:
看尽柳州山,
看遍桂林山水,
天上不须半日,
地上五千里。
古人辛苦学神仙,
要守百千戒。
看我不修不炼,
也凌云无碍。
胡适的《南游杂忆·广西山水》最后抄录了这首诗。胡明在《胡适传论》中说,胡适的广西游记发表后,引起胡适的老友兼大同乡陶行知的义愤,“也出自杜威门下的陶行知,当时已经受了左倾革命思想的影响,脑子里装满了工人阶级的阶级觉悟。他夹带讥讽地和了胡适一首打油诗。”诗曰:“流尽工人汗,/流尽工人血。/天上不须半日,/地上千万滴。/辛苦造飞机,/不能上天嬉。/让你看山看水,/这事大稀奇。”陶行知的逻辑是:美国工人流血流汗造出飞机,自己不能乘坐着到天上嬉戏,却让你胡适乘坐着看山看水,这事儿太稀奇。陶行知的诗在上海某报发表,标题是《两个安徽佬》,编辑大概当作趣闻发表的。胡明说,胡适晚年忆及此事,还笑说陶行知“这个人一点幽默感也没有”。
人们大抵以为胡适是在此番南游时第一次坐飞机,但严格说来并不是。胡颂平在《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1930年谱文的最后说,胡适晚年曾对其“偶然谈起”曾于1930年在上海首次坐飞机。这一年,中国航空公司成立,邀请几位名人在上海上空游览一周。那天请了三个人:一个是王人文,是前清的探花,曾经当过四川总督,80 岁了;一个是岑春煊,更是大名人,也80 来岁了;第三个便是胡适。胡适到了机场,看见飞机很小,只有三个座位,“心里有点怕”。后来看见岑春煊上去了,王人文也被人抬上去了,胡适也就在两位老人后面上去了。飞机在淞沪上空盘旋一周便降落了。事后有人对胡适说:“你错了!他们两位是到了年纪的人,已无所谓。你还年轻,犯不上冒险。”航空公司新成立,飞机在中国还是令几乎所有人陌生的交通工具,对飞机的恐惧是难免都会有的。中国航空公司请几位名人乘坐,自然是一种广告行为,是借此减轻、免除社会对飞机的畏惧。胡适时年四十,是另两个人的一半,也鼓起勇气登上飞机,无非是为支持中国的航空事业。胡适在精神和物质两方面都肯定、赞美现代文明。飞机是现代物质文明的杰出代表。胡适既然一直讴歌现代物质文明,自己也就觉得有义务以实际行动支持飞机这新生事物,虽然颇有些冒险,但却是必须的。在广西的专机旅游,也应作如是观。西南航空公司派专机供胡适使用,不宜视作纯粹是对胡适的礼遇,也有借胡适做宣传的目的。胡适是大名人,胡适在广西的飞来飞去,都被新闻记者盯着。胡适能如此坦然、欣然地使用飞机这交通工具,其他人还有什么必要疑虑、担忧呢? 所以,胡适1930年在上海的勇上飞机,1935年在广西的飞来飞去,都可视作是对中国航空事业的贡献。
扯得太高远了,现在回到地面。胡适此番南游,到了香港、广州、广西三地。在香港,特别值得一说的,是接受了平生35 个名誉博士学位中的第一个;在广西,特别值得一说的,是乘专机游山玩水。而在广州,特别值得一说的,是与以陈济棠为代表的广东军政当局和文化复古势力的冲突。
这事有点复杂,还得从前几年说起。
二 中华书局2011年7月出版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组织撰写的《中华民国史》,煌煌数十册,以李新为总编。这部《中华民国史》第八卷分上下两册,叙述的是1932 至1937年的历史。上册第四章第三节的标题是《对革命文化的围剿》,而这一节第一部分的标题是《文化专制与尊孔复古》,叙述的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实行文化专制和文化复古的恶行。该书强调:文化专制与尊孔复古,本身便是围剿革命文化的一种方式。该书指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国民党当局出于‘一党专政’的集权政治的需要,不仅把持着中国的社会与经济命脉,而且极力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其手法不仅融合了中国古代的文化专制,渗进近代法西斯主义的文化禁锢,而且打着三民主义和‘训政’的旗号。”南京政府成立伊始,便将“三民主义”定于一尊,宣布反对三民主义就是“反革命”,同时,国民党的御用理论家又阉割、 歪曲孙中山的主义和思想,“其重要特点之一就是将三民主义儒学化,给它接上中国古代正统思想传承的‘道统’。蒋介石曾以一种新的专制主义作为他推行个人独裁和巩固其统治地位的武器。” 该书指出:“蒋介石为把三民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封建伦理融为一体,早在1928年4月,南京政府就下令恢复孔孟旧道德”。所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和“格物致知、正义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被作为道德的“标准”。该书特别强调,国民党是打着捍卫、弘扬传统文化的旗号对共产党进行“围剿”的,因为他们认为,中共的一大罪状,便是反对、 毁灭传统文化:“1933年2月国民党中央为配合对红军和苏区的军事围攻,令各级党部及社会团体悬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匾额。接着国民党政府教育部又宣布以‘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为‘小学公民训练标准’。陈立夫在担任国民党中宣部长时提出,要用上述‘八德’作为对付共产党一切偏激宣传的对策。在蒋介石等的鼓噪下,思想文化领域掀起了一股‘尊孔祀圣’、‘复古读经’的浊流。”
1928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进行“二次北伐”期间,蒋介石就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亲自到曲阜祭孔。接着,又发布保护孔庙令,并且把保护孔庙、 尊孔读经与铲除共产主义挂上钩:“保护孔庙之义,盖欲为共产主义之根本铲除,非提倡固有的道德智能,不足以辟邪说而正人心。”蒋介石反复强调要用以“仁”为中心的三民主义“来打倒‘共匪’不仁的异端邪说”。该书告诉人们:“国民党军队就是在蒋介石‘行仁’的旗号下,在第五次军事‘围剿’中,实行极其野蛮的烧、杀、抢政策的。”
1934年的所谓孔子诞辰日,南京国民政府隆重纪念,但国民政府醉翁之意不在酒,纪念孔子诞辰,是为了为围剿中共“苏区”提供精神动力和理论支撑。李新总编的《中华民国史》指出:“南京国民政府为了配合对苏区的第五次军事‘围剿’,在孔子诞辰当日掀起了一个尊孔祀孔高潮。”蒋介石特派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叶楚伧代表中央至曲阜祭孔。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亲自陪祭。8月27日当日,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党部在南京联合召开“孔子诞辰纪念会”。同日,上海、北平、天津、汉口、长沙、广州、太原、杭州、南昌等许多地方都召开了纪念大会,国民党政要何应钦、邵元冲、吴铁城、何键等发表了尊孔反共演说。到了11月,国民党中央常委会更是通过了“尊孔祀圣”的决议。可谓一片乌烟瘴气。
李新总编的《中华民国史》指出:“在学校中推行‘尊孔读经’是国民党用封建思想毒害学生、禁锢思想的重要手段。”南京政府行政院发布训令,命令各学校礼堂一类公共活动场所,都要悬挂横书“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匾额,一律蓝底白字。1934年,何键主政的湖南、陈济棠主政的广东都强令中小学读经,将所谓“四书五经”等编入教科书。各地中学毕业会考,语文题目都是经书的原句。
李新总编的《中华民国史》指出:“南京政府为配合对工农红军的围剿,1933年7月开始,在江西、福建、安徽、湖北、河南五省推行反共的‘特种教育’”,而“灌输’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固有道德”,则是“特种教育”的重要内容。
在这次雷声大雨点也大的文化复古运动中,广东是特别起劲的省份。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南天王”陈济棠是一个满脑子陈腐观念、愚昧思想之人。李新总编的《中华民国史·人物卷》这样评说掌控了广东后的陈济棠:“在文化思想上,陈济棠大力提倡尊孔读经,宣传‘四维八德’,要求部下对他举行效忠宣誓。他迷信星相风水,任命重要部属时,有的先要由术士相面。他还不惜耗费大量钱财,设法把他母亲的坟墓迁到花县洪秀全祖坟处。说那里风水好,子孙可永享荣华富贵。”
李宗仁与陈济棠接触甚多,对陈所知颇深。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联手发动了“两广事变”(亦称“六一”事变)。后来,李宗仁在回忆录里,对陈济棠多有评说。李宗仁说,“两广事变”,陈济棠是主谋,而陈济棠之所以敢于策动这次事变,与他迷信星相也有重大关系。陈济棠的大哥陈维周,是陈济棠最为敬佩之人。对这个大哥,陈济棠“可说是言听计从”。陈维周初通翰墨,人很精敏,“惟笃信阴阳命相堪舆卜算之术”。将母亲的骨殖移葬洪秀全祖坟处,也是陈维周的主意。李宗仁说,陈维周曾特往广东花县洪秀全的故乡,考察洪氏祖茔,发现洪氏祖茔正处于“活龙口”上,所以洪秀全能够做了皇帝。而洪秀全之所以只能拥有半壁江山并且及身而败,则由于祖茔葬得高了一些,如果下移数十尺,则正在“穴”上,洪秀全也就会是真正的“真龙天子”,不会只拥有半壁江山,也不会一世而亡了。陈维周认定这一墓地极其可贵,便要洪姓子孙卖与他。洪姓起初不肯,但怎经得住陈维周的威胁利诱,只得将祖茔地割爱了。陈氏兄弟遂将生母骨殖移葬于此,并且深信弟兄中很快就要出大人物了。而这当然只能是陈济棠,“因而陈济棠就野心勃勃,予志自雄”。
将洪家的祖茔变成自家母亲的墓地后,陈济棠便派大哥到南京,与蒋介石面对面接触,借机为蒋介石“看相”。陈维周回到广东后向乃弟报告在南京的看相结果。陈维周从蒋介石的“相”上看出,蒋介石难逃“二十五年这一关”。李宗仁说,此事还真有点靠谱。民国二十五年,也就是1936年,蒋介石差点死在“西安事变”中,只不过事情的发生,并没有陈济棠什么事,而是“应在张学良身上”了。又据说,陈济棠在策动“两广事变”前,陈维周特地请了翁半玄等术士替乃弟算卦,卦中有“机不可失”字样,也使陈氏兄弟相信必须大干一场。李宗仁说,这事同样有点靠谱:“孰知事变发动之后,陈济棠的空军——飞机数十架,在黄光锐率领之下,北飞投奔中央去了。原来‘机’者‘飞机’也。济棠既‘失机’便只有亡命了。也可说,他被卦仙开了一场大玩笑吧! ”其实,李宗仁只说了其一,隐瞒了其二。据李新总编的《中华民国史·大事记》,“两广事变”发生一个月后的7月2日,广东空军驱逐机三架、轰炸机四架、战斗机两架分别从广州、从化、韶关飞往长沙,投奔中央,粤空军并有尉官四五十人逃到了香港。这是其一,李宗仁所说即此事。但李宗仁没有说的是,在同一天,他的桂军空军也有12 架飞机飞离广西而投奔中央。桂空军司令兼航校校长林伟成也离职去港。
胡适在1935年1月南游时,就是被这样一个陈济棠所打压、拒斥。
在国民党掀起文化复古狂潮时,胡适是坚定的反潮流者,是反潮流阵营的领袖。
1929年,以胡适为首的自由主义阵营,发动了一场反抗国民党政权的“人权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南京政府在文化上的从“五四”倒退、开历史倒车,也是胡适批判的对象。胡适于1929年11月写了《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的长文,发表于《新月》第2 卷第6、7 号合刊。在文章中,胡适从多个方面论证“国民党是反动的”,特别强调:“至少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看来,国民党是反动的。”胡适说:“所以我们要明白指出国民党里有许多思想在我们新文化运动者的眼里是很反动的。如果国民党的青年人们不能自觉地纠正这种反动思想,那么,国民党将来只能渐渐变成一个反时代的集团,决不能作时代的领导者,决不能担负建立中国新文化的责任。”“现在的国民党之所以大失人心,一半固然是因为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人民的期望,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不能吸引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灯草尽之时。”某种意义上,不能不说,胡适不幸而言中。
在南游之前,胡适便写了多篇文章,反抗国民党的文化复古运动,其中特别令国民党内某些政要,例如陈济棠、何键之流恼火的,是1934年举国纪念孔子诞辰时胡适大泼冷水。1934年9月3日夜,胡适写了《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发表于9月9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117 号。胡适指出,蒋介石、国民党想借助孔子解决现实的政治、文化问题,是“做戏无法,出个菩萨”。文章最后,胡适说:“孔圣人是无法帮忙的;开倒车也决不能引你们回到那个本来不存在的‘美德造成的黄金世界’的! ……向前走罢! ”
三 国民党掀起文化复古潮流,胡适则站在反抗这股潮流的最前列。就是在这样的时候,胡适开始了他的南游之旅。
胡适的《南游杂忆》,清晰地记述了此次的行踪。在香港,胡适发表了五次演讲。其时,文言在香港还占优势,绝大多数中文学校,教材基本是文言。胡适当然会批判这种现象。1月6日下午,胡适在香港华侨教育会演讲,听众为华文学校的教师,有两百多人。胡适说:“我希望香港的教育家接受新文化,用和平手段转移守旧势力,使香港成为南方的一个新文化中心。”其时广东在陈济棠主导下文化复古运动特别激烈。胡适在演讲时,劝告香港文化界应接受大陆的文化新潮,在思想文化上要向前走而不要向后退,自然而然地批判了广东:
现在广东很多人反对用语体文,主张用古文;不但古文,而且还提倡读经书。我真不懂。因为广州是革命策源地,为什么别的地方已经风起云涌了,而革命策源地的广东尚且守旧如此。
应该说,胡适的批评很温婉,并没有强烈的刺激性。胡适演讲的记录稿在报纸发表了,于是引起广东当局的强烈愤怒。胡适说:“这段笔记除了‘风起云涌’四个字和‘尚且’二字我决不会用的,此外的语气大致不错。我说的虽然很客气,但读经是陈济棠先生的政策,并且曾经西南政务会议正式通令西南各省,我的公开反对是陈济棠先生不肯轻轻放过的。于是我这篇最浅近的演说在1月8日广州报纸上登出之后,就引起很严重的反对。”
但胡适在踏上广州码头时,还不知道自己在香港“闯祸”了。船到广州时,是1月9 早晨六点多。广州岭南大学的教务长陈荣捷此前已在香港,现陪同胡适到广州(岭南大学本建立于广州,后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并入其他院校,“岭南大学”1967年在香港复建)。船停靠码头后,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吴康、教授朱之谦上船来迎接,广州地方法院院长陈达材也以朋友的身份上船迎接胡适。上船来迎接的几人,此刻也不知道广东军政当局已对胡适怒火万丈。上岸前,陈荣捷和吴康两位还与胡适商谈在广州的演讲和宴会安排。胡适说:“那日程确是可怕的! ”胡适原计划在广州停留四天。四天里在中山大学和岭南大学各有两场演讲,此外还须在第一女子中学、青年会、欧美同学会等处演讲,差不多有十次演讲。上船来的朋友还告诉胡适:中山大学校长邹鲁出了布告,宣布全校停课两天,以方便学生听胡适演讲;而青年会从昨天下午开始卖胡适演讲的入场券,一个下午便卖出了两千多张。
八点多钟,朋友们把胡适送到了广州的新亚酒店。胡适在酒店阅报,始知昨天下午在西南政务会议上,就有人提及胡适在香港华侨教育会发表演说时公然反对广东的“读经政策”。但报纸没有言及西南政务会议将如何处置胡适。胡适放下报纸,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吴康就派人送了一封信来,信曰:
适晤邹滨海(引按即邹鲁)先生云:此间党部对先生在香港言论不满,拟劝先生今日快车离省,暂勿演讲,以免发生纠纷。
所谓“快车离省”,就是以最快的方式离开广东;而之所以必须尽快离去,无非因为久留恐有人身危险。但胡适也不是那么容易被吓住的。胡适想,自己既然来了,而且是第一次到广州,怎能就这么匆匆忙忙、灰头土脸地离去。正好此时广州地方法院院长陈达材问胡适是否有意会会“广州当局”。其时广东省主席是林云陔。虽云主席,不过是摆设,是受陈济棠操纵的傀儡。但林是胡适的旧交。胡适便接过陈达材的话,说应该去看看林主席。陈达材于是陪同胡适到了省政府。与林云陔相见后,林大谈陈济棠的治粤计划,然后便问胡适是否愿意见见“陈总司令”。胡适是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当面对别人进行启蒙的机会的。尤其是陈济棠这种愚昧、愚蠢而又身居要津的人,难得有当面对之批评教育的机会,偶然有了,岂能不抓住。胡适表示愿意一晤陈济棠。林云陔便给陈打电话。陈济棠回答说,本来马上要到即将出剿的剿匪部队训话(这“匪”应指中共的红军),既然胡适来了,他愿意推迟出发,与胡适谈谈。陈济棠的总司令部就在省政府隔壁,从楼上可以直接过去。陈达材陪同胡适到了总司令部,在会客室略坐后,陈济棠就进来了。
陈济棠先开讲,讲的是广东官话,大概类似于今天的“粤普”。但胡适几乎能全懂,两人谈了一个半小时,陈济棠说了四十五分钟,胡适也说了四十五分钟,在表达的时间上算是旗鼓相当。胡适说,陈济棠的态度很不客气。这是很可以理解的。陈济棠此时是“南天王”。香港虽云在英国人治下,但毕竟是广东的近邻。胡适从遥远的北国跑到陈济棠的眼皮底下骂广东,在陈济棠看来未免太放肆。陈济棠说:“读经是我主张的,祀孔是我主张的。拜关、岳也是我主张的。我有我的理由。”陈济棠滔滔不绝地讲着。他说了自己民国十五年曾到莫斯科去研究苏联,准备回国参加共产党、当红军司令,但研究的结果是意识到共产主义是错误的,于是决心反共。他向胡适吹嘘了他的两大政纲:第一是生产建设,第二是做人。生产建设的政策就是那个“三年计划”,这主要是要创办数十个各类工厂。说完了生产建设的构想,陈济棠开始说起“人”的建设,而声调也高昂起来、情绪也激动起来。陈说:生产建设可以尽量用外国机器,外国科学,甚至于不妨用外国工程师,但是,“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必须到本国文化里寻找。这就是他主张读经祀孔的理论根据。
胡适静听着陈济棠说完,才很客气地强调,陈济棠的主张与自己的主张只有“一本之别”。像陈济棠一样,胡适也强调生产建设也好,做人也好,都要有个“本”。所不同者,陈济棠认为生产建设可以外国的“科学”为“本”,而做人则必须读经祀孔、以本国文化为“本”。奉行的是“二本主义”。而胡适则认为,生产建设和做人,都要以“科学”为“本”;生产建设离不开科学知识,做人也同样离不开科学知识。这是“一本主义”。
陈济棠本来就是有着怒气的。胡适的“一本主义”令其怒上加怒,于是怒目圆睁,厉声说:“你们都是忘本! 难道我们五千年的老祖宗都不知道怎样做人吗? ”
胡适不会动怒,仍然平心静气地说:“五千年的老祖宗,当然也有知道怎样做人的。但就绝大多数的老祖宗说来,他们在许多方面实在够不上做我们‘做人’的榜样。举一类很浅的例子说罢。女人裹小脚,裹到骨头折断,这是全世界的野蛮民族都没有的惨酷风俗。然而我们的老祖宗居然行了一千多年。大圣大贤,两位程夫子没有抗议过,朱夫子也没有抗议过,王阳明、文文山也没有抗议过。这难道是做人的好榜样? ”
陈济棠的怒火当然又往上蹿了一分。但也无法反驳胡适,于是只得泛泛地骂“现存的中国教育”,说“都是亡国的教育”。又说中国人学的科学,都是皮毛,都没有“本”,所以都学不到别人的科学精神,也因此都不能创造。胡适也以实例反驳之。
也谈到了读经问题。胡适强调,自己并不反对古代经典的研究,只是“不能赞成一班不懂得古书的人们假借经典来做复古的运动。”胡适说,这次本来打算在中山大学两次讲演都讲“儒与孔子”,这也是在对古代经典进行研究。但中山大学提出“儒与孔子”一次讲完,另一次讲一个“文学的题目”。胡适便提议第二次讲“怎样读经”,与此地的少年人谈谈研究古代经典的方法。胡适在《南游杂忆·广州》中写道:“我说这话时,陈济棠先生回过头去望着陈达材,脸上做出一种很难看的狞笑。我当作不看见,仍旧谈下去。但我现在完全明白是谁不愿意我在广州‘卖膏药’了! ”陈济棠脸上“难看的狞笑”,正在告诉胡适,正是他不愿意胡适在广州讲演。
胡适是一个乐观的人,总相信“启蒙”不会完全没有效果。从陈济棠的总司令部出来后,陈达材安慰胡适说,他对陈济棠费的这番口舌,不会完全是白费。但胡适这一次却有些悲观:“我相信天下没有白费的努力的,但对达材的乐观我却不免怀疑。这种久握大权的人,从来没有人敢对他们说一句逆耳之言,天天只听得先意承志的阿谀谄媚,如何听得进我的老实话呢? ”
回到新亚酒店,诸位友人在等候。而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吴康又送来一信,说:
鄙意留省以勿演讲为妙。党部方面空气不佳,发生纠纷,反为不妙,邹先生云,昨为党部高级人员包围,渠无法解释。故中大演讲只好布告作罢。渠云,个人极推重先生,故前布告学生停课出席先生讲演。惟事已至此,只好向先生道歉,并劝先生离省,以免发生纠纷。
看来,陈济棠和广东省党部,只是对胡适在中山大学的演讲特别在意。省党部高级人员包围校长邹鲁,当然是质问中山大学为何请胡适讲演?并且连讲两场? 并且全校停课听胡适讲演?
陈济棠也好,省党部也好,看来都并没有明确下达禁止胡适讲演的命令,只是表示了不满。那时候,即便是陈济棠这样的肆无忌惮的土皇帝,也不便明令禁止胡适在广州的讲演的。
四 明白了广州军政当局并不希望自己在广州公开发表意见后,胡适干脆把在广州的所有讲演取消。如执意要讲,也许会给邀请、张罗讲演的朋友带来麻烦。但胡适也并没有立即逃走。这点自信和胆量,胡适还是有的,胡适决定在广州“痛痛快快的玩两天”。当胡适等人到广雅书院旧址、现第一中学参观时,上千学生得知来者是胡适,便团团围住,有的还要求照相。学生们环绕着胡适、跟从着胡适,并不说话,但脸上的神气令人感动。胡适等人匆匆出来,许多学生跟着校长一直送他们到校门口。胡适在《南游杂忆·广州》中写道,上了汽车,他对同游的两位朋友说:“广州的武人政客未免太笨了。我若在广州演讲,大家也许来看热闹,也许来看看胡适之是什么样子;我说的话,他们也许可以懂得五六成;人看见了,话听完了,大家散了,也就完了。演讲的影响不过如此。可是我的不演讲,影响反大的多了。因为广州的少年都不能不想想为什么胡适之在广州不演讲。我的最大辩才至多只能使他们想想一两个问题,我不讲演却可以使他们想想无数的问题。陈伯南(引按:陈济棠字伯南)先生真是替胡适之宣传他的‘不言之教’了! ”
在广州玩了两天多,胡适便被广西方面派专机接往广西梧州了。
胡适南游期间,思想文化界颇有些动静。1935年1月10日,胡适还在广州时,上海的十名教授,王新命、何炳松、武堉干、孙寒冰、黄文山、陶希圣等,在《文化建设》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上,发表了著名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这样的宣言,其实是为了迎合、配合国民党的文化复古运动和蒋介石倡导的所谓“新生活运动”。宣言批判了“五四”以来对西方文化的推崇,主张恢复、弘扬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个宣言发表后,影响很大,许多报刊参与了论争。面对这样的宣言,胡适不可能不发言。胡适的《南游杂忆》之所以到八月间才写完,就因为时常要停下回忆的笔而面对更迫切的问题。1935年3月30日,胡适写了《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发表于次日出版的《大公报》,又发表于4月7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145 号。胡适指出,十教授之所以发表这样的宣言,“是他们的保守心理在那里作怪”,同时,“他们的宣言也正是今日一般反动空气的一种最时髦的表现”。十教授所痛心疾首的,是中国文化“本位”的丧失,胡适指出,这完全是杞人忧天。文化本是有惰性的,而中国文化的“本位”,惰性就更强了,“戊戍的维新,辛亥的革命,五四时期的潮流,民十五六的革命,都不曾动摇那个攀不倒的中国本位”。十教授声称:“中国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已经失去它的特征。”针对此种论调,胡适写道:
我们的观察,恰恰和他们相反。中国今日最可令人焦虑的,是政治的形态,社会的组织,和思想的内容与形式,处处都保持中国旧有种种罪孽的特征,太多了,太深了,所以无论什么良法美意,到了中国都成了逾淮之橘,失去了原有的良法美意。政治的形态,从娘子关到五羊城,从东海之滨到峨嵋山脚,何处不是中国旧有的把戏?社会的组织,从破败的农村,到簇新的政党组织,何处不具有“中国的特征”? 思想的内容与形式,从读经祀孔,国术国医,到满街的性史、满墙的春药,满纸的洋八股,何处不是“中国的特征”?
即便没有不久前的南游,胡适也会反击十教授的满纸昏话。但有不久前的南游,胡适对十教授的荒谬就有更痛切的认识。在广州的遭遇,会让胡适更深切地感到,十教授的所谓宣言,有多么滑稽可笑。
在1935年4月7日的《大公报》上,傅斯年发表了文章,谈论了“经”之难解。提倡“读经”,前提是“经”是可读、可解的。而傅斯年指出,那些“经”,相当程度上是今人不可读、无由解的。傅斯年当然很有资格说这样的话。对傅斯年的文章,胡适大为赞赏,于4月8日写了《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在4月14日出版的《独立评论》第146 号上,胡适转载了傅斯年的文章,同时也发表了自己的《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以为呼应。
傅斯年文章指出:
经过明末以来朴学之进步,我们今日应该充分感觉六经之难读。汉儒之师说既不可恃,宋儒的臆想又不可凭,在今日只有妄人才敢说诗书全能了解。有声音文字训诂学训练的人是深知“多闻阙疑”“不知为不知”之重要性的。那么,今日学校读经,无异于拿些教师自己半懂半不懂的东西给学生。……六经虽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半不懂的东西,一旦拿来给儿童,教者不是浑沌混过,便要自欺欺人。这样的效果,究竟是有益于儿童的理智呢,或是他们的人格?
胡适认为,这是傅斯年文章中“最精确的一段”,而傅斯年所强调的“经”之难以读、不可解的道理,“可以预料是提倡读经的文武诸公决不会了解的”。胡适在《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中,首先引用了傅斯年的这番话。接着便是对这段话意思的阐释和发挥。胡适说:“今日提倡读经的人们,梦里也没有想到五经至今还只是一半懂得一半不懂得的东西。”这道理为什么几千年来并不广为人知,就因为自古以来,研究“经”的人,谁也不敢说自己对“经”有许多地方不懂:“毛公、郑玄以下,说《诗》的人谁肯说《诗》三百篇有一半不可懂?王弼、韩康伯以下,说《易》的人谁肯说《周易》有一大半不可懂? 郑玄、马融、王肃以下,说《书》的人谁肯说《尚书》有一半不可懂? 古人且不谈,三百年中的经学家,陈奂、胡承珙、马瑞辰等人的《毛诗》学,王鸣盛、孙星衍、段玉裁、江声、皮锡瑞、王先谦诸人的《尚书》学、焦循、江藩、张惠言诸人的《易》学,又何尝肯老实承认这些古经他们只懂得一半? ”所以,傅斯年所说的“六经虽在专门家手中也是半懂半不懂的东西”,这是现代的极少数专门家的见解,是那极少数“有声音文字训诂学训练的人”的认识。而“这种见解,不但陈济棠、何键诸公不曾梦见,就是一般文人也未必肯相信”。
主张读经的文人和武人、文人兼武人的人和那些不文不武的人,都坚信古代的“经”是今人句句能懂的。如果告诉他们其实古代的“经”即便是专门“治经”的学者,也是半懂不懂、似懂非懂的,他们一定瞪大眼睛,始而惊讶,继而愤怒。其实,比傅斯年更早地承认、指出了这一点的,是现代“新经学”的开创者王国维。王国维的《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一开头就说:
《诗》《书》为人人诵习之书,然于六经中最难读。以弟之愚暗,于《书》所不能解者殆十之五,于《诗》亦十之一二。此非独弟所不能解也,汉魏以来诸大师未尝不强为之说,然其说终未可通,以是知先儒亦不能解也。其难解之故有三,讹阙一也(此以《尚书》为甚);古语与今语不同二也;古人颇用成语,其成语之意义与其中单语分别之意义又不同三也。
唐宋之成语,吾得由汉魏六朝人书解之。汉魏之成语,吾得由周秦人书解之。至于《诗》《书》,则书更无古于是者,其成语之数数见者,得比校之而求其相沿之意义,否则不能赞一辞。若但合其中之单语解之,未有不能龃龉者。
胡适也引用了王国维的这几段话。胡适强调,“这是新经学开宗明义的宣言,说话的人是近代一个学问最博而方法最缜密的大师,所以说的话最有分寸,最有斤两。”王国维这样的人坦然地说《诗经》自己有十分之一二不懂,而《尚书》自己有一半不懂,实在是石破天惊的。从王国维的时代一直到今天,有谁敢说对先秦的那些“经典”,自己比王国维更懂? 有谁敢说,《诗经》自己句句都懂? 有谁敢说《尚书》自己不懂的只有十分之四?
王国维指出,汉魏以来的大师,都是“强为之说”,也就是不懂装懂;心里并没有懂,嘴上笔下却显得懂了。王国维指出《诗经》《尚书》这类“经典”难懂的原因有三。一是文字的错讹和遗阙。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有些文字弄错了,有些文字脱落了,原貌便永不可知。第二、第三个原因,都是训诂的问题。王国维说,唐宋的书中有不解之语,还可参照较其更早的汉魏书解之;汉魏的书中有不解之语,还可参照较其更早的周秦书解之。而《诗经》《尚书》没有较其更早的书,有不解之语,没有可参照者,所以便不可解。
胡适进一步发挥了王国维的观点,指出,古经之难解,不仅难在单个字词的理解,“还有更重要的文法问题”。古经的文法,亦即组织字词的方法,与后来不同,不弄懂这一层,即便每个字词都懂了,仍然不解其意。
也许有人会说,现代研究古经的“工具和方法都比前人稍进步了”,所以古经可以懂得更多。而胡适强调,正因为“工具和方法”进步了,我们“也许比王国维先生的估计还要更小心一点,更谦卑一点”。王国维说他《诗经》不懂处有十分一二,《尚书》不懂处有十分之五。而胡适说,严格一点估计,《诗经》不可解处,恐怕有十分之三四,而《尚书》不可解处,也不止十分之五。胡适进而指出:“就是《论语》《孟子》也至少有十分一二是必须经过新经学的整理的。”
胡适的《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以这样的话结束:
在今日妄谈读经,或提倡中小学读经,都是无知之谈,不值得通人的一笑。
五 胡适是在南游归来后写这篇《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的。当他写着这篇文章的时候,眼前一定浮现着陈济棠的嘴脸,一定又一次看见了陈济棠丑陋的狞笑。主张读经的陈济棠之流,何尝知道所谓的“经”到底是怎么回事。
胡适南游,惊动的不只是主政广东的陈济棠,也惊动了主政湖南的何键。胡适在香港批评广东,在湖南的何键也愤怒了。1935年2月9日,也就是胡适北归不久,何键致电广东当局,表示对广东文化复古政策的支持,同时对胡适严厉责骂:
自胡适之倡导所谓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口号,煽惑无知青年,而共产党乘之,毁纲灭纪,率兽食人,民族美德,殆扫地荡尽。我政府惩前毖后,近特隆重礼孔……举国上下,莫不翕然景从。独胡氏惧其新文化领导头衔不保,复于《独立评论》撰文,极词丑诋,公然为共匪张目,谓其慷慨献身,超越岳飞、文天祥及东林诸君子之上。丧心病狂,一至于此,可胜浩叹。……键身膺剿匪重任,深恐邪说披猖,动摇国本,故敢略抒所感,以为同声之应。甚愿二三卫道君子,扶持正义,转移劫运。
何键在胡适离开南方不久打电报给陈济棠,应该是闻知了陈济棠对胡适的冷遇、拒斥而兴奋,故致电表示对陈济棠的支持。何键的电报,颇有意思。他指责的是胡适于上一年写的《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何键认为胡适之所以反对祀孔,是为了保住自己新文化领导的头衔,这真让人哭笑不得,可谓以鄙夫之心度君子之腹。何键强调胡适反对文化复古是“为共匪张目”,也耐人寻味。何键又强调自己“身膺剿匪重任”,所以必须反对胡适而捍卫旧文化。何键要“剿”的“匪”,当然是“共匪”,而把“剿匪”与反对胡适和捍卫旧文化联系起来,说明在何键看来,胡适、新文化和共产党是一回事,都是旧文化的敌人,都在应予剿灭之列。
何键是武人。但对胡适的新文化主张切齿痛恨的,更有文人。胡适离开广州后的第二天,1月12日,广州各报刊登了中山大学中国文学系教授古直、钟应梅、李沧萍三人联名发出的两份电报。后来,李沧萍发表谈话,声明事先并未与闻此事,是古、钟两人擅用了他的名义。那么,电报便实际表达的是古直、钟应梅两个教授的意见。第一份是打给西南及广东军政警当局的,电文如下:
广州分送西南政务委员会,陈总司令,林主席,省党部,林宪兵司令,何公安局长勋鉴,昔颜介庾信,北陷虏廷,尚有乡关之重,今胡适南履故土,反发盗憎之论,在道德为无耻,在法律为乱贼矣,又况指广东为殖民,置公等于何地,虽立正典刑,如孔子之诛少正卯可也,何乃令其逍遥法外,造谣惑众,为侵掠主义张目哉,今闻尚未出境,请即电令截回,径付执宪,庶几乱臣贼子,稍知警悚矣,否则老口北返,将笑广东为无人也,国立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古直、教员李沧萍、钟应梅,等叩,真辰。
古直、钟应梅几个教授,吁请广东当局在广州将胡适“立正典刑”,也就是“就地正法”,不应放他离开粤境。他们听说胡适虽离开了广州但尚在广东境内,所以才以电报的方式请求当局电令有关人员将胡适截留,押回广州,杀掉了事。但胡适可能在截留命令下达前到了广西,于是,古直教授、钟应梅教授随后又给广西军政当局发电报。电文如下:
探送梧州南宁李总司令、白副总司令、黄主席,马校长勋鉴(引按前段列举胡适罪状与上电同,故略)今闻将入贵境,请即电令所在截留,径付执宪,庶几乱臣贼子,稍知警悚矣,否则公方剿灭共匪,明耻教战,而反容受刘豫、张邦昌一流人物以自玷,天下其谓公何,心所谓危,不敢不告。国立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古直、教员李沧萍、钟应梅叩,真午。
如果广东方面来不及截留而任胡适到了广西,那么就请广西当局在那里将胡适杀掉。胡适读了这样的电报,应该明白广州的朋友希望其“快车离省”,真不是没有道理。
针对古直之流的电报,胡明在《胡适传论》中有一番议论:“中国旧式知识分子如古直、 钟应梅之流,对胡适、对新文化运动潮流之刻骨仇恨,必欲食肉寝皮而后快,其磨牙吮血之声,确实令人胆寒而催人深思。他们比起武人如陈济棠总司令来,实在要可怕得多、凶狠得多,也残忍得多。联想‘五四’当时林琴南之狺狺咒詈《新青年》同人,必欲撺掇武人(如徐树铮)来捉拿、来击杀、来正法,与古、钟所谓‘立正典刑,如孔子之诛少正卯’何其相似! 这样看来,中国的旧军阀旧武人实在要比旧文人旧知识分子开明得多,通达得多,也理智得多。后者真地是动不动要为他们的‘正义感’而滥杀人的。”
其实,比军阀、武人更凶残的,并非只是旧文人、旧知识分子。许多新文人、新知识分子,在面对思想文化方面的异见时,在捍卫他们的“道”时,心里也是在磨刀霍霍的。
2016年11月13日完稿
2017年1月6日改定
注释:
(1)(3)(12)见《胡适文集(5)》,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第626—627页,第637 页,第451 页。
(2)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67—268 页。
(4)(15)(16)胡明:《胡适传论》,下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6月版,第771—772 页,第775 页,第770 页。
(5)所引《中华民国史》第八卷内容,见中华书局2011年7月版,第339—343 页。
(6)见《中华民国史·人物卷》第一卷,中华书局2011年7月版第272—273 页。
(7)李宗仁的回忆,见《李宗仁回忆录》,下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5年12月版,第486—487 页。
(8)见《中华民国史·大事记》第七卷,中华书局2011年7月版,第5176 页。
(9)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见《胡适文集(5)》,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10)胡适:《写在孔子诞辰纪念之后》,见《胡适文集(5)》,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11)胡适在广州情形均见《南游杂忆·广州》,《胡适文集(5)》,欧阳哲生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
(13)王国维:《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书》,见《王国维论学集》,傅杰编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6月版。
(14)所引胡适《我们今日还不配读经》内容,均见《胡适文集(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