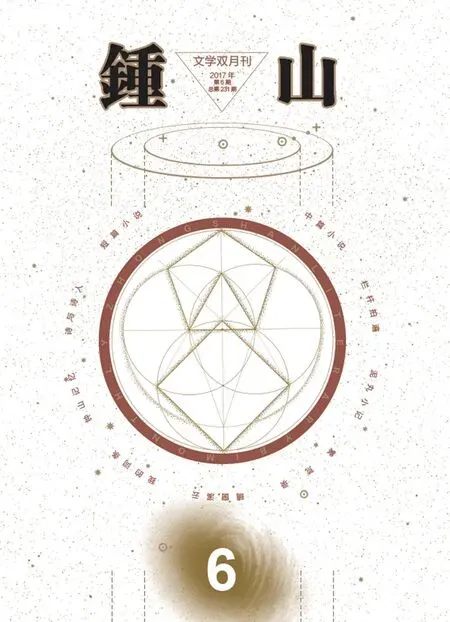船离开了我: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对纳粹的逃离
2017-11-13王彬彬
王彬彬
奥地利作家格奥尔格·马库斯所著的《弗洛伊德传》 和德国作家阿尔布雷希特·弗尔辛所著的《爱因斯坦传》都写到了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这两个“在世的最著名的犹太人”初次会面的情景。那是在1926年。1856年出生的弗洛伊德这一年七十岁,早已是蜚声世界的科学家、心理分析大师。1879年出生的爱因斯坦,这一年四十七岁,十几年前就已经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也早已是享誉全球的传奇性的物理学天才。
马库斯在《弗洛伊德传》中说,1926年的圣诞节,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在柏林会面,喝着咖啡谈了两个小时。弗尔辛在《爱因斯坦传》中则写得详细些。当时,弗洛伊德和儿子厄斯特一起在柏林过圣诞节,爱因斯坦偕妻子拜访了弗洛伊德,谈话时间长达两小时。两种传记都写到了弗洛伊德对两人初次会面的记述:“他快乐、自信、和气,对于心理学的了解程度一如我对物理学的了解,所以我们的交谈很愉快。”
在希特勒开始对犹太人进行旨在种族性灭绝的大屠杀中,许多犹太人知识分子或自杀或被杀,而弗洛伊德和爱因斯坦是属于少数在大屠杀前即逃离纳粹的犹太人知识分子。爱因斯坦在1933年3月即宣布放弃德国国籍,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安顿下来,其时希特勒刚刚登上德国总理的宝座。如果考虑到有那么多普通或并不普通的犹太人在可能逃离纳粹时没有逃离,而在渴望逃离时无由逃离,只能任由纳粹宰割,最终凄惨而屈辱地死在枪口下或毒气中,就不能不佩服爱因斯坦的敏锐。弗洛伊德生活在维也纳。1938年3月,纳粹德国吞并了奥地利,6月4日,弗洛伊德和他的家人乘火车离开了维也纳,定居于英国伦敦。
弗洛伊德是极不情愿逃离维也纳的。在纳粹的铁蹄开始恣意践踏奥地利后,弗洛伊德最亲密的朋友催促弗洛伊德尽快离开奥地利,弗洛伊德回答说:移民犹如战士放弃了自己的岗位。朋友最终用“泰坦尼克号”上二副的故事说服了弗洛伊德。当“泰坦尼克号”开始下沉、锅炉爆炸的时候,二副莱托勒被气浪顶到海面,得以幸存。后来,在接受审讯时,莱托勒这样回答为何弃船而逃的讯问:“我从来没有离开船,是船离开了我。”
一 希特勒及其追随者对犹太人的歧视、迫害,并不是希特勒攫取了政治大权后才开始的。在希特勒一步步通向权力顶峰的过程中,始终有对犹太人的辱骂、侮蔑和损害相伴随。希特勒无疑是发自内心的恐犹和反犹者。但是,在为攫取最高权力而奋斗的过程中,反犹也往往是一种策略,一种政治手段。高举反犹的大旗,有利于政治上的成功。希特勒的反犹,多大程度上是发自内心,多大程度上是一种策略、手段,本不易说清。
既然如此,德国的犹太人早在希特勒攫取最高权力前,便生活在日常性的被侮辱与被损害中了,只不过程度远没有后来那么严重。
克劳斯·P.费舍尔在《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中援引绍尔·弗里德兰德尔的话说:“值得注意的是,纳粹分子是通过企图将犹太人直接驱逐出文化领域开始他们对犹太人的攻击的,在这个领域,犹太人无疑发挥了最有害的影响。”当时,在德国的八千万人口中,犹太人只有五十万,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是很小的,但在文化领域活跃着并发生重大影响的人士中,犹太人却占了很大一部分。这自然令希特勒这类人痛恨,因此,对犹太人的攻击、迫害、驱逐,也自然而然地从文化领域开始;对犹太人知识分子的摧残,也分外严酷。在纳粹尚未攫取全面统治德国的权力时,就已经频频对犹太人施以语言和行动的暴力,那时就把犹太人知识分子作为重点打击的对象。爱因斯坦也不能幸免。实际上,正因为爱因斯坦以犹太人的身份做出震惊世界的科学贡献,正因为爱因斯坦以犹太人的身份获得诺贝尔奖并成为超级名人,正因为爱因斯坦以犹太人的身份成为神话般的人物,便令德国有着反犹思想和情绪的人心烦意乱、坐立不安。他们总是直接或间接地表示:相对论是爱因斯坦的理论,而爱因斯坦是犹太人,所以相对论是一钱不值的谬论。1922年,在莱比锡召开的自然科学家大会上,有人对爱因斯坦发起猛烈攻击。攻击者反对把爱因斯坦说成是“德国科学家”,并“号召培养健全的德国精神”。这里的意思是,爱因斯坦只是一个犹太科学家,而犹太科学家是不配称作“德国科学家”的。所谓“健全的德国精神”,无非就是“雅利安精神”。换言之,只有排除了犹太人精神,“德国精神”才能“健全”。对爱因斯坦科学成就的“犹太性”如此激烈的攻击,使这次的自然科学家大会“成为典型、粗暴的反犹太人战场”。会场上的反犹声浪得到了会场外的呼应。没有资格参加大会的人,在莱比锡演讲大厅外面散布从会场传出的“培养健全的德国精神的呼吁”,他们“反对在社会上过分强调相对论的重要性,他们还号召举行反对示威”。这个时候,阿道夫·希特勒还是混迹于慕尼黑的“无名政治家”,他对科学界的反犹言行表示了热烈赞同。在一家无名刊物上,希特勒发出了咆哮:“曾经是我们最伟大骄傲的科学,今天却由犹太人来教授,对于他们,科学只是故意、系统毒害我们国家精神的工具,因此导致我们国家内部的崩溃。”
在自然科学家大会这样的场合,爱因斯坦都受到这样下流的攻击,在日常生活中,就更是常常遭受骚扰、谩骂了。在二十年代,犹太人的仇恨者经常在威廉学院等着爱因斯坦出现,然后发出“犹太科学家”的狂叫。爱因斯坦的信箱里,往往塞满了攻击其“犹太性”的信件。有一次,爱因斯坦在柏林大学演讲,一群右翼学生粗暴地打断了他,一个学生并且吼叫道:“我要切开这个肮脏的犹太人的喉咙。”还有一群自称是科学家其实根本不懂物理学的人,租用柏林爱乐乐团的音乐厅,发表旨在揭露“爱因斯坦骗局”的系列演讲。还有犹太恐惧症患者公开表示,愿意奖励所有刺杀爱因斯坦的人。尽管爱因斯坦对犹太恐惧症患者的攻击往往一笑置之,但也不得不承认,这种恶毒的攻击常常令他烦躁不安,以至于研究工作进行得十分艰难。
如果认为犹太恐惧症患者极端仇视爱因斯坦这样的人,仅仅因为爱因斯坦是犹太人,那就会失之于偏颇和肤浅。更为深刻的原因,恐怕还在于他们对爱因斯坦理论的恐惧。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剥夺了德国公众一些被认为是良好生活本质的东西,它们是绝对之物——晚餐七点开始,这就是这个世界的正义。”爱因斯坦的理论,强烈地冲击了德国民族主义者僵化的世界观的基础,所以他们才表现得与爱因斯坦不共戴天。
爱因斯坦是“天生的和平主义者”,反对一切形式的战争。在爱因斯坦看来,国际联盟对战争做出禁止使用化学武器一类限制,是并不值得赞美的,因为这仍然认可了战争的正当性。他说:“对我来说,给战争加上某种限制是没有意义和根据的。战争并不是游戏,所以也不可能按照游戏的规则进行。我们必须反对战争,只有发动广大群众起来反对和平时期的军事服务才能更加有效地反对战争。”爱因斯坦认为,发动民众拒绝服兵役,是阻止战争的有效手段。而德国的前景,则令爱因斯坦忧心忡忡。日益浓烈的反犹气息,让爱因斯坦预感到德国将走向军国主义。到了1930年的时候,爱因斯坦悲哀地意识到“在现在的军事体系下,任何人都可能为了国家的名义被迫进行屠杀”。爱因斯坦同时认为,唯一能避免此种局面出现的方式,是号召广大民众拒绝服兵役。爱因斯坦一再强调,所有的国际间冲突都应该以和平的方式解决而不能诉诸战争。爱因斯坦并且号召建立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和筹集一笔国际和平主义基金,以帮助那些因为拒绝服兵役而陷入生存困境的人。
这些年,爱因斯坦写了许多信,发表了许多评论,宣传他的和平主义理念,呼吁有组织地拒绝服兵役。到了1931年,德国的可怕未来变得很清晰了。“议会的解散,经济的崩溃,纳粹分子的巷战,共和党的软弱,所有这些预示着将要到来的灾难。”这一切,使得爱因斯坦产生了放弃德国国籍的想法。他给朋友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的这一想法,但是,信装入信封却没有寄出。这说明,做出这一决定,即使对于爱因斯坦这样聪慧、智敏的人,也是不容易的。在爱因斯坦死后,人们清理他的遗物,才发现这一封未付邮的信。
二 但这封作为遗物的信,毕竟让我们明白,在希特勒还没有执掌德国政权时,爱因斯坦就在考虑放弃德国国籍、永久地离开德国了。
1933年1月30日,希特勒成为德国总理办公室的主人。希特勒当上了总理,意味着德国政权开始纳粹化。手握大权的希特勒立即有计划有组织地清除犹太人的文化影响。1933年3月13日,戈培尔便受命掌管一个新的部门——公共启蒙和宣传部。绘画、雕塑、文学、音乐、戏剧、电影、广播、新闻等等,统统归这个部门管辖。如果德国的艺术家、文学家、音乐家想要继续从事他们的创造性活动,就必须参加这个组织,但是,非雅利安人不得参加,这样,犹太人就被剥夺了进行文化活动的权利。与此同时,对文化领域中著名犹太人士的迫害也开始紧锣密鼓地展开。一些人被开除了公职,一些人则被取消了国籍。于是,有的人流亡国外,更有人选择了自杀。“1933年5月10日,戈培尔鼓动了一个令人厌恶的、永远是德国文化记载中一个污点的事件——焚烧政治上不正确的图书。诗人海因里希·海涅曾经预言性地认为,从焚书到烧人仅有一步之遥。这一特别的‘清洗行动’由德国学生联合会执行。它的目标是从图书馆和书店清除非德国人的或者外国人的尤其是犹太人的作品。5月10日,德国所有的大学举行集会,学生、教授、纳粹党的官员在集会期间争先恐后地表示对纳粹政治正确性的敬意。”
希特勒开始掌权时,爱因斯坦在美国访问。戈培尔烧书时爱因斯坦仍然在美国。1933年3月下旬,爱因斯坦正要离开纽约时,报载纳粹分子闯入了他在卡普斯的别墅,目的是寻找武器和其他证据。尽管后来得知消息并不属实,爱因斯坦还是觉得放弃德国国籍的时候终于到了。爱因斯坦乘坐比利时号汽轮返回欧洲,船抵安特卫普后,爱因斯坦立即乘车赶到布鲁塞尔,在德国公使馆交还护照,宣布放弃德国国籍。从这一刻起,爱因斯坦永远地与德国断绝了关系。
至于弗洛伊德,要到1938年6月才逃离纳粹。这是因为,弗洛伊德是奥地利人,生活在首都维也纳。奥地利虽然与德国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毕竟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1938年以前,纳粹的力量不似德国般强盛。但是,虽然不似德国强盛,在奥地利,反犹的烈焰仍然灼人。同爱因斯坦一样,弗洛伊德也是和平主义者。当纳粹的气焰日益高涨时,弗洛伊德与爱因斯坦之间就和平与战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通信,这些通信并且被汇编成册,以《为何打仗》为题在巴黎以德、法、英三种文字同时出版。国际联盟也介入了翻译工作。但是,纳粹党人禁止这本书在德国发行。
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说,当然对纳粹的意识形态也构成剧烈的冲击。1931年8月。《南德意志月报》出了“反对精神分析学”的专号,整个一期刊物,全用来批判、诋毁弗洛伊德。弗洛伊德的学说被歪曲。这期刊物强调,弗洛伊德的学说“对病人,乃至整个人类所产生的影响毒害了为数不多的在他们以及人类心中依然圣洁的人类关系之一”。在1933年5月10日德国的焚书行动中,弗洛伊德的书也在焚毁之列,理由是这些书“对本能的过分强调腐化了灵魂”。消息传来,弗洛伊德颇为天真地说:“他们进步多了!要在中世纪,他们烧掉的就是我了,如今他们只烧我的书就感到满意了。”之所以说弗洛伊德此时很天真,是因为这个时候,弗洛伊德还认为纳粹只会焚书,不会烧人。至少,作为奥地利公民,弗洛伊德认为自身是安全的。弗洛伊德认为,德国不可能吞并奥地利,因为国际社会不可能认可德国的做法,而且,德国人的残暴也不适合奥地利。
但局势没有按照弗洛伊德所期望的方向发展。1938年3月11日,德军侵入奥地利,“德军飞机抢占了各飞机场,维也纳街头爬满了纳粹坦克。长期隐蔽的奥地利纳粹分子们涌上了大街,他们穿着褐色衬衫,佩带着万字臂章。”纳粹德国瞬间吞并了奥地利。弗洛伊德所期待的国际社会的干预没有发生。但是,国际社会对弗洛伊德个人的安危表达了关注。德军占领奥地利后,弗洛伊德住所的楼下总是停着一辆美国使馆的汽车。这是美国总统亲自过问的结果。得知德军占领奥地利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D·罗斯福指示驻维也纳的美国代办约翰·C·威利要关注弗洛伊德博士的安危,于是便有一辆美国使馆的汽车日夜停在弗洛伊德住所附近。一旦弗洛伊德的生命受到威胁,这辆汽车就以美国的名义进行干预、拯救。驻欧洲各大城市的美国外交官都用异常坚定、明确的语言告诉德国同行,如果弗洛伊德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那将是国际丑闻。四年前,弗洛伊德曾治疗过一个意大利女病人,而女病人的父亲是意大利元首贝尼托·墨索里尼的朋友。德军占领奥地利后,墨索里尼也直接向希特勒请求放过弗洛伊德。
这时候,弗洛伊德下定了全家移民英国的决心并得到英国的许可。但是,要从纳粹手里得到出境许可证,必须缴纳三万一千三百二十九帝国马克的“帝国逃亡税”。弗洛伊德一时拿不出这么多钱,只能借债解决此难题。收取了一大笔“帝国逃亡税”,纳粹仍不满足,还想尽量从弗洛伊德那里多搜刮钱财。1938年3月15日,三名纳粹冲锋队员冲进弗洛伊德住所,抢掠了家中用以应付日常开支的生活费。一个星期后,冲锋队员又闯入弗洛伊德家中进行了更为彻底的搜查,并带走了弗洛伊德心爱的女儿。在盖世太保总部,弗洛伊德的女儿被讯问了好几个小时,后来能够平安回家,得力于美国代办的干预。
在遭受了一次又一次的盘剥、羞辱、恐吓后,弗洛伊德一家获准离开奥地利。但还有最后一道手续必须履行:弗洛伊德必须在一份声明上签字。声明是这样写的:“我,弗洛伊德教授,特此证明,奥地利归并德意志帝国后,德国当局,特别是盖世太保对我显示了与我在科学界声誉相当的尊重和礼貌,我完全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行动,并未有任何不满之处。”弗洛伊德在声明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但加上一句话:“我要向每一个人竭力推荐盖世太保! ”
盖世太保以为这是一句赞美他们的话。
三 但像爱因斯坦、弗洛伊德这样在纳粹开始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前逃离了的犹太人,相对数字是很小的。
费舍尔在《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中写道:1941年12月7日的晚上,也是珍珠港事件的那一天,700 名犹太人被带到罗兹西北35 英里处的波兰小镇彻尔姆。12月8日上午,被改装成毒气卡车的运输箱式货车,排成长长的队列驶抵彻尔姆;700 名犹太人被装入卡车运走;废气通过管子传送到车厢内;在通往附近森林的路上,车厢里的所有犹太人,包括妇女和孩子,都被毒气杀死;而森林便成了他们的埋葬地。当这一幕上演的时候,日本对珍珠港发动了攻击。“正如吉尔伯特·马丁所指出的那样,这两个事件的关联是,这一天永远声名狼藉。”这一天,也是纳粹对犹太人“最后解决方案”开始的一天。
所谓“最后解决”,就是从肉体上彻底消灭。在此之前,纳粹试图把犹太人驱逐出德国和所有纳粹占领区。犹太人移居海外,尽管困难重重,但在纳粹统治的早期,那些相对来说比较富裕的犹太人,逃离仍然是可能的。那些有可能逃离的人之所以没有逃离,最终在大屠杀中丧生,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他们对纳粹的错误估计和对故土的难以离舍。
当纳粹开始他们的统治时,德国的犹太人大都没有料想到犹太人将被赶尽杀绝。这里的原因,部分在于犹太人认知的麻痹,部分在于希特勒早期对犹政策的变幻莫测。希特勒的目标从未发生变化,即把犹太人赶走出德国或者把他们彻底消灭。但是,希特勒也深知,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等待合适的时机。希特勒于1933年1月成为德国总理。在最初几年,希特勒感到自己的权力还不够稳固,还必须注意自己在国内国际的形象,还要以国际国内和平的维护者的面目示人。因此,这几年,对犹太人时而进行残酷的迫害,时而又似乎有所缓和。正是这种状况,使犹太人难以下定逃离的决心:“断断续续的缓和标志着希望之光,哄骗了相当多的犹太社区得出错误的结论:事态很快就会变好,正如它们过去一直那样的,或者稳定在可以忍受的水平。”
犹太人难以下定逃离的决心,还因为对德国的热爱。犹太人已经在德国生存了好多代,他们对德国有着高度的认同。德国是他们的祖国。不少犹太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作为德国军队的一员,在战场上冲锋陷阵,获得过荣誉勋章。他们曾经为德国抛头颅、洒热血,他们不愿意相信德国最终没有他们的容身之地。所以,面对纳粹的反犹行动,“许多德国的犹太人采取了坐视的态度,心怀最好的希望,决定留在德国。”
在德国的犹太人不相信希特勒真的会消灭所有的犹太人,在德国以外的犹太人更不相信。参与以色列建国、曾任以色列劳工部长、外交部长和政府总理的梅厄夫人在回忆录《我的一生》中也说,“当初所有的人,包括我,做梦也想不到希特勒消灭犹太人的誓言真的会执行。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这应该归因于善良人们的起码信任,我们不相信这种极为邪恶的事情真的会发生——或者这世界会允许这种邪恶发生。这不是说我们容易上当受骗,只是因为我们不能想象当时还不可想象的事。然而今天,对我来说,已经没有什么不可想象的事了。”
是的,对于犹太人来说,目睹了、经历了纳粹对六百万犹太人的大屠杀之后,还有什么是不可想象的呢?
一开始是不愿离开德国,后来,则是想要离开却无处可去。世界各国相继对犹太人关上了国门。
然而,也毕竟有人在一开始就洞察了纳粹的本质,就毫不怀疑纳粹会做出任何疯狂的举动。德国的哲学家卡西勒,《符号形式的哲学》和《人论》的作者,也是犹太人。1933年春天,希特勒当上德国总理不久,卡西勒就看到了纳粹体制对犹太人意味着什么。他明白,这个体制的终极目标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对犹太人的迫害,而是对犹太人的灭绝。卡西勒看清了纳粹主义的本质,即纳粹主义本质上具有非理性的毁灭性,它永远不会停止消灭它真实和想象的敌人。卡西勒私下对妻子说:“我们这种人在德国没有什么可追求,也没有什么可希望的了。” 又说:“我猜想这个政权将持续十年,但是它激起的邪恶可能持续一百五十年。”于是,卡西勒及时逃离了德国。
在洞察了纳粹的本质后,卡西勒便对纳粹的行为不再关心,因为他知道,这些都是必然要发生的,同时,这一切都是过程,而纳粹的毁灭也是必然要到来的。费舍尔在《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中说,卡西勒“一直认为,假如一个人抓住了任何生存条件的本质原则,那么他就不必使自己忙于这一环境所产生的细枝末节。甚至在他逃离德国的时候,他都没有让自己沉溺于最近发生的纳粹行为。他所担心的只是这一万字徽的国度是变态的国度。它和他过去熟悉的德国没有一点相似之处。他相信这个新的体制因为自己非理性的动力而最终自我毁灭。依靠以无限的成功不断证明自己,当成功最终转向失败的时候,这个体制将毁灭其存在。”
莱托勒说:“我从没有离开船,是船离开了我。”卡西勒逃离纳粹的时候也在心里说:“我从没有离开德国,是德国离开了我。”
2017年6月30日星期五
注释:
(1)(14)(15)(17)(18)(19)[奥地利] 格奥尔格·马库斯:《弗洛伊德传》,顾牧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11月版,第207—208 页,第203页,第208 页,第214 页,第217 页,第217—218 页。
(2)(5)(8)(9)(10)(12)[德] 阿尔布雷希特·弗尔辛:《爱因斯坦传》,薛春志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7月版,第463 页,第373 页,第441 页,第451 页,第457—458 页,第468页。
(3)(4)(6)(7)(11)(20)(21)(22)(23)(25)(26)[美]克劳斯·P.费舍尔:《强迫症的历史:德国人的犹太恐惧症与大屠杀》,佘江涛译,译林出版社2017年1月版,第279 页,第243 页,第189—190 页,第190 页,第243—244 页,第357 页,第262 页,第242 页,第242 页,第243页,第243 页。
(13)(16)[美]欧文·斯通:《心灵的激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传记小说》,朱安、姚渝生等人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11月版,下册,第541 页,第552 页。
(24)[以色列]果尔达·梅厄:《我的一生》,舒云亮译,新星出版社2014年7月版,第24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