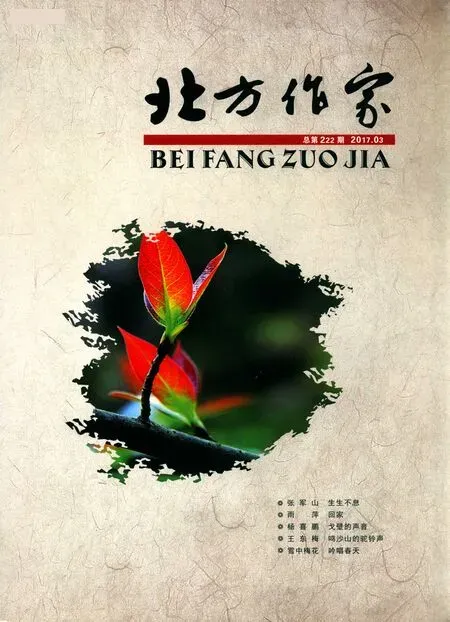镜像语言:女性意识的呈现
2017-11-13王立春
王立春
镜像语言:女性意识的呈现
王立春
题记:电影作品创造了色彩变幻的艺术形象,尤为音画映现中的女人们,就是一朵常开不败的玉莲花。
别无选择的“别离”——女人
安德烈·巴赞曾提到:“请你告诉我,当你看完一部意大利影片走出影院时,你是否感到自己高尚些,你是否强烈希望改变事物的秩序?”,巴赞曾多次强调,“人道主义”是意大利电影中最重要的价值。
伊朗电影则受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人道主义影响巨大,风格写实,镜头语言朴素,追求纯净的影像风格和简单明快的叙事。导演阿斯哈·法哈蒂在《一次别离》中体现出来了伊朗电影一贯的关注现实、扎根人性、反映社会的风貌,以一种少有的客观冷静的电影镜头和深刻而富有张力的视觉节奏,展现更广阔的人性、道德、宗教和阶层隔阂的深刻内涵,隐喻着伊朗这个国家的未来。
女性意识的呈现。把女性拍成主角,或许这是一种无意识的选择。毕竟在伊朗,女性在争取自己被剥夺的权利斗争中更加痛苦、挣扎,她们更具有抵抗力和判断。影片中导演表现出了两类截然不同的伊朗女性:女主角西敏与护工瑞茨。两类伊朗女性都于片中呈现,而且立场中肯,没有站在任何一方。戏中两位女性的斗争不是正邪之战,而是两种不同的价值观的冲突,这正是现代悲剧发生的原因。两位都是好人,却发生冲突,连观众都会产生“不知站在何方才好”的感觉。
是的,在众多情感申诉中,女性的话语权相当重要。西敏始终站在一个比纳德更为冷静的角度,知识分子的背景让她有独立思考、付诸行动的能力,向纳德提出离婚,争取孩子的抚养权,显现出的是女性独立的力量。瑞茨是另一个极端,典型的伊朗底层妇女,对丈夫由敬而畏,依赖信仰,以致替纳德80多岁的父亲换衣物,都要打电话询问是否符合教义,还因此提出辞职。看起来是片中最弱势的人物,可是她身上的力量却最有冲击力。这种力量叫做“质朴”,它无法被界定善恶。故事中没有十恶不赦的坏人,有的是不避讳人性缺点的真实人类,每个人物都有一定的善意,却都不得不面对现实生活的考验。这是一个不为观众提供任何责备对象的故事,却让每一个人物的痛苦都蔓延到观影者的心中。
用镜头语言表述生存处境。法哈蒂导演在运用长镜头这一影像表现手法时,“把纪实性美学和对伊朗社会及生活的独到关照与思索紧密结合起来,形成了独特的镜像语言风格”。《一次别离》在镜头长短的分割上忠实于自然的客观性,有好几处运用长镜头表现,准确而寓意丰富。特别是影片开篇第一个长镜头,简明扼要交代故事的来龙去脉,同时又给了人物情感的真实感和通畅感,两位演员在这段戏中的表演真实自然,充满张力。影片最后两个人等待着孩子的决定也是一个长镜头,剧中人物在等待,观众却在思考,唯一的配乐响起,就在这一固定长镜头中让观众回味着……手持镜头让观众无限逼近角色,表现冷静、客观又充满关切的风格,展现了当代伊朗人在亲情和宗教生活方面的纠结,影射批判了伊朗等级分明社会现状,直到电影完结仍使观众处在情绪当中。
冷静、客观又充满关切的镜头风格,用摄影组织故事,用摄影传达思想,用摄影阐述哲思,影片有着伊朗电影一贯的优秀特点,纪录片式的摄影手法,用长镜头还原生活的真实面貌,形成了伊朗电影作品整体的风貌与风格特征。影片结尾的处理并没有给出最终的答案,纳德与西敏隔门而坐、相对无言的不安画面,刻画出了伊朗人民在现实生活中的纠结与无奈。《一次别离》片尾留下了让人忧思的一个镜头,两家的小女孩本和睦相处,电影开头还在一起玩桌上足球,但因为大人们所属社会阶层的激烈冲突,而活生生地被逼着丢掉童真放弃善良去适应人情世故,用孩子的眼睛审视成人的进退考量,用孩子的语言道出阶层差别的无奈。
总之,《一次别离》导演的立场是客观的,用戏中人物的主观镜头来审视每一个人。导演的视角是平视的,电影中没有给任何一个角色完全的褒贬。电影没有对社会作出判决,但观众仍能从些许无奈中,看到这个社会中顽强存在的敬畏、乐观、希望和安心。“一次别离”,更多是精神割舍与外界诱因之间的抉择。
花香留痕心期许——女人
影片《蒂凡尼的早餐》那种恬静的惊艳美深深地打动了我……奥黛丽?赫本塑造的霍莉性格饱满可信,稚气而又脆弱,开创了60年代电影中女性解放角色的先河。片中突出的主题——反对“虚荣”和“金钱至上”。从1961年至今以及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该片都有着广泛而深远的现实意义。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要在内心中衡量、选择面包还是选择爱情。直到最后、霍莉才突然醒悟。最终、她尊重了自己内心的选择、知道了自己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成熟很简单、就在一瞬间。当然,这部影片的成功主要还得益于奥黛丽·赫本,她把女主角霍莉的敏感、脆弱、虚荣、任性、优雅、天真与纯情都完美结合在一起,并且很生动很自然,宛然就像在演自己,让每个观者感觉亲切而不讨厌,好似她无论犯什么错误都是可以谅解的。她的人性是矛盾的,既纯洁善良,但又时常近乎轻佻虚荣,她诚笃情痴,但又多愁善变,她既祈望未来,却又回顾止步。
霍莉遇到了住在她楼上的一位很像她弟弟的落魄年青作家保罗,保罗自从几年前出版了一本书,就再也没有作品,并且依赖着与一个贵妇人的婚外情所“馈赠”的金钱赖以生活,两人相似的遭遇和地位,使两人的心灵逐渐靠近,保罗也因此坚决离开了那个贵妇,并且重新投入到写作中,逐渐创作发表了新的作品,而霍莉在经历了弟弟意外死去的重大打击、被黑手党利用作传话人而被逮捕、并且历经两次傍大款未能成功后,最终了解到金钱财富不过是虚名,最终发现心底最需要的还是真爱,于是,在影片结尾,霍莉与保罗在下着雨的纽约街头,激情热吻,心怀爱意,迎接新的人生。
另一方面,在《蒂凡尼的早餐》中,服饰象征角色的个性特征,那套著名的小黑礼服 (Little Black Dress)具有不一样的象征作用。影片的开场便深含其味,色彩对比强烈,宛如一幅生活韵味十足的欧美油画。清晨安静的街道上驶过一辆黄色的出租车。下车的是一位身着优雅小黑裙、戴着夸张蛤蟆镜、佩戴着珍珠项链的瘦小女生……
影片中的保罗,我觉得他有些俗气,至少在《蒂凡尼的早餐》这篇小说里,他把太多来自男性世界对女性的陈旧看法涂抹在霍莉身上,涂抹上飘零、涂抹上忧愁、涂抹上坚毅却脆弱的气质,不,女性并没有变,不是因为女权主义或女性主义的裙裾飘扬而使得男性世界对女性看法显得陈旧,陈旧来自于男性的懒惰,女性在力量的对比上的确是这个世界的弱者,然而弱者并不与忧愁、飘零、不如意有直接的联系,是男性写作者的懒惰造成了这种局面,更糟糕的是有时候懒惰会直接导致媚俗。
影片的喜剧效果也别出心裁,显得亦诙亦谐,有很多精彩、搞笑、温馨的对白和场面,比如:霍莉怕被电话骚扰而把电话藏在皮箱里;楼上那个喋喋不休而且样子猥琐的日本人;水果篮里找到的高跟鞋;霍莉家里那只没有名字的喜欢在人肩膀上走动的猫;在派对中保罗被挤在地板上接电话,发现一位交际花脚踝上戴着手表;把巧克力包装袋里赠送的戒指拿到蒂凡尼珠宝店刻字;两人从廉价店偷了猫猫狗狗面具,一路戴着跑回家……这个世界上,或者在文学的世界里,的确,悲剧比喜剧更有力度,更加能够撼动人心,然而如果我们把喜剧视作悲剧就会渐渐使我们失去对悲剧的向往和鉴别力,我认为保罗通过才华和技巧将女主角霍莉篡改成一个廉价的悲剧道具。影片的结尾,伴随着《月亮河》乐声的响起,无论未来怎样,我们都会相信霍莉?戈莱特利曾经拥有的“纯洁”这一羽翼,并对未来的美好深入不疑,就像我们感受美好的童话,能够用它独有的方式,给予我们生活下去所需要的力量、温暖与希望。因为当时光沉淀,铅华尽洗,能留下来永存心中的精华,就只有过往那些真挚的情感,即使平淡、即使平凡,却永远不朽。
红尘来过意永存——女人
我发觉,电影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被理解成发生在日常生活的一起事件的,或者说是构成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是一种正在进行时,需要观众和演员去共同经历的现实,走进剧情中会发觉自己是走进了另一个世界,而它的生命却是重新开始。影院灯光暗下,就会进入到一种心情中,这种心情或感受就来自电影的精神,它使我们与世界和人生骤然有了一种新的沟通,在其中,受到了感动,也产生了幻想。《乱世佳人》是我最为喜欢的经典影片。本片其中不少音乐参考了美国民谣之父史蒂文·福斯特采集的南方民谣。片中镜头——斯嘉丽站在大树下期盼明天的瑰丽画面。这时响起了雄壮的主题音乐,将“土地不死”的精神宣泄得淋漓尽致,温馨感人,气势恢宏的史诗乐章,震撼着人的心灵。《乱世佳人》以美国南北战争为背景,着力刻画了一个任性、冷酷然而又坚强、勇敢的庄园主女儿斯嘉丽的艺术形象。人们一下就记住了:那个留着中分花蝴蝶发型,无限任性矫情的斯嘉丽!她歪起的美丽的头颅像猫咪一样可爱,随时在与人争风吃醋的无辜表情至今忘记不得。还有那个坏坏的叫瑞德的漂亮男人,更是寄托着对异性所有关于青春关于爱情的痴心妄想。电影音乐是专为影片创作的音乐,创作构思完全以影片中的思想感情、视觉形象和剧情结构为基础。音乐是一门以抒发人们思想感情而见长的听觉艺术。而作为电影音乐,它在影片中的主要功能则是根据剧情发展的需要,采用不同的音乐手段,配合画面内容,来表达剧中人物喜怒哀乐的情感,刻画人物的内心世界,从而达到塑造人物形象和深化影片主题思想的目的。在国产故事片《樱》中,有这样一个感人的场面:当日本工程师森下光子回到久别的中国养母前,她想认又不敢认,心情十分矛盾。这时电影导演在画外音响处理上用了《妈妈,看看我吧》这首歌来细腻地揭示森下光子的心理活动。在此情此景中,委婉的歌声配上真挚的表演不禁催人泪下。这里用音乐来表现人物感情的手法似乎比一般内心独白更富有感情,更富有艺术感染力。
渲染和烘托环境气氛也是电影音乐的另一个重要功能。电影音乐虽然是电影中的配角,但有时它却能能动地推动剧情发展,起到有机地组接电影镜头的重要作用。表现民族特点也是电影音乐一个独到的功能。《乱世佳人》所采用的美国南方民谣,使人闻到了浓郁的乡土气息,具有民族固有的性格特征,极为影片增色不少。小提琴是电影《乱世佳人》主题曲改编的小提琴独奏曲。至今为止,这部电影的电影原声依旧让观众记忆犹新。此外,《乱世佳人》的配乐手段与英国影片《苔丝》有相似之处。序幕:深灰色的天空沉闷而压抑,铁锈红的大地茫茫无际,深沉而富于激情的序曲音乐在广袤的原野上空回荡……。不久,音乐慢慢轻了下去,在银幕深处的地平线上出现了影影绰绰走动的人群,似乎还伴随着什么声响。渐渐地、渐渐地,人群越走越近,观众这才看清楚是一群穿着白裙,戴着花环的农村姑娘在乡村乐师的伴奏下载歌载舞地朝前走来。接着,人群来到了宽阔的草地,他们更加欢乐地双双旋转起舞,而四位乡村乐师各执着简陋的乐器:小提琴、手风琴、小号和中音号愈加兴奋地演奏着。在这充满英国田园风味的舞曲乐声中,影片的男女主人公克莱尔和苔丝初次相遇了。新婚之夜克莱尔离开苔丝远走他乡,然而对故土的眷恋又把他从异国招回家园。当克莱尔再次路过当年遇见苔丝的跳舞的草地时,场上秋风萧瑟,空无一人,但是在他的耳畔却又轻轻响起了那支熟悉的乡村舞曲,它还是那样纯朴那样欢乐,可如今苔丝她在什么地方呢?克莱尔不禁百感交集、黯然泪下……
影片的结尾,一轮暗红的朝阳正从祭太阳神的怪石林后冉冉升起,追捕的军警正从四面八方向苔丝走来,一个年轻的生命在逐步走向死亡……,然而,此刻响起的既不是悲壮的颂歌也不是沉痛的哀乐,而又是那支听见过的乡村舞曲,它虽然是那样轻微,甚至是断断续续,但它却如画面上初升的红日一样告诉人们:一颗美好的心灵虽然在黑暗中毁灭了,但她的灵魂却得到了升华。同一支质朴的乡村舞曲在影片的不同场合中先后出现了三次:第一次是作为现实生活中的音响,后两次是作为剧中人物的心声。它们相互呼应,一气呵成。这种配乐手段是如此简洁精练,既没有矫揉造作的呻吟也没有如雷贯耳的音响,却又是那样耐人寻味、令人难忘。而在《乱世佳人》的影片结尾主题曲旋律再次响起,斯嘉丽一直在做一个在浓雾中奔跑的梦,在梦中,她饥饿无助,她想找寻她也不知道的东西,直到有一天,她真的跑在浓雾里,才知道她要找瑞德,那是她的依靠,一直是他在支持她,保护她,她这才发现她爱他,而他一直也在爱她。当爱失去时,才知道它的珍贵。可惜瑞德的爱耗没了,他回家了。斯嘉丽从不缺乏勇气,踏着高昂的主题曲旋律,相信她回家疗伤之后,能如她所说找到让瑞德回来的方法,毕竟明天是新的一天了。
王立春。作家、剧作家。现任哈尔滨市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系:中国戏剧文学学会会员,中国剧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主要发表作品:文学剧本有微电影《无事生乐儿》,音乐剧《多情部落》,话剧《援助》,儿童舞台剧《华山美少年》,话剧小品《手心里的宝》,散文诗体剧《幸福的方向》等;撰稿电视纪录片《红灯记在海伦》(黑龙江电视台新闻频道播出)。作品曾荣获第五届中国戏剧文学奖;首届全国戏剧文化奖;第二届陕西戏剧奖等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