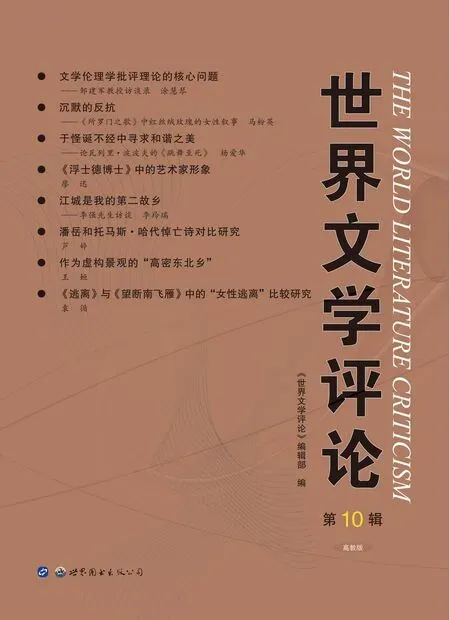新诗的地理迁变和语言现实
——新诗语境中李强的诗歌创作
2017-11-13柳宗宣
柳宗宣
新诗的地理迁变和语言现实——新诗语境中李强的诗歌创作
柳宗宣
从当代诗的迁变过程谈及中国新诗呈现的新的情景与态势,新诗的语言与生成方式的改变,论及李强在其语境里的写作方式,诗人的诗作种类与表现方式,然后用中西不同文本的比照来论述写什么与如何写的关系以及诗的语调与歌词调式的不同,最后强调新诗的形式和诗语言的现实。
当代诗 李强 诗性元素 新感性 新诗语调
一、引言:新诗的迁变地理
上个世纪初,诗人北大教授废名开课《谈新诗》到新世纪初《在北大课堂读诗》,时间相隔近一个世纪。同样是北大课堂里,同样是讲授中国新诗,其间,新诗经过了多代诗人的倾情参与,具体实践和无私传播。从既有留存的这两本书我们比照着读,可观诗文本内部的风貌发生的大幅度的迁异,可以细察辨别中国新诗这棵大树的筋脉,析解它的新的走向。从“五四”开始的白话新文化运动,到胡适、周作人、鲁迅,郭沫若、废名、卞之琳等的白话诗的开创性的工作,对白话新诗的各种尝试,汉语新诗开始了它的新生与成长,废名先生将之称为“灵魂的冒险”。废名以他个人理解的方式,以他新诗人的姿势倾情在北大课堂讲授他参与其间的理解中的白话诗。而在相隔近百年的新一代人的讲授新诗,是一群在北大执教和求学的诗人和诗歌研究者。洪子诚先生是领导者,他手下有一批志于当代新诗创作与研究的博士,他们是一个群体,每人开讲的是第三代诗人全新的当代诗歌,细读其诗作的文本与构成。有心的研究者从这样一个视角来观察和考量中国诗歌地理图,你不能不感叹中国白话诗从无到有从有到气象壮观所走过的历程。汉语新诗其前进的路径可辨,其文化地理可挖掘,其硕果累累可观瞻。
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戴望舒、林庚、穆旦、冯至、艾青等诗人的创作和译介,他们火把式的接替与运行,一直到红色政权的建立后的80年代得以恢复几中断了的近三十年新诗事业,出现了“白洋淀诗群”等地下诗歌运动,以北岛、顾城、芒克为代表的朦胧诗的登场,直到1986—1988年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的呈现,中国新诗迎来了新一轮的运动式的集体推进,此景观延续到到1989年以后的作鸟兽散,进入到20世纪90年代诗歌的整体转型,诗人们处于清寂或不安的状态下的个人艺术实验,这样处于低声部的歌写的形势下,中国新诗跨入所谓新的世纪。中国新诗的命名,诗人与诗学专家们对它发生了细微的称谓变化:白话诗、现代诗、朦胧诗、第三代诗、90年代诗歌、当代诗。尤其90年代以来,中国诗歌进行了全方位的回归本位的努力修整和补课,在诗学内部进行一个个被人忽视的“小革命”。
当代诗与时推进,自然接受了来自汉译界人文艺术的传播带来的影响,当代诗经受了来自异域的人文风浪的洗礼和误读。“在20世纪,涌现出的各种思潮几乎超出以往世纪的总和,而这些思潮的互相冲突,以及对以往理论的颠覆,更是20世纪的诗歌的特色,马克思的经济学观点和历史唯物论、社会人类学、索绪尔的语言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荣格、拉康等人的继承与发展、尼采的权力意志、胡塞尔的现象学、罗兰·巴特的符号学、德里达的解构哲学等等,给诗歌带来了全新的冲击和影响。”自然的以前未有的规模涌入中国诗学界。作为中国新文学的风向标的诗歌创作,自然受到了各种思潮的冲刷式的影响与吸纳,直接作用于它的语言观点的吸纳与变异,其诗文本的译介直接作用于中国汉诗的面貌的改写或仿写,可以说,中国新诗几乎是脱胎于国外译诗和优秀小说译本,而且不同时代的译介影响了不同年代的诗人的写作,或者说从不同汉语诗人的诗文本事可以找到它们相称的译介的外国诗人的影像。这可比照《美国现代诗选》中呈现的美国现代的实践与迁变。美国新诗的运动从惠特曼和狄金生的开启,到以后庞德倡导的意象派的原则、艾略特的诗的象征手法的强调,奥尔森的黑山派诗歌的强调的能量、以金斯伯格为代表的垮掉派自动写作,罗威尔倡导的自白派诗对个人私密生活在语言中的利用、勃莱和赖特发起的新超现实主义对潜意识的探索,这些异域诗歌的实践通过译介在中国新诗的写作中产生了不可忽视的移植式的影响。可以说,90年代以来的中国新诗被学界称为当代诗,在经过80年代的现代性新诗传统的承继与命名之后,中国新诗出现了与现时代剧变相称的当代诗的新格局。
如果说,开创时期的白话诗从古典诗歌的断裂中获得自身合法性的现代性的寻找,五四以来的新诗毫不保留地迎向现代性,寻求自身进化为现代诗,当时的白话诗充当了建构民族“共同想像体”的镜像,胡适等人将他们的写作的诗歌命名为白话诗,表明他们乌托邦的激情,到20世纪的80年代的诗歌自我标示的先锋诗歌,也是对现代激情的释放与认同。现代性就是过度、短暂、偶然,它的否定的激情,在现代社会内部自我流放的精神开放,现代派诗歌寻求着自身合法的能力,它的命名能力,体验、变形和隐喻时代的能力。第三代诗人以拒绝朦胧诗的政治对抗模式出场,遗弃启蒙的现代的宏大主题,将自己定为公共生活的反对者。那么,继而前行的90年以来的新诗,也就是当代诗,则试图写出疏离于历史的纯诗。诗人们开始建立其个人话语空间。对诗的叙事性强调(其实对诗的叙事因素的强调则是对叙事潜在的反动,在意的是能从生活事件中提取质问生活的洞察能力)。转向日常经验,着力于对本土气质的强调,令诗歌与历史的关系变得若即若离般的恍惚,与之交接的向度也变得多维而惟妙。
确实,诗歌与时代与历史的关系不再是单纯的境像关系,而是含混的隐喻关系。这从历史语境转移到了个人话语的建立,诗歌的发声在节奏、形式和构成等诸细节层面进行不断地更新与创造。况且,之前新诗的现代诗的起源与语境随着时代推移发生了变化。在近一百年来的汉语诗歌在外部与内部不断地犹豫、迁徙,与外部之间处在相互沟通融合与缠绕中,90年代的诗人们写作出“偏离诗歌的诗歌”。
具体地说,诗人们与时代沟通的愿望在当代诗的实践中得到普遍地加强;对现代诗出现的主体性的幻觉导致的自我过度沉溺,当代诗则纠正了这个偏执。当代诗对待现实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对文本现实与文本外的泛文本意义上的相互指涉的现实进行了自觉分离,而文本的现实写作者理解了的现实,包含了知识、激情、经验、观察与想象。对历史语境的束缚的提防,并将创作主体从对对自我过度的关注中摆脱出来,把创作主体看成是处在一个由历史、他人、世界诸事物组成的关联网络中,诗人们经受着朝向个人生命经验与语言技艺的双重考验;诗文体呈现出语言的精微度和认知的纤细度;他们学习着面对且处理他个人置身于其间的时代,诗人与时代的关系变得更复杂和富于韧性。换句话说,当代诗人是那些书写当下晦暗的人,他迎向当代生活,对当代历史进行持续的凝视,而非出于对现代生活无力和绝望而转身离去。这种对现代性的溢出与偏移能力,使当代诗建立起与现实的一种可靠的谦逊的关系。
如上所述,当代诗的话语空间经历的重要的转型:它从公共话语空间转向诗人个体的日常生活领域。这自然受到了胡塞尔在提出的回归“日常的生活世界”命题的影响,对抗近代以来对人的忽视,把人的活动及世界,化约为外在于个人的、与人无关的、可计算的、本质既定的存在的科学主义思维,强调可能的出路即回到前反思的生活世界中或直观思维当中。几乎同时,维特根斯坦也发现了日常生活的语言的本真性,并确立自己“把字词从形而上学的用法带到日常用法中来”。日常生活中个体的作用重要性给显现出来;从宏大的一元话语转向到个体私人话语的转型,诗人们在日常生活这个领域里开始关注主体自身的“自我观看”的技艺,超越以往与外部世界受控与反受控的二元对抗模式,诗歌试图在习得的个人话语空间里发声。从无所不能的大而空的观照世界转入个人的细微的真实的个人空间的讲述,这是当代诗的一个大的变身,语言姿态的转身。
中国当代诗,确切地说,90年代以来的诗歌完成了话语方式的转型,也就是从宏大的叙事,意识形态话语的传声筒式的发言转入个人的真实的对内外世界的理解与低语。拉康曾在他精神分析的专业领域里,把话语分为主人话语,大学话语、癔症话语和精神分析师话语,主人话语是一种能指话语,代表了所有的其他能指,代表了所有的主体,谈论所有话语;精神分析师话语与主人话语相反,主人话语占据是主体的位置,以自己的能指代替其他能指,对其他能指进行缝合,精神分析师的话语则处于客体的位置,把自己视为话语网络的残余,由此比衬地说,当代诗从主人话语里隐退,转入了精神分析师的个体的细微的发声,在个体经验与语言的空间里进行着当代诗的写作。当代诗人们开始了其个人生命的独特叙事,就是转型后对“大词”对“圣词”的自觉抵制,从而面向对个人生存的特殊处境和深度经验的开掘与呈现。由此当代诗的个人语境特显示全新的面貌。
二、李强诗歌写作中的当代诗元素
从上述谈及的中国新诗的所经历内外场域的析解,具体到诗人李强诗歌写作,他个人的诗歌写作处于何时何地,他的语言现实地理面貌有着何种特征,这是笔者所关心与在意的。
从所占有的到目前为止关于他纷呈丰富的多变多样诗歌作品来看,他似乎转入了个人空间里的书写与叙事。作为诗人的李强不是站在某个高处或广场发声。有意思的是,他在其个人的生活空间用分行的句子来对他人说话,或独白。这种诗的话语方式和品质让笔者看好,也就是如前所述的,诗人李强不是在如拉康所说的在无所不在的主人话语里露形,以自身的能指替代所有的其他能指;他的语言姿势是对着主人话语的背离与转身,面向他个人日常生活的空间,在其中用诗句呈现他作为个人的感知与情绪的语言陈述。
具体地说,他背离了自己外在的公众的身份,且从中脱身出来,以一个诗创作者独立的身份来写作,在他的日常生活领域里发现诗的蛛丝马迹。
他的诗创作不是宏大话语的叙事,是以个人视线来展开其词语的视界,他不是所谓的乡土诗的写作者,但他也通过对早年山村生活的追忆来呈现身体记忆里的山村。他写武汉这个城市的诗,十七岁的他开始远行考学进城,到大武汉生活至今,掐指算来有三十余年,他不是以一个政府官员的腔调和公文词汇来写武汉的,他的关于武汉的诗是他个人体会中的武汉,不是身外意念和某个与己无关主题的阐述,写的是他李强自己情感经历中的武汉,他写的是他如何一点点爱上这座城市的:
我在少年时走进这座城市
我在远游后回到这座城市
我把父母亲安葬在这座城市
我把青春期安葬在这座城市
在《关于向日葵的一点想法》一诗中,甚至显现了他日常生活的手势、细节,和人名、还有充满个人心愿的事件:
我要给水务局长姜铁兵打电话
我要告诉他
应该在两江四岸种满向日葵
我在少年时走进这座城市
我在远游后回到这座城市
这是我们的城市——
悠久、大气、地灵人杰
什么都不缺
就缺向日葵
从上述两首诗的片断可见,他对武汉都市生活的抒写带着他个人的情感与体温,有他个人的视觉与语调,他忠实于对个人身体里的这个城市的形象的描述。古人云,心外无物。语言之外没有诗,他的都市类的诗歌是他个人存在的词语的外化,几乎类同于皮肤与骨头。
他写城市的诗,也写行旅诗。在个人的行旅组诗(《车过北方》)中,呈现的是有着现代语言的视听和充满节律的感怀。他的最好的一首行旅诗《每次旅行都丢东西》被一些刊物选用和读者叫好。
大的都带走了
丢下小的
重的都带走了
丢下轻的
身体和随身的都带走了
丢下伸手够不着的
丢下泛黄的青春
丢下懵懵懂懂的心愿
丢下皱巴巴课本
丢下半拉子工程
丢下惊鸿一瞥
在落叶纷飞季节
丢下至爱的亲人
你也曾用力拉呀拉呀
使完了浑身的精气神
何时何地,何情何景
最后旅途丢下所有
一粒流萤微弱闪过
丢下蔚蓝色星球
其实他的行旅诗如同他的城市蓦写的是个人对存在的省思。他的花朵植物类的诗也都一样,写的是一个生命对在世万物的感应,这正如他写木槿诗:
我记得你当时并不孤单
出工、上学、走亲戚的路上
总是小姐妹们三五成群
我当时也没有和你多说话
也不觉得你有多么美
我不过把你当成了生活中的一部分
就像那些田野、院落、炊烟、烛光
以及,似乎永远也不会离我而去的亲人
诗人在和木槿对话,其实是诗人对流逝生活的喃喃自语,他的植物诗写就是自我之歌。植物与花朵成了诗人的他者。诗人李强在对它们的抒写时,找到了一个较好的视觉:在个人空间里或者说在与个人与公共空间的交叉处(如《栀子花开》诗中城区的放鹰台与回忆时空)进行打量与倾听。他有些沉湎于过往的乡村生活(邻家的小妹、那田野、院落、炊烟、烛光,不会离他而去的亲人)的回忆,又与当下身处的场景(菜市场、都市街坊)相融合;他把抒写的油菜花的场地从乡村移置到了当下的城市一角。在他的视线中,开在城市一角的油菜花有点傻,它们的笑点很低。他怀想的是乡下的灵醒的油菜花。此诗里,诗人的意念在城乡两个空间穿梭往来,他对城里的油菜花的察看与陈述,传达了他个人的特殊的理解,他的部分诗歌往往在两个或多个场景里互相参照映现,这也暗合了当代中国外部的现实情态,但笔者更在意的是从油菜花这在他看来类似于群众演员的隐喻,这命贱的油菜花修饰与命名,隐隐透现出诗人的独立的声音和意见。
展开而言,他的部分关于植物类的诗作饱满着展示出对既往确切地说是七十年代的回忆,早年乡村记忆的温馨体味。那盆“瓜叶菊”让诗人心潮起伏(详见李强诗作《瓜叶菊》)。那黑白分明的70年代,那从阳光雨水中走来的我们的姐妹,她们的手势、目光、笑容,定格在了李强诗歌回望中的70年代。李强诗歌承继着中国古典诗歌的美质,他的诗作里有歌咏的特征,这吻合了他对诗歌中的歌的元素的看重,他的诗大都押韵,他似乎在中国传统抒情诗赋比兴等元素中格外加强诗的“兴”的抒写,在意诗学上的复沓、叠韵,反复回旋的修辞,这可以回逆到中国第一部诗经中的原始审美。文有尽而意有余,这“兴”具有它含融性联想性以及弦外之音的性质。
李强诗歌中的关于自然生态的抒写,在两个维度,城乡当下与过去展开他的语言的抒写,着迷于开在诗句中的花朵。他的诗如果要归类,处于华兹华斯的物象诗的范畴,有着浪漫主义诗歌的意象与情感传达的范式,保持着写作者天人合一的审美趣味,他做的最好的是在当下城市视野里来观望这些自然残余的物象。他个人最好的诗作如《城里的油菜花》透示出了他看重的类似于浪漫派诗歌格局的可能的突破,但笔者仍要挑明的是,他的诗歌作品似乎未曾受到现代派诗歌冲刷式的捣毁与革命,现代性在他个人诗学的语境尚待表现与成就。他的代表作《萤火虫》确实可称之为其代表作,但笔者以为只是他过去词语生涯中里程碑的作品。
会飞的露珠,闪着微光
会呼吸的琥珀,记录沧桑
会舞蹈的精灵,激动整个村庄
点亮黑夜的火把,唤醒少年幻想
比一瞬间更短
比一辈子更长——
这首如同他写植物与花朵的诗一样,呈现的是自然的物象,它的抒写形式与词语生成方式可以在白话诗文本中找到对应。它的拟人的手法和常见的句式透泄出既有诗歌文本共有的浪漫的抒写语调,现代诗歌的陌生化技艺受到了某种忽视,这被历代诗人写过无数的意象(萤火虫)没有得到超常的来自于诗人个人的独特的发明式的光照,包括它的句式、节奏韵律,甚至它的押韵。如果做比照式的阅读,他的诗作《城里的油菜花》在语言范式和情感的传达的隐喻含蓄似乎先进和技艺更新了许多。后者对情感的克制与透露比前者要来得现代一些,它们的语调和切入改变了视线和方式,从这可以看出写作者在诗的朝向上的时间的变化,似乎还可以展开他对都市意象的直接纳入,更大范围内地处理个人视界中的都市生活的场景与物象。他在朝向现代诗对其颠覆性地改写,他的词语面临着挑战或更新;情感多维空间尚待侦探与开掘;他的诗歌的包容力消化能力需要更强健的胃口。作为一个诗人的词语空间自然渴望开阔与恢弘,在朝向当代诗的陌生领域的挺进的速度更需加快速度。
但笔者从他的近作《松脂》《琥珀》(参见“湖畔读诗”微信公众平台)二首诗中获得了鼓舞,他改变了咏物诗的写法,融入了现代诗的诸元素,尤其是后一首,他几乎似于蛾子伏在草纸上写遗嘱。诗人在此诗中加入少年的回忆,在词语中叙事,空间包容了不同时间的意象与事象,诗性的空间一下子给拓展了,诗的形式也不同于他的旧作,分成了多节,诗结构的营建感在形成。
李强将其个人的诗兴散溢到他的行旅他的工作之中,他的诗集不仅有回忆中萤火虫的放光,他的“一点点爱上这个城市”的当时代的动人的感兴;他还完成了他因早年经历而作的“打铁”系列——自身要硬,对象要软,师傅点出要害,徒弟火力全开——他把诗兴引入到早年打铁的劳作之中。李强还写作他的科学诗,比如他的作品《引力波引发脑瘫》《黑洞》(见《雨花》杂志2016年6期)
地球只是银河的一粒沙
银河只是宇宙的一粒沙
地球游走在黑洞、白洞、虫洞嘴边
就像磷虾游走在抹香鲸嘴边
(《引力波引发脑瘫》)
在《黑洞》一诗中,诗人这样描述:“宇宙旷野的隐士沉默的大师说够了就不再说万事万物了然于心不说出一点秘密”。诗人学的是工科,他对自然科学有着天然的兴致,当然引力波和黑洞科学物体自然进入他写作的字里行间,不过这也脱离不了他对个人存在的省思与探索,如黑洞一诗所表现的,他科学诗和其他类别的诗歌一样探究的是宇宙或人间的点点秘密。诗人李强写就的是他个人的存在之诗。
随着诗人近年外部生活的变迁,李强的写作呈现井喷状态,他的自媒体《湖畔读诗》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他几十年前对诗的爱好找到了呈现的时机,他的诗歌创作的黄金期即到来了,他的写作与其经历和身份是相关的,他做着对个人生活的观察描述观照与追忆。在这个年纪,他十分在意对个人生活的开掘,时间在他的生命里沉淀出了未显露于语言的意象与事象。现在诗界强调什么诗歌写作的地域性或草根性,这几乎都在诗的外部谈论诗,我们每个写作者都是独特唯一的写作,呈现着诗人身体性词语所携带的家乡时代地域个人经历的全息图。在个人写作的视线里,如果说有地方性也是创作者他身体的地方性,他语言里所呈现的独特于他人的语言现实。
李强的词语的事业在等待他去完成。是的,这来自他个人存在的意象与事象都纳入他词语世界,逼近一个写作者对语言的倾听与传述,在海德格尔看来,“我们不可忽视语言这个古老的本来的事实,听从语言的言说,然后进入语言的言说。”诗人李强的写作因抑制已久终得喷射的活力与语言的奇观,各种类型的诗杂然呈现,不拘于一种体式或一种题材,他的写作即有当下的也有追忆的既有沉思之语也有目击成诗,他的诗与他迁变的生活构成某种互动和隐约照应,他的存在之诗在不断地加入新的词汇与视线,比如他的近作《荷花开得恰到好处 》出现了三角湖,这与他到大学供职是相关的。他写他的城市诗花朵诗乡土诗行旅诗科学诗,他可能会写出有学院气息的类似于瓦雷里、马拉美所倡导的纯诗的。
三、新诗的写什么和如何写
新诗的写什么和如何写,成了当代新诗写作者们纠缠不清的话题。
在写什么和怎么写之间,有人倾向于前者,有人在关注于后者。这其实是关于诗的内容与形式的问题。其实这个分别没有什么必要去分别,它们几乎是一个存在物,诗所有呈现的“写什么”其实是在语言中呈现的。如何写,其实是用什么样的语言形式呈现“写什么”。恰是后者打开了前者,找到了如何写的方式,语言中“写的什么”会奇异地出现。也就是一些人所理会的诗的形式就是其内容,它们就是一体。在美国诗人奥尔森看来,形式从来说是内容的外延,这是黑山派诗人们强调的诗本身即高强度的能量结构。很多诗人把精力倾向于如何写这个问题上,在他们看来,诗是一门非常专业化的写作,强调诗写作的专业化,就是说语言或形式有它特殊于小说散文语言的形态,诗的写作不是照相式的外部现实,它的生成方式语言形态有其自身的无法归类的表现形式,而且它在不断地要求诗人们一代代地更新我们的语言,为这个古老汉语提供新的惊异感。
李强诗歌写作似乎倾向于对“物事的陈述”。即一首诗的背后有着隐隐的个人生活事件的影子的闪现,这吻合了当代诗倾向于新感性的主旨。当代诗不像既往的诗歌作品处理与己无关的抽象的宏大主题,而是对发生在个人生活中的小事件的处理,即便最后指向另一个玄妙的维度,不可言说的诗性空间,但它的起点来自于可感可触的及诗的场景及物事,这让当代诗有了它自身的肌质和张力。
比如,我们从对英国诗人哈代、拉金的诗歌中可见出诗歌中的可触的与人的生活相关的现场,其散发的诗性也变得可以触抚。如前者的《你最后一次乘车》一诗,处理的时空充盈着意象与事象,或者说它是具象的也是抽象的。后者的代表作《上教堂》强化了诗的叙事,一个清晰事件在诗中历历可观,诗的现场感毕现,诗的层次多维。这样的当代诗歌回避开了象征主义诗的空幻与晦暗之限囿,也逃离开现代主义诗歌某种诗学方面的专制,从而拓展了当代诗的对心理现实的表现力和诗能辐射的疆域。
从李强的诗歌写作中,笔者敏感到他的写作有为事而作的倾向,从他的诗作的字里行间,可辨出心里现实的影像,虽然他的诗作《城里的油菜花》只来这么一句:“一块空地就可以了”。你分明看见了油菜花的意象,诗展示的场景,由此引发的诗句都是从此可触的“空地”而生发出来的,当代诗的新感性也由此见出端倪,从他的近作《琥珀》可体现出其创作新的亮点。
李强所有类别的诗注重诗的歌咏特性。他对他自己的诗皆能背诵。而笔者特别在意他在个人语调中加入了摇滚般的节奏,如《三月来到北方》这样的呈现:
铁骑御风而行
三月来到北方
高人闻歌起舞,坚定立场
草民逆来顺受,面目枯黄
寡居的果木失色
爱情还在酝酿
扎染的天空无语
寻找逃婚新娘——
李强展示出他个人全新的诗的语调,这不同于他的《萤火虫》的调子,也不是他《城里的油菜花》的语感,其诗句式短促有力,六音步的铿锵节奏,并保持歌咏的韵脚,押的是“昂”字韵。诗句“三月来到北方”的错位式复沓设制,以及情感直接又隐含的传达,一并透出了现代的格局和韵味。
在一则访谈中,李强这样表达他的诗的特点:清新,优雅,朗朗上口,特别适合朗诵。并且,他能够背诵自己大多数的作品,甚至透露出他向武汉的码头文化学习的秘密——从“汉口竹枝词”获得诗歌节奏的感应:“六月天气热,扇子借不得。虽然是朋友,你热我也热。”他在意诗歌的能歌颂,对诗歌可读可诵的追求笔者是理解的,笔者曾对他提出了另一面向的考量:新诗与歌词的节奏是不一样的,前者更在于每首诗内在语调的呈现,而且每首诗的语调,这内心的呼吸的节律是全不一样,它的神秘不可统一于固定的节奏范式,它的语调的陌异性全然不同于歌词的调式。
新诗对诗的语调的强调是新诗自90年代以来诗人们的自觉追求,他类似于旧体诗的押韵一样重要,新诗写作者更在意听从诗人的呼吸——瞬间的自然节奏——来安排自己的诗行。诗人们往往通过诗的语调来判断诗作的真伪。在曼德尔施塔姆看来,一首诗开始于声响,开始于他自己所说的“发声的形式模块”,他是借声音来工作的,他骄傲自豪地说他是用声音在写诗,周围的人全是在涂鸦。诗的声音或语调对于他就是灵魂的呼吸与形状。希腊诗人卡瓦菲斯是进入中年才找到自己的声音的,我们读他,就是被无处不在然又无影无踪的月光般不可模仿的独特语调所迷恋。
李强近年来开始专注于诗的各种写法,他的“写什么”似乎不成其问题,他有着层出不穷的要写的东西,在如何写这个问题上,他自然地想着招数,甚至通过后者来激活前者,让更多的内容呈现出来。比如他在意的近作《小苏》(参见李强访谈录),写的是什么,又是如何在写呢。
在这首诗中,诗人力求用纯客观的笔法来呈现小苏的命运感,作者力求不动声色地描述(虽然有时站出来评议,比如倒数第四行和第五行)一个人的偶然论反对“街上的人说错了”。诗人写的什么,这个语言中现实是要靠“如何写”来透显的,仅用平易叙事似乎无法获得诗性空间的营建。一首诗如何写的技艺方式要有多种“如何写”的形式感来支撑的,不然语言的现实停留在平面的单一处境里,诗的张力与诗性匮乏会使一首诗停止其生成。
这首诗让笔者想到了爱尔兰诗人西尼写他弟弟之死的诗《期中假期》,诗人写他的弟弟被撞死,是对童年弟弟之死的回忆。西尼也是克制着叙事,诗人隔了多年的时空来叙写这个事件的,他的叙事的结构是精心布局的,他的情感传达是层层推进的,诗人没有一句评议的句子,只有最一句单独成一行,与前面的每三行一节构成反差。
四英尺的盒子,一英尺代表他一年的寿命。
诗的最后单独一句看似描述,其实是剧烈的抒情,并且与诗的前面构成出反差和张力,它们互动呈现出诗的强烈情感和不动声色所表现出的效果,让人释卷时测量诗性空间营建和情感如何得以传达的技艺。一首诗的语言的空白,无语和结构的布局和句子的安置等等共同在“如何写”中来达成对诗性“写什么”中呈现,它们二者几乎是妙合在一起。
我们读一首审美效果完好的诗作,往往并不是在意它所谓的写什么,而是关注诗人如何在写,他动用了那些诗艺手段。后者是如何建构或呈现诗性空间,二者又是如何水乳交融一体的。是啊,它们本来就是一体,如何能拘泥于二者的分别呢。
在此展开而言,如前文第一章后一部分所述,汉语新诗写作者大都从译介作品获得了他们学习诗歌如何写的技艺,甚至找到与他们写作相对应的新诗文本。新诗写作者们从译介作品中不断获得其新的写法来丰富自己的表现方式。汉语中的里尔克、艾略特、奥登、弗洛斯特、西尼,影响了一代代中国诗人,启发他们的创作,或者说我们从新诗作品不断自我更新的迹象可透析出一代代译介的诗作如何转化为汉语新诗文本的基因。
华兹华斯在《抒情歌谣集》中这样论述:诗是强烈情感的自然流露。诗起源于诗人在平静中回忆起来的情感。他强调诗人这个创作主体因素,就是说抒情诗形成于与诗人的情感,且是强烈的情感,又是在日后平静的回忆中呈现出来的。艾略特则以为宁静中回忆出来感情是一个不精确的公式,在他看来诗不是感情的也不是回忆和宁静,诗是许多经验的集中,是由营建的诗的结构发生出来的,或由诗人心灵的一条白金丝化合出来的。诗何以产生,确实关涉到诗人与语言的合作。在卡西尔看来,艺术不是对现成的实在的单纯复写,而是对实在的发现。艺术不仅仅涉及情感,且将艺术当成一个客体。一个伟大的抒情诗人有力量使我们朦胧的情感具有确定的形态。就是说,艺术是第二自然。具体点来讲,情感本身成为了一种构成的力量;艺术品是一个实在的形式结构,一个符号系统。一首诗的内容不可能与它的形式——韵文、音调、韵律——分离开来。创造者的情感隐现在一个构造物之中。
在每一首抒情诗里,主体与客体,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往往是通过主体回复到自我的精神的中介。这个中介就是语言。抒情诗退回自我,发掘自我,远离社会的表层。通过诗人,外部的存在演变成创作的冲动,语言成了此过程的媒介。在语言的最深处,抒情诗与社会联系在一起。作为诗人的李强,通过自己的诗学实验,渐渐地从粗放的社会学转向独立自持的本体诗学,抵达抒情诗的本质。对切身生存经验的体会,对外部现实进行着诗学的软处理,或者说,他迷恋诗歌在其中倾注不可估量的心力,欲望着搭建他个人的城堡。也可以这样来表达,一个伟大的诗人也是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他距离现实非常之近——内心装满了现实;他是一只从泥土中生长出来的“蝉”。通过他的诗学实践,渐渐理解,诗人面对的只是达到语言目的之手段。他的目的是诗。是的,没有直接的路从文学通向生活,也没有直接的路从生活通向文学。对一个写作者来说,诗,它是独立的,它本身就是生活。诗人史蒂文斯这样表述过“随着年龄的增长,从自身经历中采撷诗歌与纯粹的诗歌写作是两码事”。他还有一句话说得更彻底:生活是文学的反映。
几乎所有的诗人强调抒情主体的诚与真,而这个抒情自我是随着社会变化、文化熏陶、制度规训、自身努力等改变而不断变化的。抒情主体面临着自身的分裂、混乱,从自为自在到分裂意识的发生,从诚实的灵魂到分裂的意识。这是精神的进步,自我的拓展是艰难痛苦又反复的过程;而且诗主体自谓的真实与真诚,如何构成诗境的真实与真诚,成为诗境的一部分,这也是个重要话题。如何审视自己的情感和文字,让自己的情感(真实性)进入词语之中,化为词语而存在。只有进入语言,通过了诗艺真实性规则审查的诗句所体现的作者的真诚,才会成为诗意的真实和真诚,才会达至感动读者的效果。正如庞德所说:“我相信技巧,它是对一个人的真诚的考验。”这种真诚意味着学会反思的谦虚,自我在技艺面前领会到的谦虚。
注解【Notes】
①《谈新诗》、《在北大课堂读诗》分别见于人民文学出版社1944年第1版,长江文艺出版社2002年第1版。
②徐敬亚:《中国现代主义诗群大观》,同济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1版,第7页。
③李强:组诗《庐山记忆》,载《人民文学》2016年第6期,第45页。
④[爱尔兰]西莫斯·西尼:《西尼诗文集》,吴德安译,作家出版社2001年版,第230页。
⑤[英]艾略特:《传统与个人才能》,王恩宇编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12页。
⑥[德]卡西尔:《艺术在文化哲学中的地位》,选自《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伍蠡甫、胡经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下册第256页。
⑦[德]阿多尔诺:《谈谈抒情诗与社会的关系》,选自《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伍蠡甫、胡经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下册第189页。
引用作品【Works cited】
[1]张曙光:《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5页。
[2][德]海德格尔:《海德格尔诗学文集〈语言〉》,成穷、余虹、作虹译,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8页。
[3][美]特里林:《诚与真》,刘佳林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1页。
Title: The Geographical Transition and Linguistic Reality of Chinese New Poetry — A Study of Li Qiang's Poetry Writing in the Context of New Poetry
Author: Liu Zongxuan is a researcher of Research Center for Wuhan Language and Culture, Jianghan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modern Chinese poetry.
This article discusses about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ntemporary poetry ,the new situation and trend, the change of language and form of new poetry.It places Li Qiang's writing in his context, discusses about the poet's style and expression, by comparing the difference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texts, the question of "what to write and how to write" is illuminated and the form of poetry and poetic language reality is stressed.
Contemporary poetry Li Qiang Poetic element New sensibility Tone of new poetry
柳宗宣,江汉大学语言文化研究中心,研究方向为中国新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