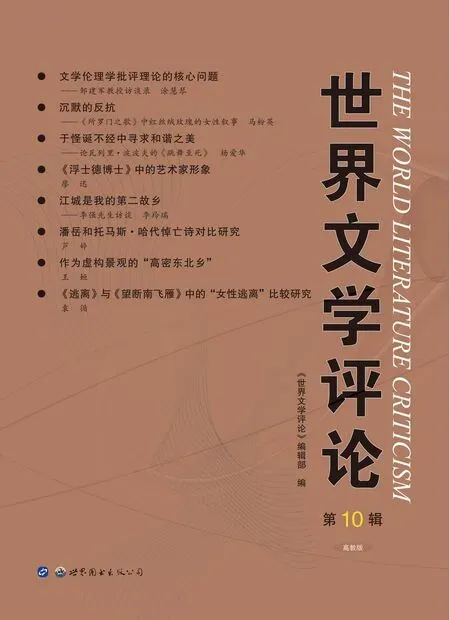痖弦:在日常状态中抵达诗艺与诗意的和谐
2017-11-13薛述方
薛述方
痖弦:在日常状态中抵达诗艺与诗意的和谐
薛述方
痖弦是台湾诗坛的著名旗手之一。他的诗有借助视觉系意象、通过有意味的形式构造以及语言的个性化雕琢再现日常的生活状态,描摹一种不可名状的情绪,从而实现有节制地传达人生体悟的特点。他有意避免探讨最深刻的生存之思和存在之故的哲学命题,转而选择直面生活的琐碎无常,在生活本身的常态中寻找诗意的来源。通过形式和语言的艺术构造,他的诗具有温和细腻的风格,呈现出诗意与诗艺在内在情感经验和外在形式方面的多重统一。
痖弦 日常状态 经验 语言 观念
上个世纪中期以来的台湾诗坛异彩纷呈。一批从大陆迁来,有着学者、诗人和士兵等不同身份的文艺青年带着对自我身份和文化认同的焦虑,书写了大量既带有浓郁台湾特色又蕴含着乡愁忧思的诗歌。痖弦即是这类诗人的代表之一,他出生并成长于中国大陆,从军之后随部队来到了台湾。自1953年在《现代诗》发表处女作《我是一朵静美的小花》,并于次年同洛夫、张默创办“创世纪”诗社开始,痖弦就开启了其长达十余年的诗歌创作生涯。他的诗歌,不以数量取胜,而专注于诗艺的独具一格,尤其在对诗歌语言的打磨、形式的探索、诗意的传达以及理论的革新等层面进行了大量实践。痖弦认为,这些有助于表达个人情感,而通过个人的情感表达,也就能恰当地解释社会现象甚至传达社会意义:“我始终坚信文学是质的问题,不是量的问题……文学是从殊相到达共相的过程,不管你写什么,点或面的,局部或全体的,个人的民族的,只要写得好,都有社会意义。”
一、经验:对日常状态的重视
由于对个人经验和内心感悟的重视,痖弦的大部分诗歌并不执着于大是大非的评判,也不感慨于人生际遇的苦闷和生存的困境,甚至都不在生存的终极命题和对生命的深度关照中下工夫。他的诗作,要么在生活的日常琐碎中发现闲趣,要么抒写一地鸡毛的芜杂,或者通过诗歌本身的语词和形式表达一种情绪、描摹一种状态,甚至只是在文字的游戏中流动地展示一种意念。痖弦的诗,很少有跌宕起伏的情节或者酣畅淋漓的宣泄,似乎尽力保持着一种克制的情绪。这样的诗歌,无论在政治性压倒文学性的50年代台湾社会,还是热衷于对个体生命进行终极追问的当下,不免显得过于质朴纯真,甚至会被人扣上无聊之作与不够深刻的帽子。然而这种避开启蒙式的书写和说教式的宣言,从我们习以为常的逻辑中找寻写作的盲点,直观地展示生存本身和生活的日常,继而创造出情感共鸣的做法,又何尝不是一个优秀诗人才华的展现?痖弦是拒斥那些过度社会化的诗歌的,他说:“社会意义是文学的重要品质之一,但却不是唯一的品质;社会意义时批评文学作品的标准之一,但却不是唯一的标准。”(242)可以说,痖弦书写的那些优美而别致的文辞,那种不疾不徐的叙事态度,恰恰是为了在那些被政治塑造得激烈无比的抒情语言之外,探索出现代诗在形式和内容方面更多的可能性。他的诗歌特点也蕴含在了这种探索的过程当中。
在传达痖弦诗歌此种神韵和气质的方面,《给桥》算是做了很好的示范:
常喜欢你这样子
坐着,散起头发,弹一些些的杜步西
在折断了的牛蒡上
在河里的云上
……
整整的一生是多么的、多么的长啊
纵有某种诅咒久久停在
竖笛和低音萧们那里
而从朝至暮念着他、惦着他是多么的美丽
想着,生活着,偶尔也微笑着
既不快活也不不快活
有一些什么在你头上飞翔
或许
从没一些什么
……
这首诗起笔即为全文定下了一个民谣式的基调:描绘着一场在旷古幽兰里清新脱俗的恋爱。但作者并没有任由炽热奔放的情感肆意地宣泄这个故事,而是以他惯常的手法反复咏叹,将一颗炽热的心化用一种幽眇的情绪缓缓道来:“整整的一生、是多么的、多么的长啊”。在这绵长而又无奈的岁月中,情感的炙热和诗思的幽眇最终合在一起,融汇成了耐人寻味的诗意:“想着,生活着,偶尔也微笑着/既不快活也不不快活/有一些什么在你头上飞翔/或许/从没一些什么。”这首诗并未使用过多华丽的语言,去追求一些更深刻的寓意或更复杂的内涵,只不过写了日常生活的百无聊赖,写个体存在琐碎且困顿的际遇。对于痖弦,诗歌不只是在表现伟大的主题和生命哲思的主题上才能成其为好的诗歌,它也可以用来记录日常生活的:没有英雄式的悲歌,看起来似乎不过是平铺直叙的描摹,好像是什么都发生了,又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而实际上,大部分人的一生都会在这样的日复一日的重复中度过,而一部分人不自知,一部分人通晓却又无可奈何,于是这些真正能对日常生活有所体悟且恰如其分地写出了生存状态的诗歌,显得更加难能可贵。痖弦尝试着对这些日常经验的表达,其写妇人的这几段诗,读来竟颇为有趣:
我太太是一个/仗着妆奁发脾气的女人/……/我太太想把/整个地球上的花/全都穿戴起来/连半朵也不剩给邻居们的女人/她又把一只喊叫的孔雀/在旗袍上,绣了又绣/绣了又绣。总之我太太/认为裁缝比国民大会还重要……
(《蛇衣》)
诗作把普通妇人的心思描绘得活灵活现、很是生动,写的是大部分女性普遍的心理状态,付诸于文字却是惟妙惟肖的表达。这是七零八落的琐碎日常,同样也是真正的生活,更容易引发读者的共鸣。在痖弦的理解中,活着本身并没有那么深刻,它真正的样子便是你看到的那样,而非我们臆想的那样。他的诗通过重复和再现的方式去表达这些散碎的经验,不需要过分的抒情,意在将这些在政治抒情中被板结的日常状态以陌生化的手段表达出来,从而起到打动人心的效果。
二、语言:视觉与节奏的创造
对日常状态的思考,让痖弦开拓出了一片属于他自己的创作领域,但同时也为其写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他既要将个人经验中日常状态的繁多意象拎起来,还要将之统统诗意化,传达到读者能够接受的层面当中去。没有政治规范力的帮助,单独以诗歌之力将个体经验转化为群体感受,这是个不小的考验。痖弦的诗歌最为独到的即是通过对语言和特定句法的使用,达到在有限的语词中表达无限的意义,而这些也是立足于上述问题展开的,他的诗歌的特点大致有三个层面的内容:
首先,特别重视带有视觉色彩的词语表达。这在痖弦创作初期的一些诗歌里表现得尤为明显。他凭借着现代汉语独特的语言优势,利用表意文字内涵的丰富和外延的宽度使得诗歌所表达的内容含蓄又模糊,从而充斥着独特的美感。以《远洋感觉》为例,运用大量的颜色和意象来表达晕船的感觉,短短十七行字即让读者有一种身临其境之感。
“哗变的海举起白旗/茫茫的天边线直立,倒垂。”海是“哗变”状,天边线一会儿“直立”,一会儿“倒垂”,一个远镜头白茫茫一片跃然纸上,视觉效果十分分明。“晕眩藏于舱厅的食盘/藏于菠萝蜜和鲟鱼/藏于女性旅客褪色的口唇”,晕船是远洋航行最常见的症状,为了恰当地呈现这种情况,诗人将它至于食物和正常的生活状态中,一切都被影响了。“时间/钟摆。秋千/木马。摇篮/时间/脑浆的流动,颠倒/搅动一些双脚接触泥土时代的残忆/残忆,残忆的流动和颠倒。”这样的长途远洋,时钟上时间的流动往往能给人强烈的感受,看着指针的摆动,反复出现的都是“时间”的概念。身体的感觉太过于私人化,但视觉的意象却是公共的,整首诗的处理实际上是一种化私为公的方法:“时间/钟摆。秋千/木马。摇篮/时间/脑浆的流动,颠倒”,痖弦巧妙地选取了一些动态的意象,借助于错位的比喻和疏离的象征来打通读者的类似经验,将原本不可传达的身体体验转化成了视觉的冲击力。于是,痖弦就用这种方式来将晕船的感觉生动表达了出来。
利用视觉色彩和浓重意象的另一个好处,即能够通过一些蒙太奇式的意象转化,让全篇达到一种诗意化的境地。《非策划性的夜曲》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诗歌从诗歌标题开始就预示着内容的构想不凡:“夜在黑人的额与朱古力之间/黎明还没有到来/雨伞丢弃各处/月光老去而市场沉睡/房屋的心自有其作为房屋的悲苦/很多等候在等候/久久望着/来时的路/死者的玻璃眼珠”这样的句子在诗中随处可见,荒诞不经的想象和充满寓意的夸张,很多时候都是通过天南海北视觉意象的迅速切换来表达出的。各种意象之间变幻莫测的组合方式,让全诗显得隐晦深涩。为了营造奇特的视觉效果,痖弦运用了大量错位的比喻和疏离的象征,这些一方面让诗歌的直观体现远离着生活经验,却在另一方面给了我们情感和趣味上的无限接近,提供了诗歌释读的多种可能性,创造了丰富的诗歌美学。在阅读过程中,我们有时甚至不知道他用这些看起来毫无关系的意象组合到底想说什么,但这些组合却十分耐读,很多时候也不会显得违和,甚至还会让我们对作者的想象力感到惊叹。
其次,痖弦擅长于在写人与状物中刻画其典型性的一面。在人物表现上,上至地位显赫的总统赫鲁晓夫、下至坤伶水夫,常人如教授上校,异态如弃妇疯妇,他均能抓住人物最典型的一面着力进行描写,从而产生出诸多形象鲜明的诗歌,刻画出一些极能体现人物身份特点的典型人物形象。《疯妇》中站在“疯妇”的立场上通过第一人称表现这个妇人的语态、神情来展现作为一个非正常状态下妇女的样子,“你们再笑我便把大街举起来/举向那警察管不住的,笛子吹不到的/户籍混乱的星空去/笑,笑,再笑,再笑/玛利亚会把虹打成结吊死你们”,一个泼辣易怒的妇人形象跃然纸上,在《弃妇》中,这个女子几乎对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保持距离,对于一个被遗弃了妇人而言,她们的一整个日子都是灰暗而忧戚的,甚至到了一种病态的悲观之境,“她已不再是/今年春天的女子/她恨听自己的血/滴在那人的名字上的声音/更狠祈祷/因耶稣也是男子”。今年的春天与往昔无异,然而女子已不是那个女子了。她怨恨一切事物,自己的,男人的,甚至是耶稣,只因为耶稣是个男子。诗作突出“怨”的一面,将整个妇人的形象化繁为简、化琐为常,并通过这个典型让诗歌中的形象进入到我们的日常所见,从而激发出我们对人物及其情感的共鸣。在有限的诗歌空间中表现人物形象,往往仅能依靠只言片语去传达,于是对诗人观察力的考验则显得尤为重要。
再次,痖弦极为重视诗歌语言中的节奏、语词速度和旋律。诗歌的内在速度直观地反映了诗人的文化气质和所要表达的情感状态,是诗歌独有的一种诗学气质,代表了诗歌本身的美学特点。而这种美学中最难把握的是时间等象征性的虚景,采用语言的各种变化来构造形式上的诗意本身也是诗歌与时间或者难以表达生命存在之间的对抗。在痖弦的诗歌中,《忧郁》就有着这种混杂着语词上的美感的表达,全诗分为七节,从第一节“像修女们一样,在春天/好像没有什么忧郁/其实,也有”开始,“忧郁”就和春天有了关系,紧接着忧郁似乎进入到春天的生活中,无处不在,带着一种特色的唯美色彩,或藏匿、或夹杂,“我曾在/跳在桌子上狂舞的/葡萄牙水手的红色须瓣里/发现忧郁/和粗糙的苎麻绳子编在一起”,又或者是“傍晚时候主妇们关门/忧郁衔着羊子们的尾巴/进了栅栏/又锁着婴儿的眼睛”,此时的忧郁像是塞满了自己的意识,和我们的正常生活一起构成生活的常态,似乎忧郁是生活的一部分,又或者只是春天的一部分,“四瓣接吻的唇/夹着忧郁/像花朵/夹着/整个春天”。全诗基调平稳而又耐读,在复沓吟咏中走向尾声而余音绕梁,“只有忧郁没有忧郁/是的,尤其在春天/没有忧郁的/只有忧郁”。有学者称痖弦的诗为“甜是他的语言,苦是他的精神”,正如这首诗中,语词的使用无不透出淡淡的缓释感,而描摹的对象却是忧郁,是使人类蒙难的情感状态之一。诗歌本身就是带有韵律感的,通过其内部节奏的把控并传达情绪,同时也考验着诗人的创作。在本诗中痖弦没有单单利用视觉效果的转换来达成目标,还用了一系列充满节奏感的短句来造成阅读的张力。连珠炮式的短句能够加快节奏,伴随着密集的视觉效果转换,让朦胧的压抑气氛更加浓厚,继而增进读者的感受。用诗人的理性通过娴熟的技巧把握诗歌创作的节奏感,痖弦无疑是较为成功的一例。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痖弦诗歌的表达技巧虽然极具特色,却也有着明显的分期:进入到20世纪60年代后,尤其在他创作了《夜曲》、《一般之歌》等诗作之后,痖弦逐渐摆脱了早期作品对语言和形式过分倚重的问题。在之后的作品中,他逐渐弱化文字上的花式和对诗歌旋律的把玩,取而代之的是用聚敛而充实的语词营造更加饱满的诗意。他曾对语言和诗歌的关系做过如下论述:
通常我们说诗是语言的艺术,只能当作语言在诗中重要性的强调;事实上,语言并不是唯一的,绝对的,第一义的存在……决定一首诗诞生的因素,在于内容的情感经验的变化,而不在于形式的语言文字的流动;永远是内在的艺术要求决定着遣词用句,而非遣词用句决定着内在的艺术要求……
(《痖弦自选集》 244)
从创作初期偏重于语言技巧到成熟时期站在诗歌美学的高度进行创作的反思,痖弦试图打破之前所习得的西方现代诗技法对创作的过度遮蔽,从而在语言、诗歌形式和作品本身的艺术表达与诗歌创作者本身的人生经验之间寻求一种平衡。痖弦对诗歌创作的思考诉诸在笔端,在中后期的诗歌创作中产生出了更有力度的作品:“铁蒺藜那厢是国民小学,再远一些是锯木厂/隔壁是苏阿姨的园子;种着莴苣,玉蜀黍/三颗枫树左边还有一些别的/再下去是邮政局,网球场,而一直向西则是车站”(《一般之歌》)。这首诗是常规的一句一景,没有了他之前诗歌中的那种连珠炮式的画面切换,也没有对语言进行扭曲为我们制造阅读的间断,而是平和地直抒所见,在移形换步的所见中折射自己复杂的内心所感,但这样的作品却无疑更显得朴实有质,内容丰富。在诗歌发展的节奏方面,仅是对方位的描述,痖弦就巧妙地运用一些连接词和方位词在各处之中收放自如,诗人到这一阶段,诗艺已经臻于成熟了。史莱夫·贝尔在其著作《艺术》中曾经提出过一个著名的美学观点——有意味的形式,即以独特方式唤起我们审美感情的各种组合、排列。通过对诗歌语言的再创造,诗人已经能比较熟稔地把握语言在诗歌创作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加以创造。相比之前,此时的诗歌则更能贴近于他写日常生活的意图,也能让这个意图更加鲜明地整合进他整个诗歌探索的进程之中。
三、观念:包容与节制
如果说对作者语言的分析更偏向于从读者的阅读感受出发的话,那么对观念的探索则体现了对作者写作意图的思考。诗艺与诗意相关,写作观念的形成也与作者的生活态度紧密相连,如何运用语言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在于作者如何看待生活。相对于诗歌技巧,诗人写诗的观念和态度则是更为重要也更需要被观照的层面。从写作观念的层面来分析痖弦,也更能体会到他的独特性所在,其观念的独特性包含在以下两个层面中:
第一,诗歌中呈现出的包容性心态。对生活日常的重视会让诗歌在意象选取的层面更具包容性,让它不再拘泥于政治派别之选、中西文化之分。像同时代的许多台湾诗人一样,痖弦在创作中也曾醉心于对西方各种文学流派思想的汲取。在语词的使用上,他的诗歌,尤其是前期的诗歌糅合了大量西方现代派的表达技巧。但这些舶来品并不是痖弦所想要模范的对象,他似乎是在汲取的过程中寻求视域上的开拓——无论是意象的选择、文法结构的突破还是对诗句的锻造,他都在试图打破现代汉语既有的语法规则和使用规范。在《红玉米》中,他试图借助锻造出来的新句式来承载更多的内容,然而,不难看出其诗歌创作的真正内核和内在的基本韵律仍然来自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来自于他曾经成长的那片惟余莽莽的北方土地:
宣统那年的风吹着/吹着那串红玉米/它就在屋檐下/挂着/好像整个北方/整个北方的忧郁/都挂在那儿/犹似一些逃学的下午/雪使私塾先生的戒尺冷了/表姊的驴儿就拴在桑树下面/犹似唢呐吹起道士们喃喃着/祖父的亡灵到京城去还没有回来
(《红玉米》)
这是一首以西方印象派的写作技巧所谱写成的诗歌,却有着典型中国传统文化的韵味:诗人选择红玉米作为主体意象,辅之北方的雪、私塾先生、戒尺、驴儿、桑树、唢呐、葫芦儿、棉袍、铜环、岗子、荞麦田……这些共同勾勒出了一幅生气十足的中国北方农村实景图。秋冬季节玉米成熟之后家家户户在自家院子里晒起了玉米,早已经是诗人记忆中的故土往事了,满满的回忆和眷念都在反复吟咏的字词中溢出来,“在记忆的屋檐下/红玉米挂着/一九五八年的风吹着/红玉米挂着”。这些意象都指向了诗人内心更深处的记忆。在痖弦的诗歌中,形式技巧实际上一直是要服务于内心表达的,经过早期的融会探索之后,后期他的创作便越发的纯熟,对西方现代派中形式的吸纳与转化也有助于他在创作中形成一种包容的心态。这种转换与借鉴也让痖弦的诗歌在意象把握与借鉴的方面极具特色,让他在意象选取的层面显得更加多元化。除了将古典意象糅合进西方的表达形式之外,他还创作了在传统文化的内在节奏上孕育着大量外国地名、人名的诗歌。诗句在不同的视觉效果中不断切换,似乎只是意象的堆砌,但其中却不难看出诗人对于世间万物的博纳包容之心。
第二,在一颗包容之心下,痖弦的创作就显得极为克制。这在上文中已有提及,对这个话题继续深究,它同样包含了两个层面的内容:首先是对诗歌表达的克制。这种克制使痖弦的诗歌创作显得精致而讲究:不论是对词句的打磨,还是在句式的变换上,似乎都是精心安排,让人不得不感慨诗人的创作功力。在对泛滥的感性极大程度的克制之后,诗的形式以一种理性而节制的表达展现出来:
我的心灵是一只古老的瓶
只装泪水,不装笑涡
只装痛苦,不装爱情
如一个旷古的鹤般的圣者
我不爱花香,也不爱鸟鸣
只是一眼睛的冷漠,一灵魂的静
……
《瓶》(《痖弦诗集》 227)
全诗一共六节,每一节均有三行,在形式构造上错落有致又不失内在韵律的构造和情感表达的饱满。前面两节首先表明身份“瓶”,随后用两句“只……不……”的句式展现出“古老的瓶”的心理状态,这是一个古老地充斥着故事的瓶,没有年轻时候的激情和青年人的放荡不羁,“不爱……不爱……”,“只是一眼睛的冷漠,一灵魂的静”,刻画出一个饱经岁月磨蚀的心灵年迈者形象,在接下来的两节中诗人交代了这种状态的由来,“一天一个少女携我于她秀发的头顶/她唱着歌儿,穿过带花的草径/又用纤纤的手指敲着我,向我要爱情!”然而“我,我本来来自那火焰的王国/但如今我已古老得不能再古老/我的热情已随着人间的风雪冷掉!”爱情求不得,心灵逐渐钝化龟裂,进而“丁丁的迸破”。诗歌的句子在衔接过程中显得温和而圆润,在句式的构造中通过动名词的联合使得句式显得温婉而又多情。正如作者自己所说:“一件完成的艺术品,读者在表面上,看到的或许只有感性的存在,而实际上感性必须有隐形的智性为骨架才能形成,才能避免感觉的泛滥。”(《痖弦自选集》,234)痖弦的每一首诗在句式的构造上几乎都有着匠心独运的设计。大部分句式在成诗的过程中即定下来全诗的基调,从而影响诗歌的节奏和声律美学,尤其在诗思愈发泛滥的地方,愈能见到诗人有意为之的克制。
其次是情感的克制。如同贝尔所言,正确的形式是受感觉支配的。在痖弦的诗歌中常会见到一些双重否定的表达,比如“不爱……不爱……”、“既不……也不……”等,这种否定形式会避免诗歌的单一抒情,从而让情感复杂化。而这种表达方式,对于诗歌创作而言,则源自于创作者个人的体悟和经验的表达。琐碎的日常状态是痖弦所要表达的对象,他需要为其找到一个正确的表述方式。而所谓形式的“正确”,对读者而言,体现的是一种审美上的满足;对于创作它的艺术家而言,则意味着对某个概念的完全认识和对某个问题的完美解答。(贝尔 45)受贝尔这个观点的启发,我们可以从痖弦对其生活状态概念的理解中去审视他的克制观:如前文讲,既然生活经验不像想象中那么明确,它可能是琐碎的、芜杂的甚至是一地鸡毛的,那么在表达中,我们就不能用自己的情感去试图统摄它,因为统摄很可能会造成简化。面对如此问题,表达需要谨慎,情感抒发更需要谨慎,而谨慎就会显得克制。
结 语
基于对日常生活概念的理解以及对日常状态的表达,痖弦不断地完善自己诗歌的表达技巧:从他在语言层面对视觉性、典型性和格律感的追寻,到诗歌观念中对包容性和克制性的思考,都能看到他在诗艺上的探索和努力。随着这些创作理念的不断清晰和成熟,痖弦的诗歌发展经历了一个从吸取借鉴到自我定位、再到探索新知的一个全过程。在诗艺日臻成熟的过程中,诗人逐渐悟出来诗歌的创作内核:“任何诗人写作初期总免不了对形势的沾恋,而当她一旦达到美学上的成熟,他便应该扬弃语言的皮相的游戏,自作品整体性的把握上追求更高层次的说服力……”(《痖弦自选集》 244)对诗意内核的思考,直接决定了诗歌在语言和观念上的外在呈现。只有金玉的外衣,却没有成熟的诗思和诗艺作为依托,依然不足以支撑起一个饱满的诗意空间。只有基于诗人一定的基础经验认知,在积攒了足够的诗思基础上,通过多向度的观察和体悟达到诗歌内在的平衡,建立起诗人的自觉,才能达到经验、语言和观念的和谐,从而真正地借助于皮相的手段恰如其分地呈现诗意。
张默在《中国当代十大诗人选集》中曾经对痖弦的诗歌做过比较全面的评价:“痖弦的诗有其戏剧性,也有其思想性,有其乡土性,也有其世界性,有其生之为生的诠释,也有其死之为死的哲学,甜是他的语言,苦是他的精神,他是既矛盾又和谐的统一体。他透过美而独特的意象,把诗转化为一曲温柔而具震撼力的恋歌。”(萧萧 141)这个评价无疑是对痖弦成熟期创作的一个肯定,表明了他提倡的基于对日常状态的书写所呈现出的复杂性逐渐被他人所认可、所接受。于一个诗人而言,痖弦的探索历程极具代表性:对西方现代诗表达技巧的学习固然有助于写诗,但只有立足于个体经验以及对生活的理解,诗人的诗歌创作才会具有特色,也只有在一定艺术思考和人生经验的基础之上产生的形式意味,才能达到诗思和诗艺的互动和谐,创造出有意味的诗歌。
注解【Notes】
①痖弦:《痖弦自选集》,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7年版,第242页。以下引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注明。
②痖弦:《痖弦诗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1页。以下引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注明。
③萧萧:《瘂弦的情感世界》,载《中外文学》1979年第8卷第4期,第141页。以下引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注明。
④[英]克莱夫·贝尔(Clive Bell):《艺术》,周金怀、马钟元译,中国文艺联合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43页。以下引文只标注页码,不再一一注明。
Tittle: Ya Xian: Searching the Balance Between the Poetic Experience and the External Form in Daily Status
Author: Xue Shufang is the College of Arts and Literature, Wuhan University, specializing in the critics of contemporary authors and works.
Ya Xian is one of the most famous standard-bearers of poetry in Taiwan. Carved with visual system imagery, the signi fi cant form, and the individuality of language, his poems reproduce the daily life and depict a kind of unexplainable feeling. Therefore, his poetry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onveying life in moderation. He intends to avoid exploring the deepest thinking and the philosophical proposition of existence, and turns to confront the trivial life, fi nding the poetic source in the normality of life itself. Through the artistic structure of form and language, his poetry forms a gentle and delicate style, which achieves the multiple uni fi cation of poetic and poetic art in the inner emotion experience and external form.
Ya Xian daily status experience language concept
薛述方,武汉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为当代作家作品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