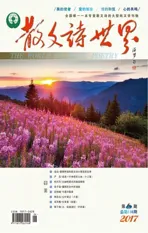今生遇到的所有坝子都是我的家乡(八章)
2017-11-13四川余元英
四川 余元英
今生遇到的所有坝子都是我的家乡(八章)
四川 余元英
今生遇到的所有坝子都是我的家乡
我的家乡是一座叫作“吊坝”的村子。
她像一个无限放大的椭圆形鸡蛋,稳稳的放在川西高原山脉的底端。在这里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用自身的营养,喂养生于斯长于斯的人和动物、植物。
在吊坝,除了房子不能种庄稼,其余的地方决不让她空白着发呆,就算是石头,也要包裹一层青苔。
我最喜欢看记忆中乡亲们种庄稼时的场景——
三月,当雪线由山脚撤退至山顶,大地就露出她的慈祥。
那时耕种还用牦牛,男人们在前面犁地、聊天、也唱山歌给牛听。女人们在后面撒种子、撒肥料、掩土,种土豆、青稞、玉米,也种遍地的欢笑……
乡亲们点缀在一望无际的沃土上,像极了在吊坝这篇大文章上落下的标点,有的是逗号,有的是感叹号,有的是问号,有的是句号。
而我是生在吊坝的省略号,为了看到山脉外的景,早早地离开了她,但我无时无刻不爱着她啊,以至于今生遇到的所有平整的坝子,都忍不住叫上一声“家乡”!
一条名叫黑河的水流进我的血液
一条河流有了名字就有了命。比如家乡的黑河,它的母亲是高原冰雪,子女是生活在沿河岸的村民,作为子民的我们用它灌溉庄稼,也灌溉自己。
黑河清绿,清绿如河岸白杨的嫩芽,在河水缓流处可以抓住飘进河底的云。我常常怀疑为河流起名的人必定是缺乏正义之人,否则,怎会黑白不分,颠倒是非?
面对黑河时,总有很多记忆,湿漉漉的爬上来。小时候,伙伴是一条没有性别的鹅,可以漂浮水面,也可以潜底。母亲的责骂惊扰垂在河边的柳枝,柔软地拍在身上没有疼痛,只有阳光的余温。
我和妹妹喜欢捞鱼,也捞走一些河水,沙滩上有我和妹妹用童年喂养着的鱼,陪我们长大,也陪岁月老去。
那些失去棱角而算不上石头的鹅卵石,是我和妹妹数学算术中一直宠爱着的宝贝,只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生活的染色缸里,我也渐渐沾染上鹅卵石的习性。
和老屋一起老去的父母
新年这根绳还是没能拴住一家人,能挣扎的都朝着既定的方向挣扎。多少次劝父母和我一起进城住,老人摆摆手,总说老屋老了,也需要人陪。
就这样,老人陪着老屋,老屋也陪着老人。
老人像一座电力不足的钟摆,从老屋的左边晃到右边,半晌,又从右边吃力的摆到左边,搀扶着把日子过成比日子更长的年。
闲暇时,老人喜欢给和自己儿女同名的小鸡说话,说子孙的乖巧,说邻里旧事,也说一些遥不可及的记忆。
夜逼近前,老人习惯与老屋相视而笑,这默契就如黎明安放在黑暗之后那么自然。
可谁能折弯岁月这把镰刀,不让它割掉嫩苗,也不割走枯草?
行走在家乡的夜空
在老家晚饭叫作“夜饭”,忙碌的农人常常用星星下饭,月光下酒,说一些家长里短,消除一天的疲惫。
习惯了城里的习惯,饭后我必定要散散步。
夜晚的村道没有车辆,只有月亮从路面走过,慢慢地,扬起的灰尘已恢复了平静。
地边飞舞的萤火虫是还没有升上天的星星,一眨一眨努力向夜空飞。
路过邻居的家门,有看门狗一直在朝我狂吠,主人见是我过路,边向我打招呼,边骂着狗的无礼。我并没有怪罪,那晚确实藏着一个秘密:沿着朦胧归来,我顺手牵走了连绵的山影和家乡的宁静。
等我回到家,父母早已睡去。黑夜与白天对于他们,仅仅是一觉瞌睡的距离。
愿世界温柔待你
疯长的竹林低矮了土坯房,像爷爷的驼背,日渐弯曲。
雷雨是土坯房最大的克星,雨来之前,必须将睡梦搁置在夜之外。
父母外出后的日子如一枚雨点,马不停蹄地从遥远赶来,像一个词语击中心坎。这时的你比任何人都匆忙,上学,照顾弟妹,喂鸡,喂猪,也喂养期盼之后的期盼。
孩子啊,愿世界温柔待你,愿过往你家门的风轻轻吹,别叩响了久未响过的门;愿梦与现实是对孪生姐妹,别让现实的眼泪沾湿梦里的笑容。
孩子啊,坚强吧,别总是朝着父母离开的方向张望,那个离去的方向早已被成千上万的孩子们,望成了小剂量的毒,每望一次,思念的囊肿就增大一寸。
乡亲,流淌在乡间的情
能喊出我乳名的,不是父母就是乡亲,每喊一声,我的心就柔软成迎风的经幡,向善的方向飘飞。
在吊坝村,乡亲们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名字,出了村庄,他们的名字都叫吊坝村的。
乡亲,是生活这条河床里,相互搀扶着向前奔流的河水。张家接媳妇,乡亲们系起围裙择菜、办宴席、闹洞房,也揣走一些喜庆。李家死了人,乡亲们自发抬棺木、打理后事,也哀伤同样要走这一步的自己。王家五保户是一位多病残疾的老人,乡亲们轮流帮种地、洗衣,也转动经筒为他祈福。
离家远了,喜欢在人群中搜寻乡亲的脸庞,因为每一位乡亲都能还原同一个故乡。
乡音,一生也听不够的天籁
人们常说,在春天种一颗名叫希望的种子,秋天就能如愿收获参天大树般的幸福。
2012年的春天,我把我这粒来自吊坝的种子种在他乡的土壤,认沃土当母亲,认阳光作父亲,努力挺直脊梁,向上生长。只是,异乡的雨水太多,为了克服水土不服,必须把家乡搁进我的梦里;为了防止溺水身亡,心里必须装着家乡的太阳;为了防止跌倒泥中,手里一定要拄着乡音的拐杖,为自己探路,也治疗摔倒后的伤。
多年后,终于收获了两个自己,一个叫躯体,另一个叫乡音。
怕黑的人,站在最深的暗里
夜追随夜,昏黄的路灯与黑对峙,偶有经过的车辆或是破碎的酒瓶,才会打破这僵持的局面。
黑,是一块海绵,柔软。柔软成父亲的轻咳,母亲的呼吸。我喜欢用乡音这滴水饱满黑这块海绵,黑就家乡一样沉甸甸了。
夜里,我憎恨蛐蛐儿的假慈悲,一声两声,试图用村庄抄袭月光,让漂泊的我误以为还停留在儿时看守过的玉米地。
我是一个怕黑的人,可我始终站在最深的暗里,抱着温暖的黑,抵挡酒杯中虚拟的真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