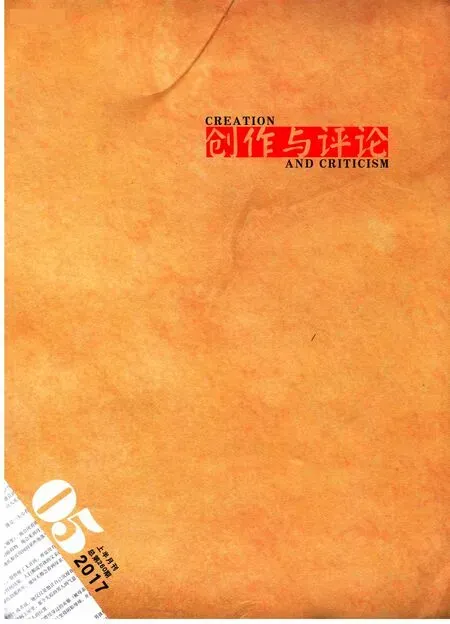儿童视角与方言叙述
——论张新科小说《树上的王国》
2017-11-13刘进才
○ 刘进才
儿童视角与方言叙述——论张新科小说《树上的王国》
○ 刘进才
在向历史的纵深处开掘方面,作家往往比历史学家更为细腻和丰富。这些年来,当代作家对特殊时期的历史一直保持了关注的热情和叙述的兴致,而究竟应该如何叙述,不同的作家自有各种不同的叙述方式。张新科的长篇小说《树上的王国》则以纯粹的儿童视角与原汁原味的方言叙述,为我们形象地展示了一个村庄的特殊时期的日常生活,一滴水可以映照一个世界,一个小小村庄上演的人和事展现了特殊时期宏大历史的冰山一角。
一、儿童视角运用与原生态生活的还原
《树上的王国》情节并不复杂,小说叙述了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一个叫槐树湾的乡村,在支部书记刘都堂的带领下成立豫剧业余剧团并到县城文艺汇演一事,故事围绕剧团人员的选拔、豫剧的排练与精彩演出一一展开。小说故事的演进是通过第一人称“我”——一个小学生的口吻加以叙述,由此穿插了小学生与他们的数学老师肖成功之间的美好故事,以及肖成功与业余剧团女演员魏莹之间美丽动人却以悲剧收场的凄美爱情故事。肖成功暗恋着魏莹,非常喜爱听魏莹每天晚上在自家院子演练豫剧,于是带领四个小学生爬上魏莹家后院高高的洋槐树,在一个荒诞混乱的年代,四个小学生却在洋槐树上聆听着肖成功讲述的美丽童话,陶醉在“树上的王国”。
与成人的眼光不同,儿童眼中所映照的世界没有太多的修饰和过滤,儿童视角叙述更能原汁原味地传达出社会生活的真实面向,这是作者采用儿童视角的优越性和独到性所在。儿童往往对世界充满着无穷无尽的好奇心,小说叙述者“我”对刘都堂自制香烟的细节也颇感兴趣:“刘都堂抽‘土炮’自由一套,先是用右手的小拇指从两个嘴角边将半干半湿、半稠半稀、半白半灰的吐沫刮下,然后均匀地沫在‘土炮’较细的一端,抹的过程也十分讲究,像木匠刷油漆似的得先后抹上三遍。抹过第三遍片刻,刘都堂噘起紫色的下嘴唇,轻轻地把五寸长的‘土炮’贴在了上面,奇迹出现了,粘在嘴唇上耷拉着的‘土炮’竟然不会掉下来。”
这是一个儿童眼中的一个日常生活细节,逼真而传神,只有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才会有如此清晰深刻的历史记忆,小说中诸如此类的细节俯拾皆是,如对李天栋手拿瓦刀娴熟的砌墙功夫的描写、对瘸子吴力耕白面袋子长衫的描写,这种大量的民间生活细节不但营造了往昔岁月浓厚的生活氛围,也显示了作者细密精深体察生活的功力,增加了文本的可读性和新奇感。
小说中不但运用儿童视角展现原生态的民间日常生活景观,也通过不谙世事的儿童的眼光冷静地打量那个特殊的年代。由于小说采用了“儿童视角”,“我”作为一个冷静的观察者,在貌似平静客观的叙述中展现了“非常时代”生活中的怪诞和滑稽。儿童是社会政治生活的边缘人和旁观者,他们的年龄和智力水平不可能直接参与到成人的政治生活中来,当然,对于社会政治生活的荒诞也不可能有太多认知。然而,正是儿童这种天真无邪的不解的目光引领读者看破了特殊时代的荒谬。
事实上,在任何一个时代大潮中,每一个人都不可能只是一个超然物外的时代高蹈者,要么站在时代的风头浪尖成为时代的弄潮儿,要么被时代的风浪所吹打、裹挟乃至吞没。小说中的儿童们也是如此,随着小说故事情节的演进,越到后来,儿童们越是积极主动参与到成人世界的生活当中。在那个不堪回首的荒谬岁月,正是在肖成功《格林童话》的熏陶之下,儿童们才不至于一味模仿成人世界的残忍和冷漠,而是一步步被童话所塑造,变得得机智勇敢、正直善良,正是有了美丽的童话,在荒诞的年代里却仍存温暖和美好,黑夜并没有完全遮蔽孩子们善良诚实的眼睛,他们却在漆黑的时代散发着美好人性的灵光。儿童们都知道自己的老师肖成功和饰演《朝阳沟》中银环的魏莹私下相爱,当“我们”几个小伙伴得知一位县领导的儿子要托人做媒为魏莹提亲,“我”则大胆地宣布了魏莹和肖老师的相爱,其他几个也应声附和,幸免了让魏莹“一朵鲜花插进牛粪里”的结局。孩子们开始以美好善良的童话世界对抗成人世界的丑陋和不公,小说写到“我”母亲在资格、能力和诸方面优秀的条件下却失去了提拔任职的机会,“我”却给愤愤不平的母亲讲述两个王国的童话故事感动和说服了母亲。
在有童话的世界里,“我”和伙伴们生活得有滋有味、情趣盎然,童话给了孩子们在灰色世界中七彩的斑斓,也塑造了孩子们的正直友爱、诚实勇敢的优秀品格,他们把自身幻化成了格林童话中的青蛙王子、忠实的约翰、聪明的乐师、森林中的猎人等英雄勇士。当肖成功老师的豫剧戏评被批为资产阶级的洋词怪调,以致取消了他的班主任工作时,孩子们便模仿格林童话中的方式,对这一事件的幕后人物夏全球采取了“四猎人擒野猪”的惩罚。当他们发现公社杜书记对城市来的漂亮女知青心怀不轨的苗头,便灵活运用格林童话故事中的《狼和人》《强盗新娘》和《小红帽》等情节保护了女知青避免了像小红帽一样被“狼”诱惑和吞噬的命运。儿童视角叙事,既可展现儿童眼中的外在世界,也可描述儿童自身的生活情趣和丰富内心。从这一层面而言,《树上的王国》也是一部成长题材的小说类型,讲述了孩子们在童话的感召下心智和灵魂健康生长的故事。
由于儿童对于外在世界处处充满好奇心和探究的勇气,作者在采用儿童视角叙事时往往以“被发现”“被窥视”“被跟踪”的叙述方式推进小说情节的演进。如肖成功与魏莹之间的相爱均是通过儿童跟踪和寻找肖老师发现的,儿童们追随肖成功的过程是受肖成功童话故事的感召,也是向真善美世界的追求,树上的王国是与地上的残酷现实相对抗的乌托邦世界,“树上是我们的王国,也是肖成功的王国。”“地上的戏曲”与“树上的童话”形成富有意味的对照,槐树湾业余剧团每次演出总能出一些不大不小的篓子:上演《红灯记》中由于后台没能配合好台上游击队员及时“压响火炮”,以致让台上的“鸠山”没能“枪响人亡”,作为一种演出事故,那位砸“压炮”的人被判了三年徒刑。“业余剧团”演的戏曲是政治规训的产物,而“树上的童话”则是理想的乐土,展现的是孩子们和肖成功无忧无虑的世界。
小说中不时呈现着寻找的主题模式,回荡着追寻的声音。《树上的王国》尽管以儿童的眼光还原了特殊时代的政治生活的残酷,但在儿童的世界里毕竟有“树上的童话”和美好的记忆,拉开久远的历史时空距离,即使儿时的苦痛在回忆的目光中也变得异样的快乐,时间的流逝总是带走了美好的往昔,过去的一切难以追寻。演戏上台前喜欢抽两口烟提神的栗贵昌已经卧床不起,杀猪的马腾子死了,孩子时的玩伴吴小锁意外地死在了坍塌的砖窑洞里,张明亮则操起了炸爆米花的营生……世事多变,白云苍狗。多年以后,当“我”因姥姥去世重回故里,得到了魏莹女儿转送来的《格林童话全集》,而物是人非,盛景不再,魏莹的女儿已经成了槐树湾集上有名的“哭丧者”,曾经年轻美丽的魏莹已老得不成样子,一辈子的戏到了曲终人散的谢幕时候了。美好事物的失落总会让人黯然神伤,但人们也总是不放弃继续寻找。在精神和身体都极为饥饿的年代里,肖成功给了“我们”与现实对抗的美好的世界,然而,在“我们”被逼“告密”之后,他回了老家,“我们”曾怀着“赎罪”的心理寻找过他,远远地看到他在河边放羊潦倒落魄的模样,以致“我”到了德国还在寻找是否有一个和格林兄弟一起骑着山羊来的爱读书的中国人。
小说以儿童的眼光看世界,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个作为小说叙述者的儿童“我”并非是原来的那个懵懂无知的“自我”,而是在成年之后有了人生经验和成熟社会认知的“自我”,是作者在成人之后观照下的那个过去的自我——“儿童”,因此,所谓儿童视角的叙述也不过是作者借助的一个叙述手段而已,就此而言,小说不可能有所谓“纯粹”的“儿童叙事”。也许正是因为《树上的王国》采用了成人目光注视下的儿童视角的叙述手法,作者满含热情的童年的回忆和怀旧的目光常常不自觉关注到当下现实,在回忆往昔的叙述中,常常会插入现在的情景。比如,小说叙述“我”老家上蔡的响器班特别多,远近有名,随即插入当下的叙述“直到近些年我去周口、漯河、许昌、信阳等城市,还经常能看到在其郊区的墙壁上歪歪扭扭地用白灰刷着上‘蔡响器班,电话’……的字样”。再如,小说回忆“我”瞒着姥姥每天起早在林子中寻找“爬叉皮”以便换钱为肖成功老师买鸡蛋,姥姥看着浑身上下被雾水打得湿淋淋的“我”总是心疼地说,“姥姥不吃恁的糖豆”,叙述至此,小说旋即插入了此后几十年的场景:姥姥下葬那天,“我”向姥姥墓穴撒糖默默祷告。小说在现在与过去的对照中隐现着作者的感伤与忧患,作者深情的悲悼目光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中,形成了作品特有的怀旧情调,产生感伤的美学效果。
二、豫南方言与乡土伦理的建构
每一个作家总是与不同的地域相连,那些来自浓郁的方言区域的作家,儿童时代根深蒂固的家乡方言成为他/她生命的底色,地方方言的烙痕深深地嵌入灵魂之中,不论成年之后的他们走向何方,方言都会如影相随,因为方言的血脉早已流淌于他们的生命之中,可以说,方言是个体生命的文化胎记。古往今来,许多伟大的作家无不表现出对母语方言的重视和偏爱,在他们所创作的许多经典文学作品中渗入了方言的元素。曹雪芹的《红楼梦》采用了北方方言的京腔京语,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被胡适誉为“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韩少功的《马桥词典》、陈忠实的《白鹿原》、莫言的系列小说等无不浸透了方言的因子,方言是作家进行文学创作的源头和生命。
张新科的《树上的王国》也自觉运用了独具特色的豫南农村方言,准确说是作家儿童时代生活过的河南上蔡这一地域的方言。小说一开始就抓住上蔡人说话爱用比喻的特点:“什么巢穴窝什么鸟,什么磨盘出什么料”,用这样的方言俗语引出上蔡人类似的独特表达习惯:“什么季节挂什么朵,什么树上摘什么果”,紧接着借在槐树湾放露天电影《李双双》的老侯的语言:“什么鸟筑什么窝,什么媳妇养什么货”,小说借助方言土语引导读者进入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历史氛围。通读全篇小说之后,读者自然会体悟到:通过这句地方语言特有的表达套路的叙述,作者不但为整部小说讲述特殊年代的故事定下基调,即叙述者所谓的“什么时辰刮什么风,什么响器发什么声”,而且也借“什么树上摘什么果”点名题意“树上的王国”,这些儿童在文革时期正是得益于肖成功老师童话故事的塑造,才不至于沾染时代恶习,反而变得诚实、善良、勇敢,闪耀着美好人性的灵光。
一种方言总是表达某一地域群体成员观察世界、表达情感以及群体之间进行交流的特殊方式,沉淀着这一群体的文化传统、生活习俗和生存方式,也呈现出群体成员普遍拥有的文化心态、情感方式及日常伦理。小说《树上的王国》描写了上蔡人特有的除善于运用比喻的语言表达习惯外,还通常以骂语的方式表达情感、解决问题。打夯的郭有生被槐树湾剧团选中唱小生,他老婆贾雪积极支持丈夫唱好这个角色,为了给他清热润嗓子,每天都精心给郭有生熬制茅草根汤,郭有生有时不愿喝,贾雪则手拎烧火棍满院子撵,边追边骂:“恁个王八犊子,喝,必须喝!喝了嗓子亮堂,将来唱出一嗓子好戏,让旁边那些看笑话的鳖孙们瞧瞧,俺男人不光会打夯!”如果联系小说情节,这几句骂人话正是上蔡乡村特有的表达情感的方式,骂语中充满关心和温情,也塑造了这位强势女性的性格特点。同样,戏班学习敲梆子的吴六斤被张福景的理论搞得迷茫无奈之时,也是用骂骂咧咧的方言表达情感:“敲个鸟梆子还得学乱七八糟这一套,俺爷俺爹懂个狗屁二八和流水,不也敲了一辈子。不干了!”刘都堂开导吴六斤,同样是责骂的语言:“王八蛋吴六斤,恁自个怀揣梆子来报名,当时梆子敲得当当响,比谁都积极。现在咋了?就这点难恁就脚底上抹油想溜,把这里当成旧社会县城里的窑子了?”当时的农村人因文化水平较低,说话直来直去,很少通过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及循循善诱的语言表达,采用这种话语方式虽然显得有些粗俗,但这种骂语却非常符合农村人的语言风格和行为习惯。
小说中不但人物的对话运用方言,而且小说叙述语言也散发着民间的朴野之气,如叙述大队支书“刘都堂不是那种放屁光听响不出味的人”,第二天迅速召集“抡锄头扶犁把的货”讨论成立文艺宣传队的事,小说描写他抽完烟吐烟蒂时“大嘴鼓得像噙了个驴屎蛋子,噗嗤一声将烟屁股突出仗把远”。再如小说叙述肖成功看饰演银环的美丽姑娘魏莹唱戏的神情:“他的眼睛绝不眨一下,好像上下眼皮用半截洋火棒死死撑着”“台上的人走到哪,眼珠子就跟到哪,肖成功那个熊样子,弄得我们四个学生都替他害臊。”小说叙述语言的乡土化与人物方言土语的个性化非常协调的交融在一起。
另外,小说有意加入乡村地域的民谣、民谚、歇后语及一些特有的方言术语,以营构小说的地域化特色和特殊年代的时代氛围。槐树湾的孩子们小时候的启蒙不是唐诗宋词,而是地方上一代代传送下来的明代时期一个叫刘都堂的歌谣:“刘都堂,喃谷糠,拉着耙子粘文章!棍作笔,月当灯,大字写到隔天明……”还有流传在打夯者之间的歌谣:“东家盖房娶媳妇呀,咱们来抬夯啊,哎嗨吆嗨——咣!……”槐树湾孩子们随口编的顺口溜:“郭有生,打夯郎,脸冲天,屁朝地,憋足力,吼一嗓,房上瓦,乱晃荡!”;村里人为吴六斤编的顺口溜:“吴六斤,打更郎,敲着梆子上学堂!东一梆,西一梆,梆梆都在戏眼上……”这些民间歌谣的采用,类似赵树理小说《李有才板话》中引板话入小说的艺术手法。如地方民谚:“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桃饱人,杏伤人,李子树下抬死人”,“大补不如枣子,好吃莫过扁食”,歇后语“驴屎蛋子屙进洪河里——泡汤了”,“蚂蚁尿在字典上——湿(识)不俩字。”等等,还有流传在槐树湾人口中的顺口溜:“大河有水小河满,老子信逑儿子蛮”。
小说中专有名词呈现了地方特色,如对不同年龄的男子的称呼也极富地方个性,用“光肚孩儿”称呼七八岁的小孩子,用“半大孩儿”或“生瓜蛋子”称呼十四五岁的孩子,“年轻货”指十七八的人。再如称儿童游戏“捉迷藏”为“藏老么”,称乐队为“响器班”,称打“篮球”为打“毛蛋”,称油条为“油果子”,称饺子为“扁食”,称聊天为“喷空”,称自制烟卷为“土炮”,称吝啬鬼为“老鳖一”等。此外小说中的方言特色还表现在乡土人物的命名上。如小说中有人物名叫“粪堆”,“粪堆”的娘外号“老叫驴”。这些方言土语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散发着朴野的草根文化魅力和特有的时代气息。
小说中方言土语运用的优长是显而易见的,其对于塑造人物性格、凸显地方特色、营造时代氛围诸方面都具有重要的修辞功能。但小说中方言土语的过多运用有时也可能会限制了作品更广泛传播,也不同程度会影响到其它地域读者的便利接受。《树上的王国》的作者由于采用了第一人称叙事,小说中的叙述者对其运用的地方土语都一一作了详尽的解释,这不但发挥了方言土语的艺术优长,建构原汁原味、独具特色的乡土世界,同时也提供了特有地域和特殊时代语言的活化石,无论从小说艺术自身的审美要求出发,还是从语言生态和文化多样性的考量都具有重要意义。
乡土方言呈现了特定地域的乡土伦理,与政治伦理要求的宰制性宏大叙事不同,乡土伦理遵循的是民间日常生活的原汁原味的表达。政治伦理作为一种压抑性的力量试图主导、规训人们的思想和生活,而乡村的日常伦理总是信赖那些在平平常常的生活中依稀可辨的道德力量和伦理价值,消除乃至对抗政治伦理带给人们的无法忍受的凝重与压抑。“我”母亲能用上蔡特有的骂语训斥保守的魏铁匠,但也会以好酒好菜热心招待魏铁匠,魏铁匠每次到“我”家做客总是带来自打的锅铲或漏勺,“母亲板着脸也不知骂了多少遍,他还是送。”这些场景呈现了充满人情与人性的乡村日常生活伦理。当然,政治伦理总是无孔不入地向乡村日常生活渗透,支部书记刘都堂充满朴野之气的乡土话语中交织着政治话语的强音。乡土社会真正的活力在于民间日常生活的朴野与温情,它交织着生命个体悲悲喜喜的忧愁与狂欢。小说运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政治话语对乡土话语的渗透与改造,也呈现了作者对那个素朴的乡土世界将要损毁的隐忧。这种略带悲悼的情调与儿童视角一起共同构成了对特殊时期历史意味深长的叙述与对荒诞年代的严峻拷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方言土语与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研究”(项目编号:14BZW139)、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础研究重大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方言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17-JCZD-0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文学院)
本栏目责任编辑 张韵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