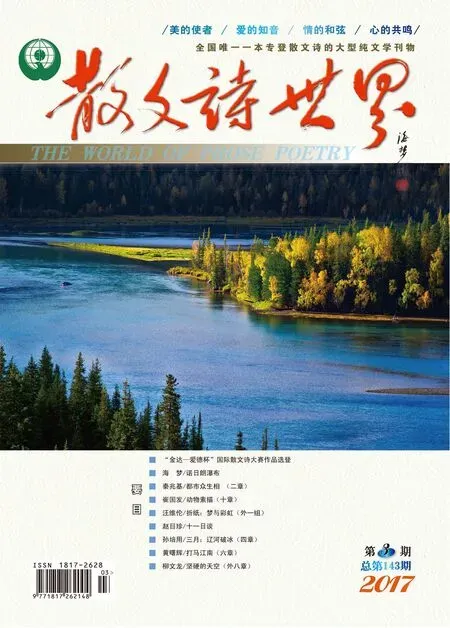在甘南(外七章)
2017-11-13云南
云南 杨 斌
深沉的思索
在甘南(外七章)
云南 杨 斌
一只藏羚羊直直的撞向红日,尘烟里,光线似松脂,滴落在空旷的巷道里。
神情模糊的游人,像蚂蚁,把一缕缕光线拖进巢穴,我写不出,他们背光的那一面,暗藏什么样的光影。
我必须在你身后等待,等待另一只藏羚羊,忽远忽近地在东山顶出现,以及它牵引着的那片逐渐膨胀的月亮出现,我才能看见他乡人在异乡,如何翻找自己的影子。
入冬记
入冬后,走过的路,静止下来,一年的收成,摊在眼前。
去远方的路途上,多少人没有归期,村前流水,带走多少沙石,又滋生了多少草木。
村庄的人,八个老死,新生五人,又有三个怀孕的小媳妇回村,年底,人口基本平衡。
还有一件事,刘二狗在树木秋黄时犯了疯病,他每天坐在村口,扒着手指和脚趾数他的羊,数累时,对着红红的落日,使劲笑。
苍 茫
青木树过大桥村,叫水冬瓜木。
蒲公英的种子被风吹过沙拉河谷,到了得嘞光山,从一个空虚跌入另一个空洞,便萍踪难定。
这是我经过团结梁子时想象出的场景,宁静,又如此苍茫。
那微风下起伏的眷恋,是无名野花在暮色边沿摆动,如同一些平常日子,在我们身边不经意间走过。
许多人,许多事,以及草木、山川、河流、时间,都是这样在我们生活里出现和消隐的。
去深山
去深山的路有两条,右路平直,不会多生出枝节,我取左路,曲径通幽,绵长,有弧度,有魂。
流水,不会随意改变自己的音质;石子温暖的心跳,多情、多姿,像坐在我心尖上的一个人。
风吹雪白长腿的芦苇,昼钓红日,夜钩一弯残月,这景致,适合写诗的人,把头埋进每个章节的留白里,感知岁月与大地微妙关系:恒温、平稳、精深。
我愿意就这样,从此随了它们。
古道黄昏
在土坎上歇气的背草人,拐过山隘口后,夕阳残照的光带着余温,又把古道抚摸了一回。
那些摆脱黑暗的羊群,褪下黑色的皮毛,身披红光向你涌来,还有多少看不清的飞鸟、虫儿,在各自的命运中潜行。
也有一阵风起,倒伏向路中央的芦苇,纷纷站直腰身,让出一截漫漫长路来;
我只能拿我的无知和莫名感动的泪水,加入这细密悠长的静谧……
北方古道口
再往高处走一程,就是古道口那棵滇杨树冠托举的天空了。
北上或南下,那么多在树上暂歇的候鸟,它们的身影,被一阵一阵的风吹走,数也数不清,我只是在它们经过我的视线时,侧了侧身子。
避不过去的,是尘土,我模仿那个老人,捡起一截松枝插在牛车边沿上,挡了挡快滚落的夕阳,拍了拍双手,接着走。
在三台洞寺
那只在寺顶静止下来的鹰,被早课的钟声驱赶,向大咪咪鼓山顶飞去,身形飘渺而旷远。
仙人洞前水潭上的鸟影,一只、两只的模样……
一个周末背着书包回家的小姑娘,她拜完观音菩萨后,又提着饮料壶,去取寺庙底座下流出的龙潭水,她坚信母亲喝了这长青水,眼疾会好起来的。
诵经声停止时,走出经堂的人,满脸平静,看不清悲和喜、苦和痛,像洁净的尘埃,一粒粒消散在山路上。
我在佛前祈祷,所有赶路的人,都能遇见未来的自己。
跨出苍老寺院的门槛时,那只又飞回来的苍鹰,给我一件黑色风衣。一抹清凉之风掠过内心的苍凉,看着远方的小咪咪鼓山顶,正被风雪扑打,我需要停下行走的脚步,静一静。
尘 世
昨天,去了趟白果林,叶子,早已落光,只剩下光秃秃的树枝,像这片树林所在的葛菇村,一条条道路,通往远方的迷茫里。
我是来看一眼那棵600多年的古树,它伸进天空的身影如此恍惚,一截吊挂的枯枝充满古旧气息,像一段颓废的青春,埋首在岁月的胯裆。
一只只蚂蚁,在苍老的树干上来回,落在地面的阴影,如我此时的倦意,再大的风也不能吹走,忍不住回想来路——杂事俗身,朝夕云烟,不值一提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