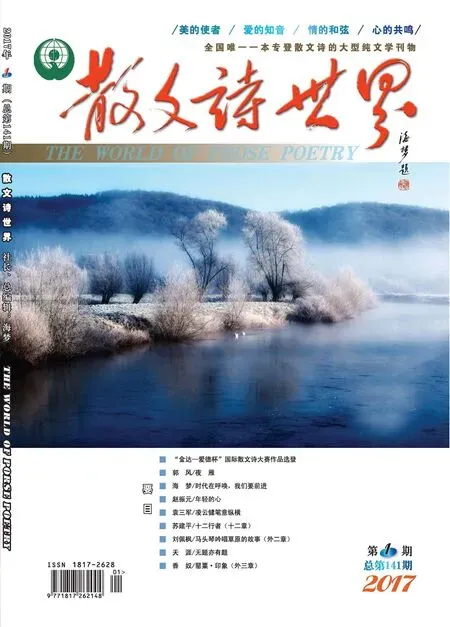回乡(四章)
2017-11-13河北孙庆丰
河北 孙庆丰
回乡(四章)
河北 孙庆丰
没有荣光的游子私自归来
荣光尽失。山道蠕动的车辆,像一匹瘦弱的老马。苍老的日历,泛黄的记忆,无法考证一颗漂泊的心,该是多少次,满载着一腔泪水归来。
总有一些树木,年轮和我的岁数相仿,离家时的鄙夷,依旧镌刻在身。尽管都老得笑不动了,风吹过时,掉了门牙的枝丫,还在拼着老命摇摆。
移不动的大山,劈不开的山路,就像丢不掉的贫穷,连缀着故乡,斩也斩不断。所有的希望,幻化成一道道魔咒,一年年,紧箍着这些走出去的,或是即将走出去的,山里的孩子。
唯有等到夜幕降临,这些幽灵般的离魂,才敢偷偷进村,小心翼翼地,生怕一声犬吠,惊醒了那些饥渴的眼神。祖祖辈辈,似乎已形成一条,不成文的条律,没有荣光的游子,他的私自归来是有罪的。
被寒冬笼罩的夜晚
院门虚掩着,又一根门闩孤独地死去。墙角堆满了腐烂的尸体,就像我年轻时的那张照片,早已被父母摩挲得皱皱巴巴,多少年却不忍丢弃,亲情是关不住的。
屋里没有开灯,明朗的月光或许让父母感到恐惧。归来的脚步越来越近,近得在他们失眠的枕旁,融合着热切而沸腾的心跳。开门的那一瞬间,泪水像月光一样泻了进来。
锅里的饭菜还有余温,不晓得一晚上,母亲要几次焐热灶台。就这样反反复复,夜空下的一缕炊烟,一年四季,都在呼唤着游子归来。其实进村的时候,我看到许多家炕头的叹息,从烟囱挤出,喘着长长的粗气。
这一夜,整个山村注定是难眠的。被寒冬笼罩的夜晚,室温急剧下滑,但比起对荣光的渴望,贫穷才是人心最大的恐惧。在村口我隐约听到了狼的嚎叫,父亲说这些年,山里的野兔都被村民们打光了。
没有人能知道,我内心曾经的锋利
上苍从不怜悯卑微的灵魂,太阳早早醒来,突兀的远山,一如我的脸上黯无光彩。任何一丝可能闯进的世俗的鄙夷,都被父亲用一根崭新的门闩阻挡起来。
我慌忙从炕头背过身去,因为我分明看到,父亲的脸上,掠过些许羞愧与无奈。平常简单的一顿早餐,今天被母亲张罗得过年一样丰盛,每一道菜都散发着母性的慈爱。
其实比起荣光,她更在乎儿子的平安和健康,只是在父亲面前,从不敢说出来。倔强的父亲,或许从心里已向命运屈服,他拼命打磨着锈蚀的农具,渴望能找到一丝慰藉的光彩,但所有的农具都是那么不争气。
我的脸颊不由地灼热起来,像一把被遗弃的镰刀,没有人能知道,我内心曾经的锋利,即使躺在冰冷的墙角,也依旧未曾忘记自身的使命。然而,我的命运还不及一把镰刀,在城市,我至今未能找到,一片可供我收割的土地。
村子越来越小
囚居般的生活,无颜去面对关爱我的乡亲,甚至无法将一滴惭愧的泪,去滋润荒芜已久的田地。负罪的灵魂,和成年累月积聚的贫穷一起,默默被大山挤压着,一只受伤的孤雁喘不过起来。
山里的风裹挟着飞涨的物价,越来越剧烈,瘦削的院子被刮得异常单薄。说不清哪一天,日子会先于屋子倒塌,那时将引得多少孤魂,夜夜在异乡暗自哭泣。
我突然想起在回乡的路上,许多熟悉的面孔,都陌生得不敢打招呼,生怕那条魔咒般的条律,箍痛每个人脆弱的神经。唯有那些苟延残喘的老树,像魔鬼一般面目狰狞,让这些跌跌撞撞的游子们,仿佛闯进了祖先的坟地。
羞愧,负罪。家是我们唯一的方向,荣光尽失,却让这些曾手足情深的孩子们,如今一个个都形同陌路,宛若幽灵。难怪村子越来越小,小得这些年,都喊不出一个熟悉的、闪耀着荣光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