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离的身体与永恒的歌声:论《夜半歌声》中的分身影像
2017-11-02王玉辉
王玉辉
游离的身体与永恒的歌声:论《夜半歌声》中的分身影像
王玉辉
《夜半歌声》作为中国电影史上恐怖电影的先驱之作,恐怖元素的背后同时蕴含着丰富的内在影像逻辑。文章以身体和歌声为切入点,分析二者内在的影像互动关系,进一步得出其背后蕴含的恐怖与分身关系。一方面,由于身体的游离带来强烈的不安定性,成为影片恐怖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歌声作为整部影片永恒的旋律,是维系游离身体的唯一纽带。由于身体的游离性,它要不断地寻找新的载体,分身影像随之出现。文章期冀在“重写中国电影史”的学术背景之下,探索一条“分身”视角下研究中国电影尤其是早期恐怖电影的新路径。
身体 歌声 游离 恐怖 分身
一、大陆学界对恐怖电影及《夜半歌声》的研究综述
恐怖电影作为一种特殊的电影类型,大陆学界对其研究与关注从未中断。但是与当下盛行的“青春电影”“二次元电影”“魔幻电影”等题材影片相比,恐怖电影的研究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似乎没有得到足够的理论关注。应该说目前国内恐怖电影的研究仍然处于类型电影研究的边缘位置。并且对一些恐怖问题的论述还停留在鉴赏层面,缺乏足够的理论深度。就现有文献来看,大陆学术界对恐怖电影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叙事结构、类型模式、服装、道具、声音等元素对恐怖氛围的营造层面,对于产生恐怖的内在影像逻辑探求略显不足。其次,很少有文章讨论“国内恐怖电影生存的内外部环境”,这恰恰是中国目前恐怖电影创造发展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目前国内恐怖电影研究还缺乏一个必要的、客观的、公平公正的外部大环境,没有真正把恐怖电影看成一个独立的社会文化单元。如果对恐怖电影适合生存的环境无清晰的认识,再多的细节性探讨也将只是流于形式。所以,大陆的恐怖电影研究系统性、理论性及影响力还比较薄弱,这与日本恐怖电影研究相比存在较大反差。如果对恐怖电影的探究一直束之高阁,那么恐怖电影将会永远“被恐怖”下去。但是,假如尝试掀开这个题材的恐怖面纱,其实恐怖电影带来的不仅仅是惊险刺激的视觉恐怖,它还蕴含着深刻的现代人文哲学思想,启迪着人类的觉醒,具有极强的社会文化表意功能。
马徐维邦(1905-1961)作为一位特征鲜明的电影作者,以其独特的光影色调与入世情怀塑造了中国早期电影史的个人传奇。其代表作《夜半歌声》更是作为中国早期电影史上优秀的国产恐怖电影,为世人所熟知。①影片的问世不仅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社会轰动,历经近百年的岁月洗礼,其光影魅力与史学价值依然值得肯定。②截至目前,大陆电影史论学者对1937年版《夜半歌声》的解读文章大致有五十余篇,除去部分介绍类文章之外,理论视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将《夜半歌声》视作中国恐怖电影的开山之作,强调它的史学意义和价值。如李道新的《马徐维邦:中国恐怖电影的拓荒者》、郑培为的《中国第一部恐怖电影》等,将其放入中国电影史的脉络中,作为国产恐怖电影的开山之作来做史料引证之用。第二,着眼于作品艺术特色,对影片的主题、音乐、恐怖效果营造等艺术表现手法进行分析。“(《夜半歌声》)不是一部纯粹的商业影片,而是一部以恐怖片的影音元素、叙事结构和导演手法传递反帝、反封建的前进意识及关注时代、探询人性的优秀作品”③“带有表现主义特点的心理恐怖风格”④“影片以恐怖类型片的面貌出现,在技巧上学习了好莱坞恐怖电影的很多手法,通过悬念的制造和光影的渲染,的确具有强烈的视觉效果。影片音响音乐效果也十分切合故事情节的发展,总体情节和氛围十分完整”⑤等等。第三,将此影片与原作《歌剧魅影》(The Phantom of the Opera, 1925)及后续几部改编版《夜半歌声》进行比较研究。在所有文章中旅美学者张真撰写的文章《〈夜半歌声〉:声音的惊悚和历史的异像》⑥研究视角新颖独特。作者对影片的声音、音乐、性别政治以及历史之间的相互关系等逐一论述,诸如“身体、分离、分身、时间”等现代性研究术语频繁使用,阐述角度极具启发性。但遗憾之处是未能深入。基于此,本文从“声音”与“身体”两个对象出发,对影片做进一步文本细读,旨在从中国早期电影尤其是早期恐怖电影中探寻中国电影中“分身”表现的影像魅力。
二、游离的魅影之于恐怖
《夜半歌声》作为中国早期电影史上恐怖电影的杰出代表,“恐怖元素”自然是本片的最大特色。本文以身体的游离性为切入点,分三个层次对影片的恐怖意义进行梳理。
第一重恐怖:视听效果
如果仅从剧情本身来看,《夜半歌声》应该算不上恐怖。但是画家出身的马徐维邦在保持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充满悬念的同时,灵活运用音乐元素和视觉影像(如倾斜拍摄、叠影构图、晃动摄影等)成功营造出阴郁诡异的恐怖气氛。影片带有明显的德国表现主义特征,强烈的明暗对比、若隐若现的魅影、夸张的肢体语言、支离破碎的布景……应该说在当时那个年代,学贯中西的马徐维邦已经熟练驾驭了恐怖电影的拍摄样式。
首先,片中人物造型对比强烈。若隐若现、神出鬼没的宋丹萍;蓬发奸诈、面貌怪异的守门人;披头散发、目光呆滞的李晓霞;动作僵硬、神情木讷的老仆人……同时宋丹萍的黑色长袍与李晓霞的一袭白衣也形成强烈对比,两个封建社会的受害者形成了极具悲情意味的象征造型。精心布置故事发生的内外场景。在幽暗的灯光中,行动不便的守门人缓缓打开门,引领着一群充满好奇的戏班子人员一步步前进。主观视角慢慢推进,镜头摇摇晃晃,狭窄的长廊、破败的楼阁、随处可见的蜘蛛网、遍地的老鼠、房梁上悬挂的面具和帷幔……无一不让人感觉毛骨悚然。⑦空镜头配合外景写意,营造出萧瑟、凄厉的气氛。影片中多次出现乌云、月亮、枯藤、浮萍、波涛、雨夜等空镜头,在表现歌曲意境和人物心境上起到了重要作用。
马徐维邦十分讲究光线和阴影的使用。影片开场,惨白的月光被乌云遮盖,古老的剧院看上去荒凉冷清,镜头慢推拉近剧院大门,一个破烂的招标启示看上去十分扎眼,仅仅十几秒钟,一个骇人又充满神秘色彩的故事环境展示给观众。同样在孙小鸥与李晓霞林中相遇的场景中,光影的运用也相当具有中国传统美学色彩。身穿一袭白衣的李晓霞幽灵般从雾气迷蒙的森林中缓缓走来,打在她身上的光若隐若现(见图1)。老树暗色的轮廓映在微微波动的湖面上,影片在表达恐怖之余又无不散发着中国传统美学中的诗意感伤情怀。

图1.丛林深处“幽灵”般走来的李晓霞
音乐和音效在影片中起到了迎合剧情、烘托氛围的作用。电影开场,在钢琴伴奏下,云开月现,一盏孤灯从门缝隙中缓缓伸出,引出一位相貌丑陋的老者。而后,风声大振,黑影攀上高墙。歌声渐起“人儿伴着孤灯,梆儿敲着三更,风凄凄,雨淋淋,花乱落,叶飘零。”在配乐与画面的共同作用下,荒凉、阴森的气场渐渐铺展开来。在这里韵律美与造型美的结合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为观众奉上一场精彩的视觉震撼。
第二重恐怖:内心的不安定性
电影中的恐怖不能只是通过一些面目狰狞的妖魔鬼怪来实现,也不能仅靠一些诡异的造型和阴森的环境来渲染,更需要通过一系列心理上的暗示,使观众从心理上产生意外的震撼。担任新华影片公司导演的马徐维邦对于当时充斥市场的许多影片甚感不满,尤其是那些单纯靠刺激感官的手段来招徕观众的影片。所以马徐维邦在《夜半歌声》中塑造了一个“幽灵般”存在的“魅影”,通过这个“游离的身体”来制造悬念,给观众带来内心的恐惧。
影片开始部分,一个游离的魅影伴随着激昂的音乐在黑夜中铿锵起舞。此时观众并不知道这就是影片主角宋丹萍的第一次登场。通过魅影的方式呈现,一方面制造了悬念、留足神秘感;另一方面成功地烘托出影片的恐怖气氛。如果说“破败的楼阁、随处可见的蜘蛛网、遍地的老鼠、房梁上悬挂的面具和帷幔……”只是一种临时性的造型恐惧,识别后便可以克服的话,那么游离的魅影带来的不安定感就是“无法克服的恐怖”了。当老鼠跑过,倒垂的面具被识别,一时的恐惧感便可立即消解。但是半夜飘荡在空中的歌声如果迟迟找不到归宿,那么这种不安定性将会一直萦绕在观众心中。它急需要寻找一个实体来附着,消解恐怖。所以另一个人物孙小鸥随即出场。魅影和歌声暂时停止,内心恐怖得到临时缓解。
人物造型和舞台道具的恐怖只是视觉感官上的一时恐怖,真正的恐怖是存在于观众对于不明事物无法识别时的内心恐怖。可以说通过这个幽灵般存在的“游离魅影”,马徐维邦成功地将电影的恐怖从一种“可以克服的恐怖”提升到“无法克服的恐怖”。所以《夜半歌声》虽然是一部恐怖电影,但是它不同于传统的牛鬼蛇神等神怪故事,它是一部完完全全立足于社会现实,通过制造不安定性来实现内心恐惧的现实影片。
第三重恐怖:暴力畸形的社会性
马徐维邦认为恐怖是一种表现手段,为什么不可以运用它来为进步而有意义的内容服务呢?为什么不可以通过恐怖样式的电影作品来描写社会、反映现实、启示观众呢?通过叶蒂于1937年2月22日发表在上海《大晚报》上的称颂小文便可略见一斑,“一般恐怖片之缺少价值,主要是在于故事构成的荒唐。现在,相反,用恐怖的形式来表现我们所需要表现的,其意义,是不可同日而语了。”⑧
首先,毁容前的宋丹萍潇洒帅气,举手投足都透露出优雅和风度。毁容后的宋丹萍不仅相貌丑陋,而且言谈举止也发生较大变化。他近乎于用一种哀求中夹杂强迫的方式让孙小鸥替自己去安慰李晓霞。人物性格一前一后形成强烈对比,揭示出当时社会的黑暗与恐怖。吃人的社会把一个好人活活地逼成鬼。同时《夜半歌声》演绎了一种“正常人与怪物的转化,最终达到不可区辨”。原本的正常人宋丹萍被迫害成一个怪物,原本富家小姐李晓霞被打击成一个精神病人。当群众看到毁容后的宋丹萍误认为是怪物,群起而攻之。黑暗的国民党封建官僚统治下人民群众的愚蒙无知一览无余。这样影片反映出一个哲学性问题:究竟谁才是正常人,谁是怪物呢?就影片的故事情节来看,我们可以说宋丹萍是一个怪物,李晓霞是一个精神病人。但是进一步思考是不是可以说称他们为怪物抑或疯子的民众或许才是精神层面的畸形人呢?所以影片不仅是一部视觉意义上的恐怖电影,同时也对黑暗丑恶的人性进行了深刻的抨击。通过恐怖片的手法反映出黑暗社会制度下人性扭曲的恐怖,或许这才是影片所要表达的真正恐怖吧。
三、身体的游离之于分身
1.镜像与精神分离
在《夜半歌声》中宋丹萍具有多重社会身份。首先他的真实身份是一位从事革命工作的地下党人。同时为了心中的革命事业,他又伪装成一位舞台名伶。所以这样一个身兼多重身份的人物在黑暗的社会压迫下,身体与精神一直处于不安定的状态。这也为毁容后的宋丹萍寻找替身埋下了伏笔。如果说黑暗社会统治是导致他身体与精神分离的根本原因,那么毁容一事则是导致两者直接分离的催化剂。
法国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吉尔·德勒兹指出“镜子的影像,对于镜子所捕捉的实在人物而言是潜在的,但是对于镜子而言,即对于仅将单纯的潜在性赋予人物、并将其推出画面之外的镜子而言,却又是实在的”⑨。镜子的影像是一个双面的影像,对于镜子捕捉到的实在人物来说,他是潜在的影像,但是对于镜子本身来说,它则是实在的影像。在镜子的影像中潜在和实在变得无法区分。“不可区辨的原理达到了极限,增殖的镜子吞噬了两个人物的实在性,他们只有通过打碎所有的镜子,面对面相互厮杀才能够获得自身的实在性。”⑩在一个长镜头中我们看到在剧院老板的帮助下,宋丹萍头上的纱布被一层层揭开。此时镜头并没有给出宋丹萍身体的任何镜头,观众看到只是戏院老板摘一条条纱布的动作(见图2)。人物表情静止,身体语言进入。固定镜头下,动作相比语言或许更擅长表意,因为动作不是单纯的指出,而是与某种关系。正如张真《银幕艳史:都市文化与上海电影(1896-1937)》一书中所言:“这个动作就如同抽丝剥茧,强调了他的变形。”11此时观众与宋丹萍一样,焦急地等待着纱布摘下,重见光明。

图2.剧院老板帮宋丹萍摘纱布
紧接着宋丹萍起身,踉踉跄跄地走到镜子前,一张血迹斑斑的脸庞出现在画面中(见图3)。因为镜头本身呈现给观众的是一种虚像,一开始看到丑陋的面孔时,观众也无法立刻辨别这到底是实像还是镜像。直到站在镜子前的宋丹萍缓缓进入画面,观众才发现之前看到的不过是宋丹萍毁容后的镜像。镜子不仅是揭示宋丹萍怪异面孔的工具,也是展现表层与深处,本体和复制品之间暧昧关系的空间。宋丹萍在镜前看到了自己扭曲的容貌,随即愤怒将其打碎。打破镜子的那一刻不仅是宣告自己与舞台的诀别,更是宣告自己肉体的死亡。观众再也见不到宋丹萍人前唱歌的形象。镜前的一束烛光既是对他死去肉体的哀悼,又为他优美的歌声留存的一束生命之光。自此优美的歌声与宋丹萍的身体彻底发生分离,只有每个孤独的夜晚与游离的魅影独舞。

图3.毁容后的镜像宋丹萍
2.作为“面具”的替身
众所周知,《夜半歌声》对美国好莱坞影片《歌剧魅影》进行了借鉴和改编12,同时融入了反封建、争取自由、铲除邪恶、复仇正义等内容13。在《歌剧魅影》中郎却乃主演的魅影出场时带着一副面具,正是这个面具也成了全片延宕故事情节发展的重要道具。直到女主角克莉丝汀演出《唐璜》时,她将魅影的面具扯下,将全片推向高潮。在《夜半歌声》中马徐维邦却将面具这一道具拿掉,添加进孙小鸥这个角色。这个人物的加入不仅是让影片的叙事更加复杂曲折化,更是增添了一层哲学韵味。与其说孙小鸥是一位杰出的后起才俊,倒不如说他是宋丹萍的一个“人皮面具”。即便是在深爱着自己的李晓霞面前,这个作为替身存在的虚假宋丹萍都不能识别。所以,虽然《夜半歌声》中为宋丹萍省去了面具这一道具,但是又为他打造了一个栩栩如生的“人皮面具”。
那么孙小鸥这个“面具”和原版魅影的面具有什么关系呢?吉尔·德勒兹立足于电影曾言到,影片中的“道具”也是一种“结晶影像”14。这个面具就像德勒兹所描述的大海中的轮船,它也同时拥有实在和潜在两个面。并且两者之间可以进行交换,构成实在和潜在的无法区辨的结晶影像。这个道具跟奥逊·威尔斯《公民凯恩》中的玫瑰花蕾,特吕弗《绿房子》中的绿房子发挥着一样的功能。《歌剧魅影》的面具后面,隐藏着的是邪恶的占有欲,强烈的对克莉丝汀的精神和肉体的占有欲望;而《夜半歌声》中宋丹萍也没有摆脱掉自己占有欲的“恶”的一面,他所做的许多事情都是在以一种近似强迫的哀求方式让孙小鸥完成的。同样,相同的人生遭遇,构成了十年前和十年后两个故事的一致性。最后两个受害者孙小鸥与李晓霞走在一起,两段不完整的情感凑成了一段爱情,这又进一步加深了整部影片的“悲情”色彩。
3.师徒关系下的分身
与宋丹萍一样,作为新一代男演员的孙小鸥也是一位舞台演员。相同的职业身份为二者的结合创造了天然的契机。宋丹萍与孙小鸥的第一次相识,便是从传授歌唱技艺开始的。孙小鸥演出成功后答谢宋丹萍,宋丹萍拍着他的肩膀,掷地有声地说道:“朋友,你是个有热情、有勇气、有希望的青年,我等了整整七年,到今天终于等到了你……”与直接语言相比,肢体更能够传达出身体的态度。一个“拍”的动作不仅是对孙小鸥的渴望,更像是中国传统武侠故事中,师徒二人内在功力的传递。影片在记录两人第一次相遇时画面的用光也暗合了这一阐述。孙小鸥与宋丹萍在破旧的阁楼内相遇,宋丹萍处在画面的光源处,身体处于暗处,孙小鸥则处在顺光处。一明一暗不仅表明了两人的身份,同时也是暗含了宋丹萍向孙小鸥传递革命光明的使命。同样孙小鸥与李晓霞的第一次约会中,影片通过李晓霞的主观视角也直接交代了宋丹萍与孙小鸥的师徒分身关系(见图4)。所以,与其说宋丹萍与孙小鸥的存在关系是一种优美声音的传递,不如说两人只是这美妙歌声的承载体。换句换说,影片通过两人建立的是一种师徒分身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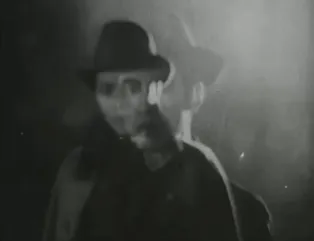
图4.宋丹萍与孙小鸥的叠影影像
四、永恒的歌声与分身
在《夜半歌声》中歌声是永远的旋律,起着延宕故事发展的重要功能。影片无刻不在用歌声建立联系。孙小鸥与宋丹萍第一次见面的场景,孙小鸥闻声寻来,问看戏园子的张老头是谁在唱歌。张老头回答:“这里只有我一个人,没有第二个人。”但是当“可奈何,像小鸟回不了窝……”歌声再次响起的时候,张老头明白了宋丹萍用意,随即改变了口吻,指向了墙上的一张陈旧的海报。“不要害怕,我已经和他相处十年了。”不需要任何的语言解释,歌声就可以充分表意。同样,在上文提及的孙小鸥谢恩的场景,声音画面给出的是孙小鸥说的“我永远忘不了你给我的恩德”,而镜头画面并没有完全给出孙小鸥的面部特写,光线只打在了他的一个侧脸上(见图5)。所以,可以说在影片中任何姣好的面容都只不过是歌声的一种陪衬,唯有这美妙的歌声才是影片永远的主角。

图5.侧脸光源的孙小鸥
歌声不仅起着延宕故事情节的功能,同时被赋予了空间上的深度。影片可以理解为是歌声视域下的载体重现。宋丹萍、孙小鸥都只不过是歌声的一个载体。通过歌声,毁容后的宋丹萍与李晓霞得以在夜晚短暂的精神邂逅。影片中只有歌声是永恒的旋律,其他的任何载体只不过是一种临时工具。所以《夜半歌声》中真正的主角是歌声,如同第五代导演陈凯歌作品《黄土地》中真正的主角是连绵起伏的黄土地。这是一种广义意向上的精神诉求,同时也是影片的内在核心所在。
如果单纯把歌声抽离出来,影片中与歌声发生关联的肉体(或载体)大致有这样一些附着物:曾经舞台上风流倜傥的宋丹萍、深夜歌唱的神秘魅影、作为替身的孙小鸥。虽然一具具承载歌声的身体受到破坏、打击,但是只要歌声还在,故事就将继续。歌声如同坚强不屈的精神灵魂,只要有灵魂就有希望。因此,影片开始部分,一个鬼魅的黑影出现在阴森昏暗的画面中,但当歌唱响起,画面的亮度一下提高(见图6)。这也正好契合了以上论述。无论身体受到何种伤害,只要美妙的歌声犹在,希望就将存在。

图6.歌声唱响前后的画面对比
分身的影像表现在影片最后部分得到进一步升华。孙小鸥和李晓霞面朝大海,偎依在夕阳之下(见图7)。此时没有任何声源的《夜半歌声》主题曲再次响起。观众知道此时宋丹萍已经投江,孙小鸥也没有引吭高歌。所以再次印证了影片中各种人物的出现都只不过是歌声的一种载体,正如影片最后歌声中所唱的那样“唯有这夜半歌声!”。

图7.面朝大海的孙小鸥和李晓霞
五、政治化受虐
虽然《夜半歌声》在中国电影史上已经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成就,但它依然带有那个年代电影的一些症候。其中政治化受虐便是其一。当然政治化受虐问题并不仅是30年代以及《夜半歌声》的个案问题,在很多中国革命题材影片中都有涉及。不过在恐怖电影中夹杂政治化受虐的表达还是具有很高的警醒意义。弗洛伊德曾经作出“性爱受虐”“女性化受虐”“道德性受虐”的分类。作为道德性受虐已经和性没有直接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宗教苦行式的负罪意识和自责。15想当然地制造出合“施虐——受虐”为一体的单位,这正是吉尔·德勒兹在《关于萨克·马索克:冷淡与残酷》(Présentation de Sacher-Masoch Le froid et le cruel,1967)中予以严厉批判的做法。德勒兹从分别成为施虐癖(Sadism)和受虐癖(Masochism)的命名契机的萨德(Sade)与马索克(Masoch)的文学中发现了它们的本来姿态,对其进行了更为严密的详细区分。他先是在这两种文学语言中,识别出“用制度的专有词语进行思考的是施虐狂,用盟约关系的语汇进行思考的是受虐狂”。在其同“法”的关系上,德勒兹从萨德文学中发现了一种“为追求更高层面的原理而超越法,将法只看作是一种二次性的存在”的讽刺性上升运动,在马索克文学里发现了一种“从法下降到其种种归结”、与表面的顺从性相反的带有嘲弄的幽默性运动。并且,他还按照精神分析的用语对自我的败北/超我的膨胀(施虐癖)和超我的崩溃/自我的理想化(受虐癖)作了详细区分16:第二章《萨德、马索克、以及二人的语言》、第七章《法、幽默、以及讽刺》、第十一章《施虐癖的超我与受虐癖的自我》。17中国革命题材影片往往会出现类似的情形,带有极强的说教主义的意识形态功能,这也正是本文称之为“政治化受虐”的理由所在。影片中作为革命流浪者的宋丹萍从与孙小鸥见面的第一刻起便开始讲述自己13年前的革命经历,诉说自己作为一名革命党人的满腔热血。紧接着痛陈历史,讲述自己遭遇到的不公与迫害。同样影片结尾部分,孙小鸥面对女友绿蝶被恶人汤俊杀害、恩师宋丹萍被群众疯狂追捕时,非但没有第一时间关心抢救女友,或者对恩师施以援助,而是跑到李晓霞面前托出宋丹萍假死的真相,并且告诉她,“……他(宋丹萍)把汤俊打死了,军阀方面也发现他是革命党,这下是绝对活不成了!”李晓霞遭遇二次打击再次瘫倒在地。再有,被围观群众挤倒在地的看门人老人奋力地抓住孙小鸥的腿,讲道,“孙先生!你要明白,宋先生要你帮助他的不是为了他的个人,是要你完成他的(革命)心愿的!”等等。生拉硬套地将政治色彩加入影片使其艺术性受损。所以也难怪这部万众褒奖的作品偶尔也会招来一些批评。电影史学家程季华先生曾经在评论中写道:
“影片大力渲染和赞美的宋丹萍的个人英雄主义、自我奋斗、小资产阶级的狂热以及他与李晓霞‘缠绵悱恻’的爱情,却是和当时国防电影运动的主导思想相背离的。在艺术表现上,导演完全照抄了《歌剧魅影》一类的好莱坞恐怖片的手法”。18
一概而论,虽有失偏薄,但也有切中要害之意。
《夜半歌声》作为中国早期电影史上的扛鼎之作,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洗礼,其艺术成就与史学价值依然熠熠生辉。影片摒弃中国传统妖魔鬼怪小说的创作方法,立足于影像本身来制作悬念和恐怖的创举对后世恐怖电影的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意义。同时,影片通过“声音”与“身体”的存在状态,营造出复杂多样的“恐怖”层次。尤其恐怖光影背后蕴含歌声“分身”的主题,更是难能可贵。马徐维邦是中国电影史上实至名归的“恐怖电影的拓荒者”。当然本部影片还有许多其他值得探究的地方,比如多次出现马的镜头。宋丹萍革命逃亡的时候身体近景与奔马形成叠影交融(见图8),再有就是宋丹萍遭遇李晓霞父亲毒打的时候,后面也有一匹咆哮的奔马……这些都是影片耐人寻味的影像表达。

图8.宋丹萍与奔马的叠影
【注释】
①目前国内学术界许多文章将《夜半歌声》称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部国产恐怖电影。但是马徐维邦在创造《夜半歌声》之前,便已经拍摄了另一部同样具有恐怖色彩的作品《情场怪人》(1926)。因为本文旨趣在于《夜半歌声》的本体论分析,否为第一部国产恐怖电影关系不大,所以在此问题上不做过多赘述。
②在近半个世纪后,中国电影人不断把其重新搬上银幕。1985年导演杨延晋第一次重拍《夜半歌声》,由翟乃社和李芸分别扮演宋丹萍和李晓霞;1995年,香港地区推出了新一版的《夜半歌声》,该片由黄百鸣、于仁泰任编剧,于仁泰导演,张国荣、吴倩莲、黄磊主演,不过该影片较原版的影像表现手法大大减弱了恐怖元素,呈现给观众的是一场纯美的爱情悲剧故事。2005年,黄磊自编、自导、自演了电视连续剧版《夜半歌声》。
③[中]李道新.中国电影文化史(1905—2004年)[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67.
④[中]陆弘石,舒晓鸣.中国电影史[M],文化艺术出版社,1998:50.
⑤[中]李少白.中国电影史[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88—89.
⑥[美]张真.银幕艳史:都市文化与上海电影(1896-1937)[M],上海书店出版社,2012.
⑦与之相比之后几版的《夜半歌声》虽然在技术上有所提高,演员造型更加逼真、剧院也变得华丽颓美,但是对于影片的主题表达远不及本片。
⑧[中]叶蒂.夜半歌声[N],大晚报,1937.2.22.
⑨[法]ジル·ドゥル一ズ.シネマ2時間イメ一ジ[M],宇野邦一,石原陽一郎,江澤健一郎等日本語訳.法政大学出版局,2007:96-97.
⑩同上。
⑪[美]Yomi Braester. Witness against History: Literature, Film and Public Discourse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3:99.
⑫再往前可追溯到故事的小说原型,改编自善于制造悬疑和恐怖气氛的加斯顿·勒鲁(Gaston Leroux)于1911年发表的著名小说《歌剧魅影》。
⑬《夜半歌声》在恐怖之外融入了歌剧片的元素。由田汉作词、冼星海作曲的《夜半歌声》《黄河之恋》和《热血》三首插曲委婉动人,出色地烘托出了影片的革命主题。
⑭关于结晶影像的论述,吉尔·德勒兹在其著作《电影2时间影像》第四章中有详细阐述。
⑮フロイト、「マゾヒズムの経済的問題」、『フロイト著作集6』、人文書院、1970年、p.301.
⑯参见吉尔·德勒兹(莲实重彦译)《马索克与萨德》(日文ジル·ドゥル一ズ「マゾッホとサド」晶文社1998/10出版)。
⑰具体可以参见日文文章応雄「過剰が呼びかけた時—文革映画、『南海長城』(1976)、〈政治化したマゾヒズム〉」、『映像学』、第77号、2006年、pp.23-41.
⑱[中]程季华.中国电影发展史[M],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
王玉辉,日本北海道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映像·表现文化论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