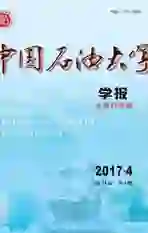弗莱神话原型批评的意识形态转向
2017-10-27李巍��
李巍��
Aug.2017Vol.33No.4
DOI:10.13216/j.cnki.upcjess.2017.04.0013
摘要:弗莱在《批评的解剖》中区隔出独立循环的文学世界,但外在语境的缺失让文学整体循环的可能性受到质疑。弗莱起初通过建构文学的关怀功能来连接它与社会的断裂,但循环的动力何在依然悬而未决。因此在《圣经》研究中他引入意识形态概念,意识形态被限定为语言的一種功能特性,能根据社会的变迁来调整语言能指与所指的关系。由此文学整体循环的动力以及文学与社会的互动问题得以解决,同时还不违背文学的本体地位。但神话与意识形态的这种对接也让弗莱的原型批评逐渐走向更加宽泛的文化批评。
关键词:弗莱;原型批评;意识形态;《圣经》;关怀神话
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5595(2017)04007506
弗莱的原型批评一贯强调文学的自足与文学批评的本体化,这几乎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在弗莱那本具有世界影响的著作《批评的解剖》中,他也确实如此这般地践行着这一主张。对文学发展的规律以及文学的意义生成等问题,弗莱都表现出十足的克制,他始终没有滑向对此有巨大阐释力的社会学批评或历史传统更悠久的哲学批评。不仅如此,弗莱也拒绝承认自己属于任何一个流派(包括神话原型批评),他表示自己出版研究布莱克的专著时,“还不知世上有什么‘神话批评,可是事后人们对我说我属于这一流派”[1]。弗莱将任何从外围研究文学文本的方式,统称为“文献式”研究。马克思主义批评、社会学批评、心理学批评、传记式批评等皆属此类。他从根本上否决了文献式批评能达至诗的真正意义。但是弗莱后期的学术研究却一反常态,大量援引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研究成果,并将意识形态概念引进自己的理论体系,置于非常显要的位置。此种一反常态的转变根源于弗莱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整体有机且置换循环的文学架构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暴露出诸多问题,甚至面临难以为继的局面。意识形态的引进是为了进一步打开原型批评的理论空间,也是其理论突破自我的更新。
一、关怀神话与自由神话:重建文学的社会维度
弗莱的原型批评向意识形态转移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不是一次突变的革命。弗莱的文学批评总是避免那种激进的破与立,包括对文学意义的阐释和理解。他更喜欢将文学的意义还原于绵长悠久的文学历史当中,这一点让他跟新批评进一步拉开距离,尽管两者都主张立足文学本身的形式和语言来阐释文学,强调文学的本体地位。一般人们认为弗莱与新批评的分歧在于后者拘泥于单个文本细读,而前者视整个文学世界为一体。事实上两者深层的区别在于,弗莱坚信文学意象或象征意义的一脉相传,它们具备某种恒定的特征,以及文本之间的互文性和相关性,而新批评则不断解构文本的确切意义。作为先行者俄苏形式主义提出的陌生化,还只是强调文学的不断更新和进步,而稍后含混、反讽、悖论、意图谬误等概念的出场已然摆出一副解构主义姿态,任何确定意义的解读都会遭到批评家们轻蔑的嘲讽。这种情况如同阿多诺对20世纪初艺术寻求自律冲动的分析一样,本来是探寻艺术的本质特征,结果却导向了所有确定性的消失。“1910年前后,革命艺术运动开始探寻的那一出乎预料的广阔领域,未能兑现其早先提出的幸运与奇遇的诺言,反倒出现了这样的情形——此过程在当时危及到自有理由存在的诸多类似范畴。”[2]文学自律性便是首当其冲受到怀疑的范畴。新批评面临同样的困境,丧失语境或者历史纵深之后,文学意义的捕捉变得更加困难,其阐释力的贫乏很快暴露出来。弗莱断言:“这种批评方法的局限很快就变得十分明显,而且大多数新批评派的批评家迟早会重新依赖已经确立的某种文献的语境,一般是历史的语境,尽管他们最初被认为是反历史的。”[3]7而这将导致他们重新滑向传统的传记式批评、心理学批评或者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式批评。弗莱认为文学研究无法抛弃历史的纵深,也不可能在完全丢弃语境的情况下就文本谈文本。这种情况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被弗莱所言中,新批评的主将们有不少后来都转向了宏观的社会批评。
弗莱一开始就意识到新批评的软肋所在,所以他要打造属于文学自己的历史语境,“批评必须在文学内部培育一种历史感,以补充那种把文学同其非文学的历史背景相联系的历史批评”[3]9。这种批评正是弗莱所说的原型批评。《批评的解剖》正是这一宣言的最好实践,不过一直以来弗莱只是从原型出发来建构文学的历史维度,却并没有解释这一独立的历史语境具体是如何形成以及如何运作的,这个问题被弗莱长期忽略。当弗莱正视它并致力于给出合理阐释时,被隔离的历史维度又明显无法提供强大合理的解释,重新转向文学与社会之间的联系就成了不可绕行之路。这种转向从《批评之路》对关怀神话的构建开始,此时距《批评的解剖》出版已有15年之久。这本小书在弗莱的学术生涯中具有重要意义,它像一个分水岭,隔开了弗莱学术生涯的两个迥然不同的侧面:前期致力于神话原型的理论建构,形成了整体有机且置换循环的文学世界,范围非常克制地在文学范围内游走;后期从理论建构走向实践佐证,从民间传奇特别是《圣经》等具体的文学文本出发,佐证前期建构的神话原型理论。后期弗莱的学术考察范围不断扩大,社会学以及文化人类学视角不可避免地突入进来。
中国石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8月
第33卷第4期李巍:弗莱神话原型批评的意识形态转向
在该书第一章,弗莱一如既往地强调了其在《批评的解剖》中的立场,他再次明确了诸多外围“文献式”批评将与诗真正的意义无缘。诗的意义必须基于它本身的形式和语言,这也是他始终与新批评保持一致的地方。第二章却笔锋陡转,抛出自己的神话概念。他以民间故事、民间歌谣等为对立参照物确定神话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神话必然以神话群的状态存在。“随着一种文化的发展,它的神话倾向于包罗各个学科,扩展成一个总的神话,它包括一个社会对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的看法,与它的诸神和邻里之间的关系,它的传统,它的社会和宗教责任,以及它的最终归宿。”[3]18为什么神话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整体,而民间故事只是一些散兵游勇,这是由它们的功能决定的,因为神话或文学具备社会关怀功能,“关怀神话的存在就是为了将社会凝聚在一起。对于神话来说,真理和现实与推理和证据并非直接相联系,而是社会地建立起来的”[3]18。关怀神话能够对抗社会长期存在的所谓“持续性焦虑”,并将社会凝聚起来,而“持续性焦虑”产生于人类的某些基本困境,如疾病、食物等。弗莱对关怀神话的社会建构性和人为性的界定已然让其具备了意识形态属性,特别是它维护社会稳定的功能正是意识形态的内在规定性。弗莱将神话与社会这样连接,已经接近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批评范式,如英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考德威尔对诗的起源和功能界定。考德威尔认为诗在诞生之初就具备强大的社会作用,它通过塑造高于现实的“幻象”让人们提前感受收获的喜悦,从而能够战胜艰苦的现实劳作。“唯有通过诗的幻象,一个更高的现实才能显现,不然它无法存在。要是没有异想天开地描绘充盈的粮仓和收获的欢愉的仪式,人们难以正视从事收获所必需的艰苦劳动。有一首丰收歌助兴,工作就进展顺利。”[4]能制造“幻象”的诗似乎与解决“持续性焦虑”的神话在功能上并无多大差别。endprint
相反,那些不能发挥社会稳定作用的文学形式,统统被弗莱扔出神话体系之外。“符合真理的正常趋向是非神话的,不是直接诉诸关怀而是诉诸更能自我确证的标准,如论证的逻辑或(通常在后期)非个人的证据和检验。但它所演化出的心理态度,其中包括客观性、判断推理、容忍和尊重个人,也会变成社会态度。对关心这些态度的文字,我将之称为自由神话。”[3]2425这种自由神话包括科学、逻辑等领域。通过自由神话与关怀神话的对立,文学开始走向社会。对神话或文学的论述逐渐偏离弗莱最初的预想,文学和文学批评虽然还保持表面上的独立自足,但文学与外部社会产生了不可动摇的联系,甚至“神话就是文学,文学就是神话”的铿锵断言也是在文学“维护社会稳定”的巨大前提下实现的,而所谓文学独立的历史维度早已掺杂了某种外围因素。当然在《批评之路》一节中,这种转向并不明显,弗莱只是表明文学作为一种关怀神话,具备某种社会功能,这并不威胁文学的独立性。文学是否在缺乏社会维度之后将无所适从,这个问题并没有凸显出来。
二、意识形态在《圣经》研究中的出场
当《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1982)成书时,弗莱明确了文学或神话是某种意识形态发挥作用的重要工具。当然《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主要是讨论《圣经》,文学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文学的意识形态属性都是通过《圣经》得以展现。至于为什么意识形态是在《圣经》的研究中出场,原因大概是“假如我们承认西方文明可以概括为基督教文明,那么西方传统中核心的观念和表达程式、规则就有可能通过基督教的经典神话得到重现”[5]138。那么,《圣经》的特性就是后世一切西方文学的特性,而且是其最原初、最集中的表达形式。
弗莱借用加拿大学者麦克卢汉的媒介学观点,按照媒介的不同将语言分为三个发展阶段,三个阶段也分别代表了语言的三种特性。第一是口语传播时代,人们面对面交流,交流时主体双方高度参与,各种感官官能能够综合调度。此时神话隐喻思维盛行,这种思维“表示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的生命或力量或能的同一性的意思”[6]24。即一个东西可以是另外一个东西的思维能力。第二是书写媒介(文字)的产生,语言的转喻功能被强调,线性字母文字凸显了视觉的优先地位,线性逻辑思维不断得到强调,各种形而上学思想大行其道。古希腊和中世纪欧洲都是其典型代表。“随着文学融入书写文化的思想习惯,文学被认为是一种休闲的装饰,是发达文明的一种副产品。”[3]54第三是文字的描述阶段,这一阶段科学崛起,实证主义思维大行其道,人们要求语言能严格对应客观自然。它大概是文艺复兴之后的事情,跟印刷术的普及推广有一定关系。人们常把《圣经》当做宗教圣典或历史文献(反映了古犹太人的历史),这两者分别是在语言的转喻和描述层面上来理解。毫无疑问这些切入《圣经》的方式会产生严重误解,因为《圣经》产生于口语传播时代(即神话时代),是用隐喻语言写成的神话,唯有用当今读诗的方式切入才能更接近它的本真。
《圣经》最初用隐喻语言写成,因为它诞生“在语言的隐喻阶段,词语意义的许多方面如果不通过隐喻或诗的方式,是无法表达的”[6]80。更重要的是它也必须在隐喻的层面被理解。“传统的基督教的很多重要教义必须通过隐喻的形式才能合乎语法地表达出来。”[6]82如,三位一体教义、基督的血肉化为圣餐中的面包和酒等都必须依赖语言的隐喻性来把握,理性思维和科学实证面对《圣经》,有点读天书的意味。除了基督教,世界其他宗教甚至世俗政权的合法性表达都依赖语言的隐喻特性。如在中西都颇为流行的君权神授观念,中国皇帝与真龙或天子相互等同的观念等都是如此。弗莱在这里虽然没有明确提及神话的意识形态功能,但他的论述和举例都证明了神话隐喻在实际运用时可以成为支配阶级的意识形态或至少能为之服务,这一点在稍后的《神力的语言》中得到明确回应。隐喻不仅帮助传达正统教会的教义,还帮助营造一系列隐喻体系来佐证自己的教义,如对婚姻和女性的规训,《圣经》提供了三种女性的隐喻形象,恶魔的、类比的以及启示的。她们分别对应巴比伦淫妇、被宽恕的淫妇(出现在以西结书等章节)以及《雅歌》中的新娘。通过三种不同女性形象的隐喻对比,人们更能直观地吸收基督教的教义内容,从而实现对社会的规训与管控,或者说关怀功能。如前所述,在弗莱构建的文学历史中,文学皆起源于神话,而西方神话的源头正是《圣经》。那么将《圣经》与文学的隐喻本性理清之后,二者就站到了同一条战线,《圣经》所拥有的社会建构作用都将传导给后世的文学作品。后世文学的隐喻特性也必然发挥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阐释和维护功能。
除了对《圣经》的神话和隐喻特性进行强调外,弗莱还指出《圣经》和马克思主义(两者都是弗莱认可的具备百科全书式的关怀神话)所特有的“类型学特征”。类型学与其他意识形态的区别在于它们不仅维系社会稳定,还引导人们朝向未来定向运动。《圣经》宣扬伊甸园的复归和人性的救赎,马克思主義宣扬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大同世界,这无疑都是一种指向未来的神话,这让它们与一般指向过去的关怀神话区别开来。类型学特征表明某些神话形态不仅要为持续性的社会焦虑提供支持,还要为未来的发展提供路标。弗莱对《圣经》类型学特征的强调及其与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对比都进一步强化了《圣经》的关怀作用,或曰干预社会的作用。
意识形态概念最终在《神力的语言》中出场。弗莱在语言的三个阶段中插入一个意识形态阶段,而且置于非常靠前的位置,形成了隐喻、意识形态、转喻、描述性四个阶段。“我们第三种模式最紧密的发展,便是由人们所接受(且大部分为经检验)的我们称为意识形态的那些观念所构成的庞大框架。”[7]17由于弗莱是回溯式的论述,所以意识形态是处于隐喻之后的第二个阶段。如果横向考察的话,可用一个金字塔来表示四者的关系,隐喻处在金字塔的底层,它是一切语言的基础性能,往上依次是意识形态、转喻和描述。上一层必然包含下一层的语言特性,如描述性语言(如新闻等)必然具备意识形态和隐喻特性,但隐喻(诗)性的古老诗歌却并不必然包括转喻或描述特性。从流动性来说越是居于高处流动性愈大,如描述性语言十分严格地对应自己的时代和语境,脱离了时代和语境就失去了描述价值。对此弗莱多次以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为例,该书在它诞生的年代具备描述特征,它被视为历史事实,该书一系列结论伴随新史料的发掘被推翻后,其描述性功能丧失,但是意识形态和隐喻功能依然存在,它依然可以作为文学作品被人们阅读,不过此时它主要建构于文字的隐喻特性之上。意识形态虽然非常靠前,这表明它的流动性较小,但它并非一成不变,它们也会“由诞生逐渐衰退、死亡或转变为其他形式”[7]21。不过相对来说变化更为缓慢一些,如科学和世俗哲学崛起之后,基督教以地球为中心的宇宙观(一种意识形态)才逐渐被新的意识形态所取代。这几种特性虽然共存于语言之中,但在实际理解时却是相互排斥的,如当我们把《罗马帝国衰亡史》当做科学时,隐喻和意识形态功能就被抑制了,反之亦然。endprint
自此,弗莱的原型批评已经完成了向意识形态的转向,尽管弗莱强调的意识形态不是国家机器的表征而是语言进入文明之后的一种功能形态,他想借此拉开自己与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的距离,同时保持原型批评的纯粹性。因为如果他论述的意识形态只是一种语言功能,那么他就没有越出新批评以来的传统。从语言出发来谈文学向来都是正当合法的,符合对文学本体化的建构。但毫无疑问意识形态的出场已然表明文学与社会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语言意识形态的发挥必然是社会变迁所致。而且意识形态被置于隐喻之后的第二阶段,跟人类文明的曙光同时诞生,这基本上意味着文明兴起之后的语言形态(特别是文学),必然涉及语言的意识形态。那么离开了社会维度,对文学的把握将是不可能的。纵观弗莱的学术研究,神话的意识形态属性是关怀神话这一思路继续深挖之后的结果,意识形态的突入有着深刻的学理动机。
三、意识形态转向的原因辨析
弗莱从关怀神话的建构开始,逐渐建立起文学的社会维度,直至意识形态的出场、完全承认文学与社会之间的必然联系。弗莱这一转变的内在动力来自何处?对这一问题的考察需要首先回到弗莱最初的理论建构上。在《批评的解剖》中弗莱建构了一个独立自足的文学世界以及同样本体化的文学批评场域。“批评看起来非常需要一个整合的原则,即一种中心的假设,能够像生物学中的进化论一样,把自己所研究的现象都视为某个整体的一部分。”[8]另外,文学不仅被设想为一个整体,有一个类似进化论的中心假设将所有文学收纳,而且该整体还呈现为规律循环状态。如从人物行动能力的高低来看,文学整体是从神话、传奇、高模仿、低模仿到讽刺的循环变迁;从完整的故事链条来看(英雄的死而复生),文学整体是从春季叙事(对应喜剧)到冬季叙事(对应讽刺)的循环变迁。每个季节的叙事又有六个相位,前三个相位与上一季节的后三个相位相连,后三个相位与下个季节的前三个相位相连。当然由此带来的还有文学意义层面的循环变迁,它们分别是字面、描述、形式、神话以及总释五个阶段。这个循环必然是整体联动的,否则文学世界必然混乱不堪。
《批评的解剖》借助整体循环理论的确在某种层面上完成了对文学世界的重构,但它的漏洞如同它的创见一样多。首要一点是如果文学自足独立,与外部世界互不干涉,那么文学本身循环的动力将无从解释,毕竟循环也是一种运动变化。“弗莱批评理论的缺陷是缺乏动力系统。要想建构一个严密的运动体系,必须解决动力问题,即回答原型在文学发展中移位变形、一系列大大小小的相位不断嬗变循环的力量源泉是什么。”[9]文学不可能自行进行这种循环运动。其实后期的弗莱对这一问题是有所警觉的,他曾说“《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一书在很多地方得益于维科,他是现代思想家中第一位理解一切主要文字结构的,从历史上讲都是由诗歌和神话结构演变而来。但是即使维科,对文学持续的社会功能也并无多大兴趣,因而很少关注是什么原理促使这种功能恒久不衰的”[7]23。无论是源于理论自觉还是出于对理论完善的需要,弗莱都会迈出这重要的一步,为整体循环的文学世界找到背后的动力机制。但弗莱显然又不想陷入之前的老路,将文学的发展或解释权完全拱手交给一个完全不同的学科,如社会学、哲学或心理学。马克思式的经济社会学考察显然不符合他的理论品位,黑格尔、荣格等人的绝对理念和集体无意识概念也不能令他满足,因为这依然是一种心理学或哲学入侵。文学还是没有独立存在的证据。于是,一个既能让文学独立自足又能提供其循环动力的概念就呼之欲出了,被限定为语言特性的意识形态概念将是最适合的。于是弗莱首先确定隐喻为语言的始基,它表征人与万物的互联以及行动的可能性,它的指涉是无穷的、性质是中立的,因此它不会变化且内涵无限丰富。进而语言的意识形态功能被确定为一种“应用型神话体系”,它存在的目的就是根据意识形态标准限制隐喻语言的无穷指涉功能,将其能指与所指固定下来为我所用。意识形态按照自己的需求从这个神话体系中肆意抽出于己有利的部分,同时去掉于己有害或无用的部分。“每种意识形态开始时都就其传统神话体系中意义重大部分提出自己的认识,并利用这种认识去形成并实施一种社会契约。这样一来,意识形态便成了应用神话体系。”[7]25文学之所以会呈现循环流转的样态,是因为社会形态的变迁导致对语言意识形态的调用。隐喻语言在这里承担的角色类似于荣格的集体无意识,一个完整而略带形而上学特性的事物。因为荣格的集体无意识是每个人都拥有的完整心灵,文明发展导致这种完整性被破坏,进而才有心理原型的不断复现来弥补这一欠缺。“一个时代如同一个人;它有它自己意识观念的局限,因此需要一种补偿和调节。这种补偿和调节通过集体无意识获得实现。”[10]荣格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解决了原型复现的动力问题。显然弗莱在这里对他进行了一次巧妙的置换,集体无意识被置换成了神话隐喻,而时代缺陷则与语言的意识形态性在功能上相等同,它们是动力的来源之地。
除了动力性问题外,弗莱还面临文学整体性如何可能的难题。毫无疑问,弗莱的文学世界是有机统一的整体,即使它们循环也是作为整体循环。在关怀功能出现之前,文学的整体性无从确认,是关怀神话让文学世界被一个具体功能收编,即“维护社会的稳定”或“解决社会的持续性焦虑”。功能统一保证了文学作为整体的可能,因为不在关怀之内的语言形式将转化为其他学科形态,如哲学、科学等等。它们不是神话的一部分,自然也不是文学的一部分,所以文学能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相比关怀神话,意识形态显然更具备这种整体收纳能力,意识形态本身就包含着“群”和“控制”的含义,“意识形态既可以被看作有关一系列假设的描述性标签,也可以看作对社会世界是如何运行,以及对应该所是的情况如何做出规定的信念,……它们被坚信具有更多的一致性,而且它们经常与特定利益的辩護和维持相关联”[11]。一种意识形态要想发生作用,也必然有一系列相应的文化、政治、经济等策略相支撑。所以在《神力的语言》中,弗莱将关怀和意识形态并提,两者一同发挥作用。关怀在此时又被弗莱进一步分成两种关切:第一种关切是针对吃喝拉撒等人类基本问题,第二种关切针对阶级、民族、爱国主义等身份归宿问题。第一种是《批评之路》中所说的解决持续性焦虑的内容,第二种是意识形态。前者基本上没有变化,向来都是基本原型;第二种则因为社会的变迁而不断改变,其改变途径是抢夺对第一关切神话的解释权。关怀功能和意识形态功能,让文学必然趋于整体运动得到了一个合理的解释,文学关注的吃喝拉撒以及身份归宿等问题都是人类普遍面临的问题,特别是意识形态对人类社会身份的建构必然是整齐划一的,没有哪个意识形态是专门培养敌对意识或多元意识的。endprint
当然,弗莱原型批评的意识形态转向跟马克思主义本身强大而持久的影响力不无关系。西方马克思主义一向都是影响巨大的人文思潮,其理论形态也不断更新发展。弗莱在为自己的理论张目时,借用一种对立的理论作为反面典型也是合情合理的,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各方面来说都符合这一条件,理论立场不同而且其影响力巨大。纵观弗莱学术生涯,其对马克思主义的关注是一如既往的,在写作《批评之路》时,他把马克思主义等其他文学批评与原型批评进行对比,从而否定前者的文献式批评。在《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中他又单独列出马克思主义,并声称它与《圣经》的独特之处在于具备一种“类型学思维”,这让两者得以区别于其他意识形态体系。弗莱在建构自己的原型理论体系时,处处都与马克思主义做对比,这表明他对马克思主义熟稔在心。在对马克思主义持续的批评之中,最后借入对方某些合理的观念和论述似乎也是理所当然的;而且马克思主义与《圣经》的相似也表明弗莱开始从神话的角度而不是对手的角度看待马克思主义,所以后来弗莱在进行理论完善时借用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概念也并不令人惊讶。
四、结语
弗莱要在坚持文学本体地位的前提下解决文学整体循环的可能性和动力性问题,语言的特性必然是他必须始终握住的救命稻草。从文学的关怀属性到神话的意识形态属性,弗莱看似解决了漏洞又守住了文学独立的学术立场,实则早已跨出纯粹的文学研究走向更为宽泛的文化研究。这是一种理论自觉的走向,也是弗莱“向后站”视角的必然结果,“从纯文学退到宗教、文化的大背景上,这实际上已经超出所谓‘纯正的文学史的界域,说明这位文学批评理论家在学术发展途中实现了学科超越与自我超越,实际上也以文化批评家的身份出现了”[5]152。文学是自足的,它有一个本体存在依据,弗莱所坚持的这一文学信念本身就是历史的产物,是现代学科分化的结果。早期西方并没有纯文学概念,更不用说独立的文学批评,现今被视为文学文本的作品从来都是多属性混杂的,如伊格尔顿所说:“在18世纪的英国,文学这一概念不像今天有些时候那样,仅限于‘创造性和‘想象性作品。它意味着社会中被赋予高度价值的全部作品:既有诗,也有哲学、历史、随笔和书信。”[12]所以“向后站”在超越了某个时间节点之后必然导致跨学科的视野。也许弗莱并不会承认文化研究者的称号,要不然他也不会强调意识形态是种语言特性,而非国家机器的表征。但是这并不妨碍弗莱的理论已经游走到弗莱所设定的边界之外。而意识形态的出场更是敞开了原型批评通向文化研究的大门,从而结束了文学研究的形式主义时代。它将神话原型批评带入了更广阔的人类学和文化研究领域,因而不至于让原型批评走向自我封闭的绝路。
参考文献:
[1] 诺思洛普·弗莱.诺思洛普·弗莱文论选集[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147.
[2] 阿多诺.美学理论[M].王柯平,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8:1.
[3] 诺思洛普·弗莱.批评之路[M].王逢振,秦明利,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4] 考德威尔.考德威尔文学论文集[M].陆建德,黄梅,等译.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25.
[5] 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知识全球化时代的文学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6] 诺思洛普·弗莱.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M].郝振益,樊振帼,何成洲,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7] 诺思洛普·弗莱.神力的语言——“圣经与文学”研究续编[M].吴持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8] 诺思洛普·弗萊.批评的解剖[M].陈慧,袁宪军,吴伟仁,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6:22.
[9] 梁工.试议弗莱原型批评的缺失之处[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1):18.
[10] 荣格.心理学与文学[M].冯川,苏克,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101.
[11] 马克·J·史密斯.文化——再造社会科学[M].张美川,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4950.
[12] 特雷·伊格尔顿.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伍晓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16.
责任编辑:夏畅兰
"Ideology Turn" of Fryes Archetypal Criticism
LI We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 South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Guangdong 510006, China)
Abstract: Frye isolated an independent and circular literary world in Anatomy of Criticism. But the possibility of the whole circle of literature was questioned because of the absence of external context. Initially Frye intended to connect literature with society through the concern function of literature, but where the motive power of circle comes from is still hanging. So he introduced the concept of ideology in the study of the Bible, which was defined as a function of language. Ideology can adjust the relationship of signifier and signified of language according to the changes of the society. The problems, such as where power comes from and what is the re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iterature and society, were solved. At the same time, it does not violate the ontological status of literature. Bu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literature and ideology moves Fryes archetypal criticism towards broader cultural criticism gradually.
Key words: Frye; archetypal criticism; ideology; Bible; concern myth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