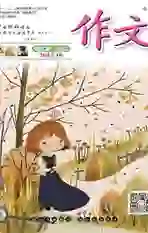鞋子的故事
2017-10-25杨秀生
杨秀生
每到暮春,母亲都要用她忙碌了一个秋冬的成果(自纺自织的一大卷白粗布,或染成胶泥色或染成毛蓝色、黑色),为全家每个人做一身单衣过夏,还有一双白底黑面的粗布夹鞋。我是例外,夹鞋是两双。
我生来就是“镰刀脚”(大拇脚指比二拇脚指长半指),穿鞋特别费。一双新鞋穿在别人脚上,两三个月还是好好的;可是到了我的脚上,用不了一月四十天,就会“前头脚趾着地,后头鸭蛋出气”。也许因为我是弟兄三个中最小的一个,母亲特别偏爱我。“小三儿小三儿,娘的心尖儿”嘛,反正俩哥哥都是一双夹鞋,而我是两双。有时候哥哥们不服,我就说:“火车头冒烟——白气儿。”
爱玩是孩子的天性。那时候太穷,没有太多的东西可玩,脚上的鞋子便是很好的玩具。夏天,吃了晚饭,天刚刚擦黑,蚊子就上“市”了,围着光光的黑脊梁“嗡嗡”响。坐着不动“喂”蚊子,那滋味实在难受。掷鞋楼吧,跑起来,动起来,蚊子就不会咬了。
掷鞋楼开始了,我们每个人脱下一只鞋子,鞋跟在下,鞋尖朝上,堆在一起,搭成一个下面粗上面细的鞋楼。那鞋楼倒也五颜六色,因为鞋子的主人来自不同的家庭,所以鞋子的新旧、颜色、大小也就各不相同。鞋楼搭好了,通过抽签的方式,定出一个守楼的人。守楼人要哈下腰来,撅着屁股,叉开双腿,罩着鞋楼,然后脱下另外一只鞋,双手紧紧握住,在两腿之间不停地晃动。其余的人,退到一丈以外,脱下另一只鞋,攒足力气朝鞋楼狠狠掷去。一阵猛烈的“鞋雨”朝鞋楼及守楼人袭击之后,如果鞋楼塌了,守楼人算输,继续守楼,继续遭受“鞋雨”的袭击。如果鞋楼没塌,安然无恙,则守楼人取胜,换人守楼。我当过守鞋楼的人,经受过暴风骤雨般的鞋子袭击,头、脸、手、脚、胳膊、腿被砸得生疼生疼的,火燎一般。但过去之后,一种胜利者的快感便会油然而生。我也当过投掷者,攥紧自己的鞋子,瞄准鞋楼,奋力一掷,鞋子闪开守楼人的双手,穿过他两腿之间的空当,只听“噗”的一声鞋楼坍塌了,那种成就感也是妙不可言的。我们就这样掷着、叫着、喊着、闹着,几天下来,一双新鞋子也就浑身开了花,破烂得挂不住脚了。母亲没有因此吵骂过我,只是等我玩累了,睡下了,就着昏暗的油灯,把破烂的鞋子一针一线地缝好补住。第二天,我们照样穿着鞋子满街跑,晚上照样掷鞋楼。
阴历初二或初三,黄昏,挂在西南天空的月亮弯弯的,两头尖尖,像啃剩的西瓜牙儿。我们刚把鞋楼搭好,不知谁的眼尖,大叫一声:“看,盐蝙蝠!”我们立即停手驻足,向天空看去。哇,头顶上,黑乎乎几十只盐蝙蝠在翩翩起舞,听大人说那是盐蝙蝠在捕食蚊子。我们不太相信,黑灯瞎火的,月光也不太亮,它们会捕到蚊子?管他呢,跟它们玩玩再说吧。我们便把鞋子抛向天空,并且边抛边喊:“盐蝙蝠、盐蝙蝠,我的鞋是你的屋。”盐蝙蝠好像有意逗我们玩儿,每当我们把鞋子抛上去,盐蝙蝠就会接近它,好像真的要把我们的鞋子当作它们的屋子钻进去,可是眼瞅着盐蝙蝠就要钻进去了,它们却又悠然地飞开了。我们不甘心,盐蝙蝠也乐此不疲。直到我们累得坐在地上爬不起来了,盐蝙蝠才一只只飞走了。可是,等到收拾鞋子回家睡觉的时候,却发现我的鞋子丢了一只。“是不是被盐蝙蝠背走做了屋呢?”我默默地想。这样一想,心里就有些害怕了,因为我早听人说,盐蝙蝠是偷吃了盐的老鼠变的,你想啊,丑陋的老鼠再长出两个翅膀来,样子多可怕呀,要是真把我的鞋当成了它们的屋,住上一段时间,它们又会变成什么样的怪物呢?我的鞋还能不能再穿呢?
我不敢再想下去,急急忙忙地跑回家。母亲还没有睡,她在灯下做针线活。见我浑身是土,一只脚光着,问道:“鞋呢?”“丢了,要不就是叫盐蝙蝠背走了。”“瞎说,盐蝙蝠才不要你的臭鞋呢。”母亲佯装生气地说。说着便走出了院子。到底在我们投掷盐蝙蝠场地旁边的土墙根儿处,找到了那只浑身开花的鞋子。可是,那只鞋子已经破烂得不能再补了。
第二天早上,母亲从箱子里拿出一双新鞋给我。我穿在脚上,轻轻地跺了跺,看到大拇脚指头顶得老高,就说:“娘,小了,有点儿窝脚。”母亲说:“你呀,不见人大,光见脚长。也好,大拇腳指头长,长大孝顺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