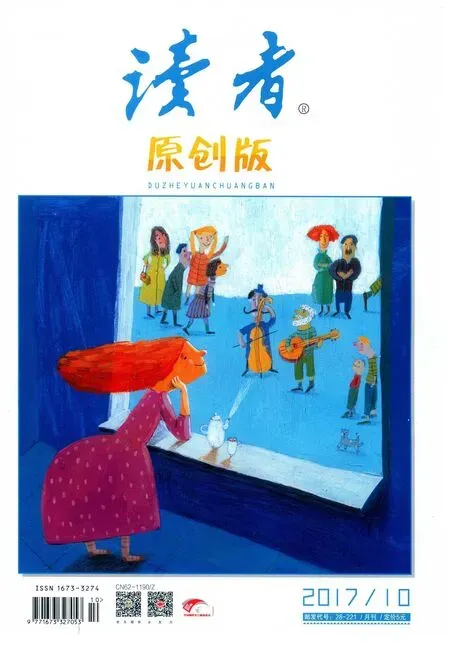“猪笼寨”里的“贵族”
2017-10-12严柳晴
文|严柳晴
“猪笼寨”里的“贵族”
文|严柳晴

一
老赵站在弄堂的院子里向外望,四面楼房,四面人家。活了半世,老赵第一次觉得,自家院子像口井,人坐在里面,只看得见圆圆的、镜子似的一面天。
这是他长大的地方。很久以前,这里是公共租界巡捕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划归国有,改名隆昌公寓。以前,他觉得隆昌公寓很大,简直是整个地球;现在它显得那么小,比不上一颗弹子糖。
一道羊肠弄堂,连接了隆昌路与隆昌公寓的大院子。马蹄形的环状楼房,圈起一个世界。
电影《功夫》里面有一座楼房,形貌与之酷似,叫作“猪笼寨”。看过《功夫》的年轻人,看到隆昌公寓尤其起劲:“上海还有这种楼!长得跟‘猪笼寨’一样。”
网络时代,一句屁话如逢好运,瞬时就可声震万里。所以,隆昌公寓就顺理成章地被叫作“猪笼寨”了。这个土得掉渣的名字没有经过老赵的批准。如果有人征求他的意见,他一定是不乐意的。一拨儿又一拨儿年轻人捧着照相机,颠颠地跑来,小年轻说:“叔,我们想听‘猪笼寨’里的故事。”
“啥?‘猪笼寨’?!”老赵手伸得老长,皮夹克的袖子直往下落,一条闪闪的金链子松松垮垮地搭在手腕上。见众人的眼光都被攫走,老赵戴着金链子的手在空中停顿了一下,然后两只手臂环扣,顺势搭在后脑勺上。
“告诉你,这里是个豪宅。”老赵坐在一把藤椅上,人舒服地往后一靠,老藤椅吱嘎一摇,说:“现在什么汤臣一品啦、嘉庭啦,都比不上这里。几十年之前,不要说高楼了,像样的房子都很少,这里可是一栋5层电梯房。这不叫豪宅,啥叫豪宅?”
“原来‘猪笼寨’老早那么风光。”小年轻敷衍道。
“怎么又叫‘猪笼寨’?!”老赵似身上被浇了热油,火急火燎地站起来,狠狠地从鼻腔里掼出一声:“嘁—”
二
这里已经没有一点儿豪宅的样子了。凭良心讲,“猪笼寨”这个土名字,完全配得上它如今的落魄光景。以前一个院子住10户人家,现在变成了250户。走廊里东一只碗橱,西一只柜子,物件缝里还要填破报纸、烂鞋、螺丝钉……
但无论如何,这里曾经是个豪宅呀。老赵话兴已起,不吐不快。他要和小年轻们聊一个老同学,姓钱。老赵说,现在这位同窗年纪也大了,姑且叫作“老钱”吧。
老钱和老赵的关系好得不一般。上海男人不打架,但只要一起玩大,一样能同甘共苦,一样是兄弟。这个叫老钱的家伙,夏天一件大白背心,冬天一件灰绿棉衣,半个脑袋缩进脖子里,显得肩膀又尖又高。老钱第一次到隆昌公寓,脑袋探进羊肠弄堂,看一看:“哇,这是什么地方,乖乖。”又一缩头,把脑袋从小弄堂里抽了出来。
“那时候,同学们是很崇拜我们的。老钱看到这里面这么大,住得那么高级,差点儿被吓死。”
老赵当然有家底。住隆昌公寓的人,大都是北方南下的干部。老赵的父亲是山东人,在上海待久了,培养出一口“山东上海话”,开口是“阿拉山东人”,同学一听就知道,这是住隆昌公寓的,贵族;老钱讲“苏北上海话”,一听就是棚户区出身,穷人一个。
老赵有时候想,语言这东西多么奇怪,嘴一张,身份就已不同。不过,他也懒得细想穷究,毕竟他是占便宜的一方。
“老钱是穷小孩嘛,对他来说这里什么都是好玩的、高级的。”老赵伸了伸脖子,继续说道。在老钱把脑袋缩回去的那天,老赵把他带进了公寓里。
一天上完课,他们在学校后院抓了一只兔子。老赵把兔子养在隆昌公寓的走廊里。兔子每天都饿不着,今天啃菠菜叶子,明天啃花菜叶子。老钱见了,哭哭啼啼:“兔子吃的比我们家里吃的好多了!”
老赵拍了拍他的肩:“别跟个娘儿们似的,以后跟我混,保你日子过舒服了。”
三
20世纪60年代,老钱和大多数同龄人一样,随时代吃苦受累。辣椒酱拌白米饭,一家老小吃一年。而老赵这个说着“山东上海话”的贵族,从来不用担惊受怕。隆昌公寓一直都很温暖,像刚喝饱热牛奶的胃,保持着优雅的恒温。
老赵一碰到老钱,手一扬:“走,跟我走吧!”
老赵从没有尝过饿肚子的滋味,怎么可以让兄弟受苦。而且,吃饱饭这件事对老赵而言,多么容易。隆昌公寓斜对角有一个供给处,猪肉粉条、菜饭都能吃上。老赵有的是粮票,一到饭点,就神气地吆喝一声:“吃饭了!”
供给处里开灶头,木盖一掀,热气一轮轮滚上来。老钱被满屋子的蒸汽迷昏了头脑,恍惚之中,扒光了碗里的每一粒米饭。老赵扫了他一眼说:“别吃了,剩点儿,碗里吃得空荡荡的,寒碜不?”
饱餐一顿后,他们从食堂里捎了些菜叶子,带给宠物兔子。一只兔子能过得那么好,老钱始终想不通。兔子和隆昌公寓的人,年纪轻轻就能颐养天年,上辈子得积多大的德。那些日子,老赵和老钱骑着自行车,在隆昌公寓的环形楼道里打转,一圈,两圈,三圈……
老钱对老赵说:“在这里过日子真开心,像在云里一样,像在天堂一样,什么都不用发愁……”老赵又把话劈断了:“愣子,别跟个娘儿们似的。”
四
“老钱大概从来没享受过这种好日子,恨不得过继到你家来了。”
“你们小辈要记牢,一家人有一家人的苦,谁都不容易。”老赵似乎觉得,如果人这一生顺逆相抵的话,他享的福根本抵不上受的委屈,还得不到旁人的同情,“做那个年代的有钱人,不太合算”。
老赵也是个苦命人。从小学到中学,班上的同学都知道,他有两个妈:一个妈在山东,一个妈在上海。父亲从北方南下,在上海再度成家。自打出生,老赵的头上就顶着三个字—“二奶生”。
老赵的大妈跑到上海来了,并不是来算老赵爹那笔“三心二意”的账,而是来向赵家讨吃的。在被饥荒裹挟的山东老家,老赵爹的前妻经年累月揭不开锅。于是她选择南下,把前夫当作救命稻草。
说着“山东上海话”的老赵爹深信“离婚不离家”,他强势、自负,也热心肠。从家里的角角落落搜出几斤粮票,又拎出一篮子鸡蛋。
两位妻子自然是摆不平的。日子过得像跷跷板一样,甜了这家,苦了那家。两位赵妈整日哭嚷,一个哭穷,一个叫骂,推推搡搡。
同学见状,编了个唱段:“老赵大娘哎,大老远跑来不饿肚皮;二娘哎,不是阿拉山东人……”
人群中冲出一匹野狼,那是老钱。他撕扯开集群“唱戏”的同学,正在亮嗓高歌的捣蛋鬼被他一把推倒在地:“滚,给我滚—”
用一笔巨款和全部的屯粮打发走老家大妈之后,老赵也终于体会到了拮据的滋味。家里说不上一贫如洗,但元气已伤。首先遭殃的是他的兔子,断粮了,兔子被掐断脖子时,惶恐地睁着眼睛。老赵不想吃饭,饿了几顿,神气都被抽走了。
他望着老钱,可老钱能帮上什么忙呢?老钱家里,弟弟妹妹一大堆。老赵坐在藤椅上,老钱坐在一级台阶上依着他,像两个老人一样,看太阳掉下山头。
五
时代变换了几轮,老赵去新疆当兵,老钱去崇明岛农场开垦。此去经年,各自在对方的人生里,都是一段空白。老赵偶尔给老钱写信,寄一点儿部队发的粮票,老钱偶有回音。但荒漠辽远,通信渐稀。
老赵在新疆当兵的那些年,身边有个喜欢文学的知青,知青常对着他念诗。老赵书没念好,但有些诗句,他听懂了。知青念“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他想到老钱;念“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想到老钱为他打抱不平的拳头;念“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他又想到那个娘儿们一样的老钱,一见隆昌公寓的好日子就多愁善感的老钱。老钱在哪儿呢?“少小离家老大回”,这家伙还活着吗?
老赵在乌鲁木齐娶妻生子,等再回隆昌公寓的时候,灰头土脸的。邻居见他蔫着一张脸,劝道:“老赵,想开点儿。现在的日子和以前也差不多,供给处那块开了一家大超市,什么都有。你的退休工资加当兵补贴,过日子足够了。”
但老赵觉得,世界已经调了个儿,与以前全然不同了:隆昌公寓住进了许多户人家,到处都是“七十二家房客”的痕迹。再后来,隆昌公寓就莫名其妙地被年轻人叫作“猪笼寨”了,一拨儿一拨儿的年轻人,拍照片的,看西洋镜的,在楼里横摆竖摆,搔首弄姿。
最要紧的是,老钱不知道哪里去了。老赵使劲儿想,也想不起老钱的模样。他也没有去打听老钱的消息,他怕老钱离开了,怕他变成孤老头儿了,也怕老钱发财了……故友旺达自然好,但他老赵的面子往哪儿搁?犹豫又犹豫,没有老钱的隆昌公寓,一日比一日陌生。
六
其实,老赵早已见过老钱。
老赵骑车子跑出去,东游游,西逛逛,想找点儿活干。刚回上海,又没什么技能,不能守着祖业坐吃山空。老赵想,小时候家里有点儿钱,享了点儿福,现在,一样一样的劳役,一件一件地还债。享福有日,还债无期。
有邻居告诉他,路边的一家扬州饭馆正在招聘杂工。老赵辗转寻了过去,走到距饭店大门10米处,看到一个60岁左右的男人,微微低着头,肩又尖又高。那是老钱吧?老赵想,又好像不是。
“老板,做大生意了啊?”有人跟男人搭讪。
“老早卖烘山芋存了点儿钞票,现在可以开小饭店了。扬州干丝、杂烩、芹菜炒牛肉……生意还可以……唉,小孩不争气,我就想着多赚一点儿。”
老赵看到饭店门口养了一只兔子,装在一只笼子里,兔子又大又白。他知道,那一定是老钱的店。想到老钱说“乖乖,兔子比人吃得还好”,老赵的眼泪顺着沟壑纵深的脸滑下来,又被皱纹给吞了,跟个娘儿们似的。